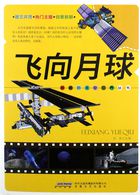“许久没出来看看了,这周围都变了。”阮绥忍不住的慨叹。而殷荀在身后却冷不丁的来了一句,“所以你是后悔进宫了吗?”
阮绥背后发凉,却不敢回头,只佯装疑惑,“您这是什么意思?”殷荀一把拉住阮绥的身子,阮绥踉跄了两步,只听到他没有温度的声音,“我什么意思你不会不清楚。今儿你已回了娘家探了亲,时候不早了我们便回去吧。”阮绥不敢多言,只跟着他的步伐。
回了丞相府,皇上都未曾发一言,阮绥也是匆匆的告别了双亲便上了香车,马蹄嗒嗒带走了本可以更靠近的两个人。
车里是恐怖的沉默,皇帝终是打破了这寂静,“回了娘家该满足了,以后便别再出来了。”
阮绥皱眉,那是如死刑一般的言语,不可置信道,“不知皇上此话何意?若是有人在您面前妄言也是道听途说断不可信。”
皇帝冷哼,打量着她,神情冰冷,让她不敢直视,“朕的皇后莫不以为朕是傻子亦或是瞎子?你敢说那皇宫你依然向往,不曾有一丝的后悔?”
他一针见血,她早已溃不成军。她紧握拳头,思量着该如何回答,可许久都不曾想到一个能应对他的答案。
“那皇上让臣妾如何?”她觉着心里酸涩,想哭却哭不出来。皇帝不再看她,掀开帘子,夕下的阳光打在他的脸上,添了几分和煦,薄唇抿着。看着外面,俊美的五官思考着,突然眸子微眯,残忍地开口道,“后宫杂事繁多,若没有要事,还是留在宫里。”
阮绥一脸的惊讶,她不敢想象方才在集市上像孩子般任性的男子是眼前的皇上,明明是一个人,却又像两个人。她恳求,“皇上……”而皇上却只摆手,并不想再听她多言。
阮绥一下子泄了气。
**
就这样,几天后,灵雨突然神神秘秘的向她禀报,“娘娘,宋婕妤的贴身丫鬟没了。”太监今儿早在井里发现了她,被人勒死的,那狰狞的神情可见死前的痛苦。
阮绥唏嘘,却对此事无太多兴趣,毕竟这宫里死人也是常见的。只是可怜了她成为一缕冤魂。
灵雨见皇后并未有异状,又附在她身旁轻轻的开口,“据说她曾给麟妃送过汤。”阮绥这下来了兴趣,“查明属实吗?”
灵雨点点头,“奴婢已派人查过,那宫人给麟妃送了汤没多时日麟妃便小产了。”
皇后心想,这若是宋婕妤干的,岂不是太明目张胆?抬眸问道,“此事你作何看法?”灵雨再三思量才敢回道,“宋婕妤给麟妃送汤不是一次两次,奴婢认为定是有人从中使诡计,利用了宋婕妤。”
这样的答案足以让阮绥刮目相看,她记得刚见灵雨的时候她是畏畏缩缩,讲话支支吾吾的,与如今这模样大相径庭。灵雨察觉到了皇后的质疑,搪塞道,“奴婢愚钝,乱加猜测,请娘娘恕罪。”
阮绥摆摆手,正色道,“你去查查,看那宫人去麟水宫途中是否与人见过。”
灵雨便领命去查了。
**
没过几日,就迎来了麟妃哭哭啼啼的跑进了俐荀殿。
“求皇后娘娘给臣妾做主,害臣妾小产的定是那贱人青黛!”麟妃的言语里夹着恨意,几乎是咬牙切齿。
皇后本在院子里看宫人打理花草,听到麟妃的话是满脸的不可思议,“麟妃,查明真相固然重要,可若是莫须有的罪名,后果可有想过?”
麟妃整理好自己的心情,向阮绥一字一句的说道,“皇后娘娘,麟妃派贴身丫鬟清幽给臣妾送了几次汤,有宫人看到后来两次清幽中途都遇到了那贱人,之后清幽就被人勒死投井。那贱人一定是想要消灭证人并栽赃嫁祸给宋婕妤!”麟妃越来越激动,让阮绥不得不相信。
麟妃看阮绥不言语,便更加急了,“若皇后娘娘不信,便去贱人那里搜一搜,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阮绥想着兹事重大不可轻视,“先不要走漏消息,本宫带人去搜屋。”
麟妃擦擦眼泪,谢恩。
青黛自从成了夜使,虽不必做重活,可也是不被人尊重的,这样平平淡淡的活着还不如从前。
就在青黛怀念从前的时候,被一群闯进来的人吓到了,表情严肃。
阮绥看了一眼青黛,又环视了一周,说出的话甚是威严,“搜!”
身后的侍卫听到了命令立即行动,那原本整洁的屋子一下子失去了原本的色彩。
青黛被这场景吓得花容失色,“皇后娘娘,臣妾不知犯了何事?”
阮绥还未开口那身后的麟妃就呵斥道,“青黛,你以为害本宫小产之事做得天衣无缝,不想东窗事发。今日皇后娘娘为本宫主持公道,你就等着皇上降罪吧!”麟妃噙着阴狠的面容,像地狱勾魂的使者。
青黛愣在当场口不能言,不一会,便有人喊道,“找到了!找到了!”
侍卫将东西呈到皇后面前,用纸包着,打开一看,是类似中药的东西。
阮绥闻了闻那味道,便清楚了,跟之前她喝的去胎药味道一模一样。她狐疑的望着青黛,后者紧张的面色惨白,双手绞着帕子。
麟妃看这情形见风使舵,指着青黛,“如今证据确凿,你可认罪?”
青黛颤着身子跪在地上,“臣妾虽有这些药物,却不曾害过别人,请皇后娘娘明查。”
阮绥皱眉,神情中透着失望,“那为何藏着这些药?”
青黛却怎么也答不上话来,垂手哭泣着。
阮绥悠悠的叹了口气,“此事本宫自会秉明皇上,由皇上发落。这期间,你不可踏出此半步。”于是转身甩袖离开。
青黛摊在地上,眼神空洞。
皇帝知道此事似乎并无异样,只平淡的说了句,“打入冷宫罢。”
阮绥再次去见青黛的时候,青黛已是一副衰败的模样,头发稍稍挽起,碎发落在额前,无一丝修饰。
“皇后娘娘……”青黛笑着,并不看她,咯咯的声音像哭泣的乌鸦一样恐怖。
她不再有下文,只是重复的呢喃,像痴了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