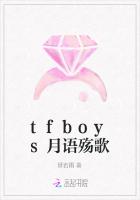林飞——林飞,眼前的这个叫作林飞的男人,怎么当初会爱上他?自己怎么就爱上这种男人了!
“林飞!你给我听着,你要是敢近小志半米的距离,我就让你死不得安宁!我白惠芬说到做到!你现在站在我面前,就象一只硕大的浑身散发着恶臭的苍蝇,让我倾尽全力也无法掩饰对你的反感和厌恶,你听着,不是仇恨,是厌恶,你明白么?我不会允许你这样的父亲,接近我的小志,我不会让你这种软弱自私连一个小小的约定都不能遵守的男人,改变影响我的孩子的人生。你最好离小志远一点,离我远一点,越远越好,最好永远不要出现!我要和我的小志,过全新的生活,请你离开我们的世界!林飞!永远离开!”
她的声调在最后一句提高了两倍,目光死死咬着,不容一丝退却。
林飞站在风里,感觉这个风快要把自己吹散了。
自己的神经就象勉强拼凑起似的,一不小心,轻而易举地,所有的意念就会散落一地,无处可寻。他去捡那些掉落的勇气,回忆,和属于他与她之间的某些快乐的碎片,他拾起,又掉下,掉下,再拾起,捧在手里,忽然一阵风来了,就没了。
他空落落地,怯生生地,犹犹豫豫地,徬徨不安地——站在那儿,站在白惠芬面前,象个罪犯无法避免地被送到了法官面前,他浑浑噩噩地游荡了一天,脑子里充噬着关于人生命运爱情什么之类的混乱的声音,努力想理出头绪,脚步却不知不觉地到了她楼下,到了她面前,然后,义无反顾地接受着她的嘲讽和责骂。
她脸上挂着泪痕,眼里盛着愤怒,他透过她的双眼,仿佛看到了小志伤心的脸庞,撕声力竭地哭泣。那个他所不敢面对的画面,此刻如此轮廓分明地映在他脑海里,为什么会这样?他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熟悉而陌生的女人——忽然想起第一次见她的样子。她穿着一条花格裙,象只轻飞的蝴蝶从风中走来,那是什么花啊,落英纷纷地飘洒在整片天地,他拉住她的手,在心里下定决心,要守护这个女人一辈子,永远不让她伤心。
是啊,立誓不难,难的是要遵守一辈子。
眼前的女人,已然不是那个落英中翩飞的女子了,她已幻化成坚硬的巨石,庞然屹立,这一切,均是拜自己所赐。
但自己又能做什么?林飞已被绑进另一个誓言中,不能自拔。
“他还好么?”林飞有气无力地问。
白惠芬眼睛突地就湿润了。
他还好么?
他能好么?
她苦笑。“好!当然好!你放心。”
“我今天是来给他送......书的。”林飞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拿出那一套“奥特曼”,送到白惠芬手上。
“其实,我也不确定自己能否面对小志。”他的眼睛也湿润了。这是他第一次当着白惠芬的面哭。“你,不让我见......也好。我也怕见了他,就再也舍不得离开了。”
他拭过泪,将书又递近了几分。“你把这书转交给小志吧,他看了一定喜欢的,就说是爸爸给他买的礼物道歉......当然,我也知道你不屑于这份道歉,但孩子是无辜的,他不可能理解大人世界的复杂和艰难,就当为了孩子吧,惠芬,请你转交给他。”
白惠芬望着那一叠厚厚的上面还系着蝴蝶结的图书,很想哭,眼泪已经蓄在泪腺的最末端,下一步便如洪流倾泻,但很快,那份生冷生冷的感觉,再次席卷过全身,眼泪在最后一刻,集结成冰,化作一丝清阴冰冷的冷笑,接过书,“吡——”她拿出一本,缓缓地撕作两半,“吡——”又拿出一本......直到,将它们化作一片片彩色的纸片,象满天飞舞的雪花一般,抛洒在林飞的面前......
“你走吧,从今天起,小志没有你这个爸爸的存在。”她冷冷地,象刀子一般地吐出话来。
小志醒了。
“妈妈。”他叫着,象只受惊的兔子般躲进白惠芬的怀里。
“妈妈,你在哭么?”小志吓坏了。
“妈妈没有哭。”白惠芬紧紧地搂着他。“只是灰尘进了眼睛。”
“妈妈不哭不哭,小志不惹妈妈生气了。”
“小志没有惹妈妈生气......小志最乖了。”
“可是......妈妈,你为什么眼泪流个不停。”
白惠芬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她紧紧地拥住怀里的孩子。这是她的生命,她的心,她的全部啊。窗外,那个男人已经远离,十年的情意,只在一瞬间化为乌有,仿佛这一切根本不存在过,她,小志,这两个曾经在他生命中那么重要的人,这两个曾经为他而生的人,此刻,就这样,永远地被抛离在这个空荡荡的房间里,任凭黑暗吞噬,她,与怀里这个弱小的孩子,将真正地独自去面对这个残忍的世界,未来,象个未知的恶魔,张口等着她们,唯有这双纤细的臂膀,为小志挡风遮雨。她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她真的不知道,这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妈妈,爸爸不会回来了是么?”小志躲在她的怀里,忽然用一种从未有过的伤感语气,低低地问。
李想今天特意早早的下班,她路过菜场的时候,买了一条三斤重的黑鱼,晚上下厨给林飞做他最爱的酸菜鱼。
她兴匆匆地进门,准备给林飞一个惊喜,但却发现屋子里黑黑的,空空的,她有些失落,“他去哪儿了?平时这会他应该已经下班了。”“他今天甚至都没有来接自己。”她开始胡思乱想了。“他还在生气吧。”她默默对自己说。“不过他会回来的,等下好好向他解释。”
她卷起袖子进了厨房,洗菜,切菜,下锅,淘米,她发现自己好久没有做过这些事了,今天做着有些生疏,有些手忙脚乱,期间,杀鱼的时候还不小心被菜刀割伤了手指。她冲进了卧室找到了创口贴,总算是止住了血。她抬头看了下钟,已经七点了,可是林飞还没有回来。
等到所有的菜上桌,她终于空闲下来,拿走围裙坐在桌边,忽然发现无事可做,无事可做的时候,便显得时间过得特别慢,她抬头看着时钟一格格的爬过,觉得每一秒都很难熬。
她试着给林飞打了电话,但电话始终没有人接听。她只得悻悻地坐下,看着桌上的菜一点点冷去。她冲进厨房,将所有的菜又热了一遍,然后又给林飞打了个电话,仍然无人接听,所以,她又只得在桌边重新坐下发着呆。
到了这时候,人一般就会开始胡思乱想。各种担忧和假想如潮水般涌进脑子,又如乱针密密扎着神经,让人坐立不安。
好几次,她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想冲出门去找林飞,甚至有要去派出所报案的冲动,她俳徊在桌子和大门的距离中,不停地站起坐下,坐下站起,到后来,象个钟摆似的来回走动,她觉得自己的神经愈来愈绷紧,仿佛只稍稍一用力就瞬间断了似的。
就在那么离崩溃的最后一刻,林飞回来了。
他垂头丧气地站在门口,身上带着夜晚的湿气,仿佛蔫了的树叶。
她象是被人刺了下似的从位子上跳了起来,几乎是扑进了林飞的怀抱。
“为什么不接电话?你快急死我了。”她带着哭腔不停地从嘴皮子里蹦出话来。
“我有点事。”林飞木无表情地回答。
“你至少应该接个电话,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么?”
“手机开静音,没听见。”
“你没吃饭吧,瞧我做了什么?”她将他拉到了饭桌前,硬生生地将他按进座位。“酸菜鱼,你不会忘记我的手艺了吧。来尝一口。”
林飞避开她的奉承, “我累了,想先休息了。”
他说着,似有似无地叹着气,神情恍惚地朝屋内走去。
临近门边,身影又停下,冷冷地抛出一句:
“还有,那支里面包着一万元美金的钢笔,麻烦你还给胡老板吧。”
门就这么生冷地随着一声“砰”重重地关上了。
屋子里徒然安静下来,时针的滴答渐渐变的清晰。
她空荡荡地站着,忽然,就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