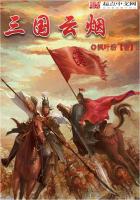此次文会较为仓促,因此前来参加的大多都是附近江宁、溧水、当涂三县的世家大族。不过,此处接近前朝皇宫,可以说江淮地区真正的豪门基本上都已经到场了。
不时有人凑过来与陶德阳攀谈,却都不约而同地无视了范遥。
范遥百无聊赖地离开座位,转身来到窗边,双手撑着护栏,向窗外眺望。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绿色,山上草木茂盛,盛夏时节枝繁叶茂,给炎炎夏日遮出了一处清凉。石头山西南麓,江水长年累月冲击拍打的缘故,形成高耸的悬崖峭壁。
俯瞰奔腾的江水,江面碧波荡漾,浪花不经意间反射明媚的阳光装点出朵朵银色的波纹,整条长江如同身披银色铠甲的长龙一般,沿着河道永不停息地东去。偶尔猛烈拍打在峭壁上的巨浪似乎传来阵阵轰鸣。
江上有一叶扁舟,船头一位船夫正在高声唱着什么,距离太远了听不真切。不知是何处的船家在江上苦苦谋生,亦或是哪里的渔夫在捕捞这一季的收获?
过了一会儿。天空猛然间暗了下来,天地之间似乎有什么东西要出现了,山顶的风也大了起来,楼里四处通风,在盛夏时节却让人感到一阵寒意。江水更加急切了,小舟随着浪花忽上忽下,若隐若现,范遥手心替船家捏了一把汗,却也只能站在楼里干着急。
天空一道亮光闪过,随即传来一声雷鸣,豆大的雨点倾盆而下,雨势不同往日,显得更加急躁且集中,视线变得模糊了,小舟已经看不见了,风更大了,似乎要将人吹走,范遥手紧紧抓着栏杆。从楼外跑进来几位落汤鸡,看那打扮显然是外出赏景取材的各位才子。
雨水顺着风向从窗外落进楼内,打湿了前襟。范遥往后微微退了一步,环顾四周,所有人都紧紧裹着衣物,显然这场突如其来的疾风骤雨让大家都猝不及防。杨昭不为所动,依旧淡定地坐在主位抬头看着楼顶,似乎在考虑些什么。柳抃不知所踪,陶德阳似乎已经睡着了,趴在案几上,韩二公子与他带来的文士交头接耳。
这场雨来得快去得也快,盏茶的功夫,雨势骤然停止了,风势也弱了下去,太阳重新从云层透出了光。温暖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众人纷纷或靠窗,或出楼,有的取景,有的只是为了祛除寒意。
范遥的目光在江面上逡巡,却不知船家是否安好。一时之间没有看到船影,范遥心里正要着急。却听到隐隐绰绰似乎传来了歌声,循声望去,范遥会心一笑,放下心思。
“如何?遥弟似乎佳文在腹,胸有成竹啊。”陶德阳见范遥回到了座位上,抬头问道。
“德阳兄才是,一直稳如泰山。”
陶德阳微微一笑也不否认。范遥不由多看了他一眼。
……
“众所周知,编著县志少不了写景,写人,写物,因此,以这三个为题,各位请各创作一篇诗文,每个家族的代表需展示三个方面的诗文至少一篇。”杨广站在二楼,大声向楼下宣读文会题目。
“写景,写人,写物诗或文各一篇?为何范围如此宽泛?”陶德阳疑惑的看着公布的题目,“如此岂不是可以随意默写出宿作?”
“恐怕就是为了让一些人事先做好的文章派上用场。”范遥看着对面韩二少含笑的嘴角和身边奋笔疾书的文士说道。
陶德阳点了点头,“如此下作之事我陶家不屑为之。”
范遥动了动嘴,刚想说写物不如自己默写一边爱莲说,结果被陶德阳一句话堵了下去。
范遥不由腹诽几句猪队友,嘴上却也只好应和。
“写人那一首诗交给我吧,写物就托付给你了。至于写景……为兄实在是不擅长写景,几次三番想有所突破,结果落得个被爷爷禁足的下场。”陶德阳一脸真诚地对范遥说道,“刚才为兄想破了脑袋也没有什么好句子。”
范遥一脸卧槽地呆呆地看着陶德阳,想从后者脸上看出一些不好意思出来,结果范遥失望了,陶德阳一脸理所当然的样子。原来刚才趴着是因为想的头疼吗?我是来抱大腿的啊!怎么就莫名其妙成了大腿呢?说好的要证明自己呢?这就托付给我了?
“遥弟莫要用这种眼神看着为兄,这是爷爷的决定,扬长避短,献丑不如藏拙。你的写物笔力明显高于我,就不必自谦了。写人方面为兄尚有几分自信。”陶德阳叹了一口气,“还是爷爷看得准啊。为兄本来以为县志也就写写人物,没想到居然还会考查描写景物的笔力。”
范遥嘴角抽搐,却也不得不承认了这个事实,有那么一瞬间认为陶德阳可靠真是太大意了,一路上那个逗比才是他的原貌吧?范遥认命地叹了一口气,开始搜肠刮肚地思考契合的诗文,被陶德阳的发言堵住了退路,随便找一首已经不可能了。
……
“伯施。依你之见,谁家能拔得头筹?”二楼,杨广扶着护栏边看着楼下众人的姿态,兴致勃勃地对身边的人问道。
“谁胜谁负,本与王府无关,殿下何必参与其中。徒遭陶家不满。”被问者不咸不淡地回道。
杨广碰了个软钉子,沉默一会儿,满含深意地说道:“伯施觉得现在还不到时候?”
“若是王府堂堂正正地取胜也无不可。”伯施答非所问,深深的看了一眼杨广。
杨广有些心虚的干笑一声,“顾言之才伯施你也不是不知,何况昭儿也有几分才气,想来不会有什么差错。”
“天下才学之士多如牛毛,我等蒙殿下赏识才入得王府,还望殿下不可小瞧天下文士。尚且不知陶家二公子深居简出,其才学如何,今日是否有惊世之作。但既然殿下将评判之事托于微臣,臣自当公正评判。”
“理应如此!”杨广赞了一句,看向陶家的位置,见范遥和陶适正在讨论什么,目光微微一沉,真正要注意的,是那个小子啊。昭儿回来说陶家那个老头子不顾礼节当场收了范遥为弟子。今日就让此人同陶德阳一起前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也不知这小子的文采如何出众,当得起陶家老头子如此厚望。
杨广回想小屋里的密谈,瞳孔微微一缩,十四岁的孩子,仅凭蛛丝马迹就能看得如此透彻,握着栏杆的双手渐渐收紧了,若是不能为我所用……。
正在和陶德阳争论甜豆腐脑和咸豆腐脑哪个好吃范遥没由来地感到一阵恶寒,环顾四周,除了不知何时回到楼内的柳抃以外见没有什么异样,所有人都在深思题目的样子,有些已经开始动笔写下自己的得意之作了。
范遥失去了争论的兴趣,摆一摆手,“你乐意吃什么就吃什么吧,吃死活该。”说完就靠在椅背上假寐。
“你可是要负责写两首诗文,为何如此悠闲?”陶德阳奇怪的问道。
“小弟胸中有丘壑,肚内有文章,张口即来,何必苦思冥想。”范遥有些心虚,只能凭借吹牛壮壮胆气。
陶德阳随意地哦了一声,显然是不信,托腮开始构思起自己的诗句来。
……
“遥弟!遥弟!我当你是闭目沉思,怎的真的睡着了?”范遥睡得迷迷糊糊,隐约感到有人在推搡自己。
“怎么了怎么了?”范遥睁开朦胧的双眼,疑惑的问道。
“什么怎么了。过去了半个时辰了。马上就要有人来取第一题的答卷了。写景的诗词可有了?”陶德阳催问道。
“就这事啊,小弟自然已经准备好了。”范遥摇了摇脑袋,清醒了一些。去过不知何时送来的笔墨纸砚,挥毫写下: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如何?”范遥放下笔问道。
“意境不错,但是贤弟啊,曲子词难登大雅之堂。”陶德阳无奈地说道,“也罢,没有时间了,就这样吧。”说完就将宣纸递给了眼前的文吏。
范遥一愣,原以为随便写一首就行,才回想起词盛行的时代是宋朝。无奈宣纸已经被楼上下来的文吏糊上名字收走了。
一拍脑袋,又取过一张宣纸,洋洋洒洒写下诗句,在右下角标上陶德阳,离席追上文吏的脚步,将纸塞在了他的怀里:“这么不小心,陶家有两份呢。”
待范遥回到座位上,陶德阳好奇的问道,“又写了什么?”
“稍后自有分晓。”范遥神秘地说道。
“莫不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又觅得了什么佳句?”
范遥微笑不语。目光随着文吏移动,到了柳抃那里时似乎还有什么小动作,杨昭似乎也在说着什么。范遥一挑眉,猛地起身。
“怎么了?”陶德阳奇怪的问道。
由于角度原因还是看不真切,范遥踮起了脚尖,那个文吏注意到了这里的情况,回头看了范遥一眼。举着木盘匆匆上楼。
“呐,德阳兄,你觉得杨广……晋王殿下是个怎么样的人?”范遥坐下后靠在椅背上,看着二楼的隔板问道。
“晋王殿下称赞一句贤王也不为过。你这是什么意思?”陶德阳心里一动,追问道。
“晋王殿下会为了这次文会打压陶家而舞弊么?”
“不至于吧?我陶家并没有死死得罪晋王府,近几年来对王府也算言听计从,从未有过大的分歧,晋王一向礼贤下士,勤政爱民。爷爷也说了,晋王有可能借此次文会尝试统领扬州文坛风向,但是失败了也不会有损晋王府威严……用舞弊来达到目的?何必如此?这恐怕不太可能。”陶德阳思考了一会儿说道。
“嗬……”深知杨广历史真面目的范遥从喉咙里发出一声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