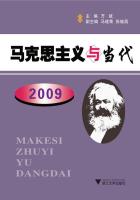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用一切不幸来威胁理性的憎恨者。但他们能保护那些热爱理性的人幸免于难吗?还有一个更令人忧虑的问题:之所以应当爱理性,是因为假如不爱它的话,那么就必须由此而受到报复,或者应当去无私地爱它,而不去预测。它将带来的是高兴还是悲伤——仅仅是因为它是理性吗?显然,柏拉图是远非大公无私的,否则他不会以厄难相威胁。而他会真诚地宣布,就像圣训一样:全心全意地爱理性——无论你将会因此而不幸或者走运。理性要求爱自己,并未提出任何袒护辩解的理由,因为它本身就是辩解的本源,并且还是一切辩解理由中的唯一本源。但是柏拉图并未走得“如此之远”,显然,苏格拉底也没有走得如此之远。在提出最大的不幸就是成为理性的憎恨者的那篇《斐多篇》中,叙述了当苏格拉底看清了在青年时代如此诱惑他的阿那克萨戈拉的(理性),并非给他提供“最美好”的东西时,就与自己的导师一刀两断了。“最美好”应当超越一切,“最美好”应当在世界上主宰一切。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在爱理性之前应当弄清楚,它果真能给人提供最美好的东西,这样就不能预先知道是应该喜爱理性还是仇恨理性。它提供出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就喜爱它,否则——就不会喜爱它。假如它招致任何什么别的或者糟糕透顶的东西——我们就会憎恨和拒绝它。我们会喜爱它永恒的敌人——悖论、荒谬。无论是柏拉图,还是苏格拉底到底都没有把问题提得如此尖锐。尽管阿那克萨戈拉的uaue(理性)并未使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如愿以偿,他们仍然一再赞颂理性,不过,他们不再赞美阿那克萨戈拉。任何力量也不能使他们与理性分道扬镳。
然而理性有时给他们带来真理,可真理与“最美好”的相似之处简直微乎其微,甚至相反,真理隐含有许多不好的、极为糟糕的东西。仅以柏拉图的自白为例(《蒂麦欧篇》,48A),“我们的世界源于理性与必然性的混和之中”;或者还有另一种形式的论断:“应当识别两种因果性——必然的和神秘的因果性”(同上书,68E.)。假如再提一下理性特别确信自己的正确性,不断地教诲柏拉图说,就是神祗也不能与必然性争胜负(《普罗泰哥拉篇》,345),那么对处于理性支配之下的幸福的指望,就会在现实中成为空中楼阁。理性部分地支配着世界,它也在某种程度上维护神祗;然而无论是它本身还是为它所赞颂的神祗都同样毫无力量去反对必然性。而且软弱无力是永远如此的:理性确信这一点,不允许任何人怀疑自己的知识,因此,就像丧失理智一样,完全彻底和斩钉截铁地拒绝与必然性进行斗争的任何试图。
但是要知道,无论是神还是人,都无力反对必然性,必然性能带来无数的不幸!当然,理性知道这一点,它也把这一点暗示给了人——不过,它在这里突然从自己身上卸下了全部责任,它不愿意谈论这一点。它仍然继续要求人喜爱它,虽然结果是喜爱理性之人可能像憎恨理性之人一样不幸,或许要更为不幸。因而,柏拉图的著名格言在与经验材料当面对质时终究显得极为软弱无力,或者甚至几乎完全毫无根据。理性,就像但丁的厄洛斯,不是神祗,而是源自丌opoā(财富)和euca(贫穷)的恶魔。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此没有高谈阔论一番,相反,他们千方百计地使审视的思维不去探寻理性的起源。他们为了摆脱必然性,发明了著名的Icaeap(卡塔西斯)。什么是Icaeap?柏拉图解释道:“卡塔西斯就在于把灵魂与肉体尽可能分离开来……无论是现在在这里还是以后,尽可能让灵魂摆脱肉体的锁链单独存在。”
这就是能使人、神灵及其理性同不知道也不愿知道理性的必然性对立的全部东西。任何人也无权对肉体和世界发号施令。就是说,这里是无事可干:让世界存在吧,像它想的那样或应该的那样,我们会通晓并也教会其他人在没有世界和没有属于这一世界的肉体的条件下行事。
我们宣告这一点,是作为我们最伟大的胜利,是作为对所向无敌、连神也屈从的必然性的胜利。或者最好是说,神只是借助于理性所想到的诡计才可能战胜必然性。柏拉图式的斯多葛学者爱比克泰德,尽管人们通常把他的心地善良称为天真,但他也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用他的话说,宙斯告诉克利齐普:“如果可能的话,我会让你完全支配自己的肉体和一切外部事物。但是实不相瞒,我只是让你暂时使用这一切。因为我不能让这一切归你所有,为此我让你分享我们(神祗)的一部分——决定干还是不干,想要还是不想要的能力。一句话,就是使用观念的能力。”当然,现代人很难设想宙斯会开恩同克利齐普交谈。
但是,也没有多大必要提到宙斯。要知道,他自己也不得不从某种难以猜测的本源里获取他对克利齐普所宣称的真理,即“不可能”给人以外部事物的所有权。似乎不是宙斯在教诲克利齐普,而是克利齐普在教诲宙斯,因为克利齐普本人知道,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没有任何必要因为询问而惹神灵厌烦自己。假如宙斯同克利齐普进行了交谈,并且尝试把自己的见解与他的关于可能与不可能的见解相比较,他是不会听从它的——可是,假如听从了,那么也不会相信它的:难道神灵高居于真理之上?难道真理不是与一切有思维的生物平起平坐?
无论是人还是恶魔,也无论是神灵还是天使——大家都有平等的权利,或者更确切些说,在真理面前它们都同样没有权利,而真理完全听命于理性。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懂得,不仅有神灵,而且还有必然性在驾驭世界。任何人也不能在必然性之上发号施令,他们是既为凡人,也为神祗发明了真理。宙斯威力无穷——任何人也不敢对这一点提出异议。然而,他又不是万能的,他作为有理性的生物也会不亚于克利齐普甚至克利齐普的导师——苏格拉底,也不能不崇拜真理并成为zctaoXoyos(理性的仇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适应生存条件的能力赋予了人。换言之,既然一切外在事物中包括肉体,可能只是让人暂时使用,既然这已不能有任何变动——尽管还凑合,甚至还不错,假如能按另一种方式安排一切——那么就让它这样吧。要知道人有“神灵”的惠赐:选择要与不要的自由。他完全可以不去力争自己的肉体和外在事物的所有权,他也可以只是去争取暂时使用它们。那时一切都会立刻时来运转,实际上理性也有权自夸,喜爱并听从它的人将幸福地生活在世界上,厄难也仅成为理性的仇敌,不会有更大的灾难。
这就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斯多葛派哲学家在其著名理论里把它表述为:“事物”本身不具有价值,我们可随意认为想要的东西是有价值的还是毫无价值的,自主的伦理学就发轫于此。伦理学是自己赋予自己以规律。它能承认任何东西(当然,也得随它所欲)是有价值的、重要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也能承认任何东西是无价值的、不重要的,或者是毫无用处的。任何人,就连神灵们也不能与自主伦理学进行斗争。一切都应该俯首听命于它,一切都应该向它顶礼膜拜。
伦理学的“你应当”产生于必然性告诉人和神“你不能”的那一时刻。
生育伦理学和必然性的是同一对父母(富裕)和Tuvia(贫穷)。
世界上存在的一切都是opo(富裕)和euvia(贫穷)的产物。就连神灵也来自它们。因此说实在话,神灵是不存在的,而且是任何时候都不存在的;存在着的只是魔鬼。理性就是这样教诲的,理性的视觉和聪慧的视觉以及思辨所启示的就是这个。假如理性本身也是源自opo(富裕)和rguvia(和贫穷),那么它是否可以启示其他的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