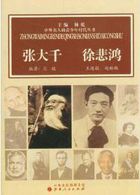例如,童年所存在的疑惑远多于许多别的现象。童年的主体性所表现出的任性和混乱,会拒不接受理性的控制。我们能“了解”儿童,或能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解释,却不能令他们保持不变,也不能排除他们介入成人生活的随意性。并且,正是这种在构成成人———儿童的差异中产生的持续的他者性,是理解儿童的必备条件。因此,我们认为,儿童是成为社会秩序和社会再生产的潜在威胁和挑战。但是,这种儿童观不仅受到现代性或学术争论单方面的影响,而且,我们对儿童潜在所具有破坏性的日常研究策略既是一系列现代性话语的具体体现,又受到早期思想传统的影响。在本章中,我们所描述的童年的前社会学话语是由很多牢固且传统的智慧组成,这些智慧塑造着我们的儿童观,甚至在理论中也塑造着我们的儿童观。在下一章中,我们试图通过考察社会学的反思转向(turntorelexvity)所提供的理论方法来呈现这种话语的转向。童年的日常话语寻求解释童年的“真相”,而本书中提供的理论方法则将会解释和解构那些已有的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童年“真相”。
接下来,让我们开始对童年的前社会学话语进行概述。我们期望这些但是,我们认为任何一种关于社会的话语都是具体的、与情境有关的。
能提供一个分析性的分类学,据此,读者能开始以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日益增长的童年研究。
前社会学中的儿童
这个宽泛的类别包含了一些被遗忘的历史。它包括常识、古典哲学、发展心理学(非常有影响的学科)和精神分析的领域。这一组理论模式的共同原则是,它们都基于这样一个观点:童年外在于儿童所处的社会环境或是与儿童所处的社会环境不一致的。更具体来说,这些模式没有提到任何社会结构的作用。
邪恶的儿童
虽然我们能找到的第一个含有“儿童”前社会学话语来源于更早的历史时期,但在当代犯罪学、公共道德和针对教育学实践的争论中也能找到类似话语。它假定邪恶(evil)、堕落(corruption)、自私(baseness)是构成“儿童”的主要元素。在童年这一背景下,儿童的他者性得到处理,童年因此要接受那些对他们的坏性格的约束的塑造。更过分的是,这些坏性格要被纪律和惩罚的手段所驱除。根据福柯的分析和推测的方法所形成的连带和社会控制的隐语,对儿童正确的训练会产生驯服的成年人身体。驯服的身体是良好公民、顺应社会秩序的社会成员,在这一经典模型中(但不包括内部或内部生活的理论),儿童身体成为童年的主要场所。正如福柯(1977,第136页)所说:“古典时期发现了身体作为权力的目标。不难找到将注意力放在身体上的信号———被操纵、被塑造、被训练的身体,使身体遵从、回应,并变得熟练,增长力量。”
邪恶儿童的形象能在亚当原罪论中找到其神话学基础。原罪论提出,儿童作为一个任性的物质能量来到世界,但在这个世界里他们的任性被认为既是普遍又是基本的,却不被认为是故意的。相反,儿童是恶魔般的,如果忽视他们或对他们关注不够,他们暗藏的潜在的黑暗力量就会被激发,就会使得他们偏离文明生活的正路。
这些黑暗力量的解放会威胁儿童自身的幸福,这是不言自明的。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也会威胁成人集体的稳定,因为这种社会秩序是儿童以后将要追求的。这样一种原始力量的神话学一直是当代文学和电影的一个有力的主题,例如在《蝇王》(Golding,1958)、《戴茅斯的孩子们》(Trevor,1976)和电影《驱魔人》中就是如此———并且,我们认为,在当代更为常见的公众对于对儿童的谋杀和欺侮能力的理解中也体现了这一主题。这些共同表现出一种酒神式(Dionysian)的神话学:
儿童是酒神式的,这体现在它热爱享乐、它庆祝自我满足,它在面对任何阻碍它获得满足的客体甚至是主体时,都表现得完全地难以满足。童年这种侵入性的嘈杂表现了一组专一的唯我论的需求,与这些需求相比,其他所有的兴趣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其他所有的存在都成为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Jenks,1995a,第182页)。
所以,贯穿这种话语的是一种关切,这种关切认为这些邪恶的儿童应该避开危险场所,以免陷入不良的环境,养成坏习惯和变得懒惰;认为这些儿童不仅仅应该被监视,还应该被监听。“危险的场所”———从商场到功能失调的家庭,这些场所与儿童身体内(或精神)已存在的邪恶力量的释放起到共谋作用。正是这些凸显出对儿童进行限制的需要。
邪恶儿童的哲学前提可以在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的著作中找到。尽管他没有解释童年的条件,但他通过他非常著名的“行动者”(humanactor)概念已经含蓄地对童年的内容进行了具体阐述。霍布斯最初的学术训练是清教徒式的,他认同良好行为是最为重要的这一观点。
他在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Leviathan)中,在谈到社会秩序的连续性问题时表现出对专制主义强烈的支持。君主的权力以及类似的父母的权力,是凌驾于百姓或儿童之上的绝对权力,百姓和儿童既没有权利,也没有权力。父母权力的来源是知识,儿童只有通过自身逐渐成长为父母才能获得知识。国家和父母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个体通过融入社会或家庭将自己从越轨行为中“拯救”出来。如果没有父母的限制,儿童的生活就会变成无政府主义的生活。
尽管这些论点起源于17世纪,但就当前大众对于“儿童”的关注而言,它们仍然相当中肯。“家庭”破裂和“家庭价值”的缺失被认为是儿童行为出轨的原因,或是当前儿童生活“孤独、贫穷、恶劣、粗暴和短暂”与不受控制的原因。《旧约全书》印证了这些看法并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邪恶儿童的形象。父母、教父母和代理父母的指导令儿童通过严肃的方式了解了上帝(almighty),这样的指导也被证明是儿童养育的一项持久的传统。如希普曼(Shipman,1972)所指出的,婴儿死亡率的急剧下降和现代性带来的不可逆转的世俗化过程降低了关于婴儿蒙恩的集体焦虑。阿里耶斯(1962)认为,儿童在16世纪被描写为弱小的标志,它们易受到邪恶的影响,几乎没有决心,易分心和堕落。这种信念导致了“娇惯”的广泛实践,“娇惯”即是通过限制儿童的身体,对他们原本任性的倾向进行物质控制。
但是,娇惯也可以被看作具有教育意义,是一种限制儿童的需求和期待的教养风格。它是对年轻人的一种疏远的、严格的身体指示。随着邪恶儿童模式在16世纪的形成,这种社会化实践采用了一种竞争的形式,成人对待儿童的方式,是一种人“打破”或“驯服”家畜,将它们的自然属性整合进成人的文化世界的方式,儿童与成人间保持着斗争关系(Stone,1979)。伴随16、17世纪的清教徒主义而来的对更大改革的热忱中,儿童养育中的这种粗鲁甚至粗暴获得了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基础,并且,在最残酷的社会运动中,对主体(儿童)施加的控制和限制被认为是为他们自身着想。清教徒主义认定,为了拯救孩子,必须使用棍棒。同样确定的是,儿童应该为自己所受到的这种待遇表示感激。尽管清教徒主义作为一种正式教派已近消失,但清教徒道德的要素却仍伴随着新教会的热忱延续到19世纪,在发起了“济贫法”和“禁酒运动”的同时,仍然认为儿童需要得到纠正。这一时期许多文学作品都将邪恶的儿童作为一种继续支持反民主国家的过时伪善的道德的象征。例如,在狄更斯的小说中,这种对儿童的制度化的暴力被描绘成一个道德限制,并且,我们还能在20世纪晚期要求儿童接受“新兵训练营”和“短刑期、严纪律、强阻吓”并认为其对儿童和成人将来都有好处的做法中发现这种限制的政治学。
天真的儿童
童年的第二种前社会学模式是天真的儿童,柯文尼(Coveney,1957)在其重要著作中将其作为邪恶儿童模式的对立面而提出,概括了我们所想象的现代的、西方的童年。在布莱克(Blake)和华兹华斯(Worldsworth)所构建的浪漫形象中,可以发现我们对儿童的态度以及对与儿童相关的政策和规则的期望的大众标准的来源。他们所描述的婴儿内心纯净,像天使一般,未被他们所踏入的世界所腐蚀。尽管认为这一观点是自发形成的会让人感到高兴,但作为现代性文明进程的一部分,和人类文明中所有重要的步骤一样,这一观点也有一位缔造者,那就是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卢梭是一位个人自由的先驱倡导者,他在其1762年发表的《社会契约论》中以这样的话语开头:“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却无不处于枷锁之中。自以为是他人主人的人,只不过比他人更是奴隶。”在《爱弥儿》中,他也以一个相似的观点开头:“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
那么,儿童与生俱来有着善良和清澈的视野。他们天生的特质是构成明日社会之基础,也是我们都应学习的东西;他们代表一种已被丢失或被忘记的事物,因此值得保护(并且易于感情化)。确实,卢梭试图消除所有关于原罪的顾虑,主张将教育儿童当作一个最终到达优雅的惩罚过程,崇拜(idolizeorworship)儿童带到世界来的内在价值令我们更为受益。
因此,卢梭不仅注入了天真的儿童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儿童特性的问题。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个问题处于当代理论的核心。在《爱弥儿》中,儿童被提升为人的身份,是有需要、欲望甚至权利的特定阶层。正是这种人格化为当代对儿童的关注铺平了道路。正如罗宾逊(Robertson ,1976,第407页)所说:
如果启蒙时代的哲学为18世纪欧洲带来对人类幸福可能性的新的信心,那么必须要感谢卢梭唤起了对儿童需要的关注。他是历史上首次令很多人相信童年值得聪明的成人来关注,并激发了对成长过程而非仅仅是结果的兴趣。儿童的教育是当时正在形成的学术兴趣的一部分,并在当时的学术趋势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20世纪的思想遗产是郑重承认了儿童不是消极特性的集合体,或是等待长大的不完整的人,他们就是他们自己。作为父母和教育者,我们有义务用一种不让周遭的暴力和丑恶破坏他们原初的天真的方式来养育他们。但是,我们同样注意到成人———儿童关系中被注入了责任的观念,这种责任必须与卢梭所提倡的儿童自由相协调。如果童年的天真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来呵护,那么我们有必要建立大众承认的对待儿童的标准。所有成人在认识到自身的意向和能力的同时,还必须承担对儿童的责任。儿童不能再受到日复一日(routinely)的不公正对待,也不能让他们随心所欲。在这种话语中,儿童成为主体。
因此,当代对于儿童教育的关注开始于卢梭,开始于一个在鼓励、协助、支持和促进下得到认可的童年。简克斯(Jenks,1996a,第73页)将这一模式比作阿波罗神话学:
阿波罗式的儿童,太阳和光明的孩子,诗歌和美丽的制造者?这样的儿童玩耍嬉笑、微笑大笑,既是自然的又受到我们不断地鼓励。
我们不能纵容他们的眼泪和脾气,我们想要的只是来自他们光芒的启迪。这是耶诞前或偷吃禁果前的人类。在这个模式中,我们尊重和赞美儿童,并致力于揭示儿童的崭新和独特。我们去除了塑造单一性的种种约束,以一种浪漫的视角来发掘人的特殊性。这样一种思想在所有儿童中心的学习和特殊教育中都有体现,从蒙台梭利、《普劳登报告》、尼尔、《瓦那克报告》,以及过去30年来许多小学教育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