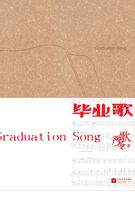【黑夜是睡眠的时候,
做梦很正常;
白天睡眠就不正常,
做梦当然更不正常。
然而只有在不正常中,
才发生这些故事。
梦已经逝去,
只留下一些淡淡的记忆。】
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
(俄)赫尔岑
艰难跋涉
一辆接站的篷布小卡车把我送进了S工学院大门。
下了车,我已置身在一个新的环境,很难说清心中是一种什么滋味。我提着我所有的行李——一个帆布包和一个老布(农民自己纺纱织的布,但并没有贵州蜡染的风采)包袱,跟着接站的同学向新生报到处走去。当我交出录取通知书、粮户关系后,便获知分配在金属压力加工专业二班,并发给我一只海碗和一把折叠椅(椅背上写着我的名字),安排到12栋3号宿舍住宿。
有必要交代一下海碗。海是大的意思,自然这是一只粗瓷大碗。我是浙江人,我们习惯用小碗吃饭,即便上了中学为了方便起见买了只搪瓷缸吃饭,最多也只能盛二三两米饭。然而学院发给我这只海碗大约能打八两米饭,不能不使我发了一阵呆,于是我恍然大悟北方人长得粗壮结实的原因了。等到吃饭时我才知道大家用这只碗既打饭又打菜,在当时粮食不足人们不能奢侈地吃几样菜时确是很方便了。再交代一下椅子。大学生上课不像中学生那样固定在一个教室里,有时在大教室上课,有时在礼堂(兼饭厅)听报告,有时到实验室做实验,有时回宿舍自习,随时带上,实在方便。
当我走进宿舍时,别的同学都到了,原来他们都是提前来到这个向往已久的城市的,其中有班长郭亦武,山东人;谭一声,上海人;叶斌,江苏人;等等。真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后来我才知道,全宿舍七个人除我之外都是出身较好的,充分体现了学校为工农开门的政策。
宿舍有四张双层床,住七个人,留下一个铺位是给大家放行李的。我便睡在靠门口的那张床的上铺,自然是六个同学拣剩的位置了。宿舍是平房,没有水,更没有厕所,但有暖气,这样的条件对我这样的乡下孩子来说,无疑是天堂了。
晚上躺在床上,思绪万千。去年招生25万,今年招生10.7万,被录取者,都是幸运儿了。像我这样出身的在反右之后能进大学,更是幸运儿了。于是我认识到当初太幼稚了,偏要报考什么名牌大学。幸亏这第九志愿收留了我,要不,随便给我定个政治条件不合格不录取,回到农村从事光荣而报酬极微的繁重的体力劳动,有什么话说!认识到这一点,是极大的安慰。于是我决心以优异的成绩来报效祖国。
我们的教室在2号楼,楼前的几十米席棚正是全院的大字报栏。虽然开学前已经冲刷干净了,但仍能使人想象到不久前这里曾是硝烟弥漫的战场,有几百名大大小小的右派在这里一触即溃,成了人民的敌人。这些从教师中学生中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此刻正在学校从事光荣的体力劳动,如搬运设备、打扫卫生等等,以改造思想。那些学生右派,比我大一两岁,显得很文雅,遗憾的是没有看到这些文雅的书生“疯狂进攻”和“负隅顽抗”的姿态。因为持刀枪杀人者都比较形象,用笔杆子杀人的实在缺乏形象。尽管如此,我还是写了一首《我们胜利了》的诗发表在院刊上,表示我和这些“丧心病狂”的敌人划清界限。
开学典礼上刘教务长的讲话使我难以忘怀。教务长中等身材,头已谢顶,略显肥胖,显出一种大学者风度。当时便有人告诉我他是著名的力学家。他把毛主席称作毛泽东先生,这是我解放八年来第一次听到的。他说毛泽东先生说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将出现一个文化高潮。他要我们去迎接这个高潮。他还说广播这玩意儿干扰学习,以后不要放了,又让我吃了一惊。
开学典礼结束后我们夹着椅子回到教室,辅导员马丁兵立即给我们消毒。他说教务长是全国著名的专家,一级教授,保护对象。如果是一般人,早就打成右派了。他的讲话纯粹是胡说八道,同学们不要听他的。
大学生是善于思考的。自然,智商并不低的我也会思考:既然教务长是胡说八道,那为什么还要让他讲呢?他称毛泽东先生,这不是不尊敬我们的领袖吗?他说不要放广播,这不是和我们争夺宣传阵地吗?他的这次讲话,是不折不扣的右派言论。右派是客观存在,他实实在在是个右派,但为什么保了便不是了?
这些问题我好长时间没有想通。
接着,学院反右扫尾工程开始了。第一个回合便是批斗大右派刘飞。刘飞是留苏预备生,是尖子学生。偏偏在出国前补习一年俄语的最后阶段,他攻击了统购统销政策,他说农民把粮食卖光了,饿肚子了,还饿死了人。于是他被取消了留苏的资格。批斗会上,一位工农速中的同学发言慷慨激昂。他说:“刘飞,你出身贫苦,是共产党救了你,是共产党培养你上了中学又上大学,你不思图报,忘恩负义,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竟敢攻击党,诬蔑党的政策,成了十恶不赦的大右派,要不是党的政策约束我,我真想抽你的筋,扒你的皮!”接着,他便高呼口号:“打倒大右派刘飞!”“刘飞他不投降,便叫他灭亡!”于是大家便跟着他高呼。场面惊心动魄、叫人不寒而栗。
说实话,我生活在农村,卖“余粮”的事情很清楚的。农村把每户的田都做了三定:定产量、定公粮、定口粮,然后算出余粮。公式是:
产量-公粮-口粮=余粮
在秋收后,政府便按三定收购,公粮必须交,余粮必须卖。
产量搞浮夸,定得很高,实际很低,口粮便成纸上的数字了。饿死人的事是确实的,但在30年后才有所披露。刘飞说了实话,便成了右派;那些说假话的,却成了左派。我什么也没有说,自然是中间派了。
扫尾工程的第二个回合是继续反右。辅导员说:机械系还有两个右派没有挖出来(所谓没有挖出来是指党委已经批了,但尚未经过批斗让他们自己承认)。自然,我们新生也要参加这个攻坚战了。那天,我们停了课,吃过早饭便夹着椅子排队进会议室。因为批斗右派比上课重要得多,右派不铲除,国家要变色,学了有什么用!会议室墙上贴着白纸黑字“把右派分子王××、李××揪出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等大标语。还把王××李××的名字颠倒着写,气氛十分严肃、紧张。
批斗大会开始,先让王××同学检查。王××自然避重就轻地说自己学习不够,说了些错话,一直回避可怕的“右派”两个字,这当然是通不过的。于是群情激昂地开始了批判。批判的火力自然很猛,不猛怎么能叫右派投降?开头,一位穿红衬衣戴眼镜长得很漂亮的女生起来发言。她说:“王××说校党委要发扬民主,言外之意便是说党委不讲民主,这就是攻击党的领导。
攻击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党,梦想把蒋介石请回来,再骑在人民头上。用心何其毒也。”她的演绎、推论无懈可击。在诸如此类的高水平的批判下,不到两小时,王××便涕流满面,承认自己是右派了。于是便休息20分钟,再攻李××……
我亲身参加了这次伟大的斗争,感慨颇多。当然,这也有使我迷惑的问题。对那位红衣女子,我以前就见过,我以为她一定是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小姐,一定是个右派,然而她却是左派,我真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觉得可笑。
经过两个回合的战斗,我深感自己危机四伏了。通过对右派的批判,我发现凡出身不好的同学,发言太积极,便是别有用心;发言不积极,又是消极抵制。总而言之,有些人说的永远是真理,有的人说的永远是错误,说话太难了。然而太难了还不能不说。因为第三个回合开始了,那就是大鸣大放。
大鸣大放是以鸣放小组为单位进行的。我在第二组。组长张之明是个高个儿,爱打篮球,对小组的工作有些力不从心,也不想当这个“官”。我同宿舍的都在一个组。另外,还有一名留级生,他是名调干生,30多了,身体很魁伟,是个党员,对人很宽厚。只是班长常常爱教训人。听说他正在申请入党,表现很积极。他越积极,我越觉得对我的威胁越大。
因为大家都有一些反右的经验了,所以说话都很谨慎,从不放要害问题,只拣些哪里有浪费这类小事来放。自然鸣放小组显得死气沉沉。辅导员对我们组不满意,批评了几次。但是批评归批评,鸣放还是照旧。谁愿意往火坑里跳!我是有自知之明的,因此总是小心谨慎地鸣放。也许是我太稳重了,也许是我能写一手好字和一手好文章,同学们都很赏识我。不被人赏识固然不好,但被人赏识不一定是好事。别的不说,整理材料抄写大字报便历史地落到我头上了。而更为难的事情还在后面。
风波骤起
一天,照例是鸣放小组开会鸣放。组长突然提出要求不担任组长工作,说自己不能胜任。他提议我担任组长,说我能写文章,有组织能力。不知是他的诚恳,还是别的同学也有这种想法,全组同学竟然都同意了。但我坚决不同意,因为组长是院方指定的(其实是辅导员指定的),根本不是民主选举的。我找了很多不能任组长的理由,如我不是团员、思想水平低,等等,但是班长也说叫我当,党员也说叫你干你就干。我把目光投向辅导员,辅导员笑着说:“同学们相信你,你就干吧,没啥了不得的。”他是山东人,带着浓浓的山东腔。推又推不了,摔又不敢摔,只好硬着头皮干。
让我当组长对大家有很多方便,不用别人记录,做记录是大家都不愿意干的事。而且抄大字报也是我了,贴大字报也是我了。当然,其他同学还是积极帮忙的,比如找纸和墨水,提糨糊桶刷大字报等。
然而鸣放时大家都是很谨慎的,如同走路一样,总要绕开那些危险的区域,只把路上偶尔看到的小石子踢几脚。其实说穿了,都是一个“怕”字,怕冒出几句“右派言论”来扣上一顶“右派分子”帽子。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自然,辅导员看穿了我们的顾虑。他说:“右派分子是客观存在,也就是说本来就存在的,不是鸣放放出来的。同学们你们都不是右派,你们就不可能放出右派言论来的。更不会打成右派。”辅导员的逻辑很严密,无懈可击。但是同学们心里很清楚,因为谁只要越雷池一步,马上就有人说某某人本来就是右派,本性难改,这回就跳出来了。同样是无懈可击的理论。这些理论学好了,随时都可以解释发生的一切,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尽管如此,全组同学的眼睛还是盯着看学院办的那次浪费展览。说什么进口摩托车是个极大的浪费,浪费的是人民的血汗钱;那台闲置几年的机器没有活儿干,少创造了多少财富等等。
于是辅导员又启发道:“咱们这幢楼本来就是院属工农速成中学,今年起不再招生了。今年毕业的还有12名同学没有考上大学,学院决定补习一年,明年再考。现在他们都返校来学习了。他们都是生产岗位的劳动模范、积极分子。现在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说应该补习,让他们再考大学。”“如果他们明年还考不上呢?”有一位同学插嘴问。“那就知不道了。”辅导员说。他总是把“不知道”说成“知不道”,这是山东人的习惯。
他接着说:“另一种看法是他们基础差,学习费劲,不如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干活,还能给国家做更多的贡献。你们也可以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想,这倒是个好题目,碰不着统购统销、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这些敏感的问题,安全系数比较大,出不了差错,就动员大家鸣放。果然,这回鸣放就热烈起来了。大家的看法完全一致,都认为他们在生产岗位上更能发挥作用,将来一样可以当车间主任、支部书记甚至厂长。而学习,他们基础差,今年考不上大学,明年也不一定考得上。还是扬长避短为好。再说,学校为工农开门,招收一些工农出身的尖子学生上大学深造也是一样的。
我记得班长当时发言也是神采飞扬的。只是党员不多发言,只是笑笑。于是大家一致同意写成大字报贴出去,另外再抄一份投院刊。自然,这个光荣任务落到我头上了。我写了一份底稿,立即念给大家听,让大家逐字逐句进行推敲。这样做,一则发扬了民主,二则大家推敲了肯定能不出问题,也可以说这是我当组长的为了保护自己所采取的手段。底稿一致通过了,便由一位同学念,我抄大字报,另外一位同学抄在稿纸上。这样稿子抄好了,大字报也写完了。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将稿子送院刊编辑部,一路便到大字报栏张贴。我呢,同学们说我太辛苦了,让我休息一会儿。
当一个人做完一件工作,总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放学时我走过大字报栏,远远就看到我抄写的大字报《这是为什么?》。它像是我们共同设计的一件艺术品,在向我们亲切地打招呼。我想,一定已经有很多人看过了。去吃晚饭的时候,我便听到了很多议论。当然,议论的都是新生。因为新生爱串联,熟悉起来快,也爱议论。老生经过一次反右的洗礼,更有经验更沉默寡言了,然而我当时以为他们是摆老资格,不屑一顾。
第二天上午,环绕这张大字报贴出几份支持的大字报,都是新生写的。老同学也来看,但讳莫如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