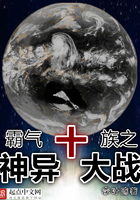时而清醒时而迷糊,应笑枕在他膝上,“当初人人觉得我来历可疑,为何你偏偏留我?”
君怀沉默半响,似在回忆一般:“因为你的呼吸。”
应笑闭上眼,并不催促。
他道:“太多人以假面示人,无奈我是个瞎子无从分辨他人面目,双耳较他人更为灵聪些,人可伪装面目,修饰言语,但是呼吸却是骗不了人的,因此得益。比如紧张时会憋气,愤怒时呼吸格外粗重。”
应笑回忆了一番,“可我那天心里有事,你又是如何分辨的?”
“我听得出来。你那天十分欢喜,不知为何,我也开心起来。”
“原来如此。”
君怀抚了抚她的发:“小幺,睡罢。”
他的动作很温柔,像儿时哄她入睡的大师兄。
“别这么叫。”她忽然道。
“你不喜欢被人这么叫?可是,上次你说家里人才这么叫你。”
应笑睁开眼,看着他:“我阿笑吧,这才是我的名字。我家人就是我师父和师兄弟姐妹,我在师门中排行最末,只有我师父和我大师兄唤我小幺。”
“阿笑。”他轻唤。
“嗯。”她微笑。
“你家人都怎么叫你?”
“他们叫我的名。”
“君怀。”
“嗯。”
“有字吗?”
“还未取。”
“以后你有了字,一定要第一个告诉我。”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睡吧,养足精神,病好得快些。”
“我睡不着。”
“要不你给我讲个故事。”
“怎么是我讲?”
“我从未讲过故事。”
“你讲吧。”
“那讲前朝兵败?”
“不想听打仗,能不能讲个别的。”
“你想听什么?”
“什么都行,就是不想听打仗。”
他沉思片刻:“有个男子,他出生高贵,为了家业他同时娶了两个女人。一个女人为夫人,另一个为如夫人。两位夫人同时怀有身孕,他便决定无论哪位先产下儿子,都由长子继承家业。两位夫人生产那天,天降异象,世人皆惊。后来夫人先一步产子,而几乎在同一时辰,二子也诞生了。男子惊喜非常,却分不清是哪个儿子带来的吉兆。后来两个孩子渐渐长大,年长的那个显现出了过人的才华,称得机灵聪明的二子事事平庸,男子着重培养长子,希望有一天他能够顶替自己的位置。他对夫人以及长子疼爱至极,除了他们竟像是再无妻儿,半年也不去如夫人那里一次。在长子八岁的时候,夫人又有了身孕,男子高兴得不得了,他对所有人昭告了长子的地位。但是如夫人不甘心就这样输了,在夫人生产之时传统家仆做了手脚,以至于夫人难产死去,余一女婴。在家中混乱的时候,长子身中剧毒将死,恰逢一位名医来访,将长子体内的毒祛除了大半,只是毕竟耽误了些时辰,损了肝气······”
君怀听她呼吸均匀,不知何时应笑已经睡着了。
他的手指从她的额间轻轻滑到她的脸颊上,明明颈上滚烫,脸颊却是凉的。他修长的手指顺着凉热交替的皮肤边缘细细摩挲,轻轻揭起一片薄薄的皮肤。
他的手指探到这层皮肤下面轻轻抚摸,指腹下的肌肤烫得灼心。
君怀慢慢将那层皮肤严丝合缝地重新贴好。
每隔半个时辰,他尝试将仅剩的一些水喂给她,她却要紧牙关,滴水不进。
风雨声震耳欲聋,雨水从屋顶渗入殿内,青石地面上积聚了一大片水洼,又湿又滑。君怀慢慢淌过积水,将装满砂锅从殿外拿到手中。只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他的衣袖和肩膀便已湿透。
他将砂锅外面的水珠擦干,小心翼翼地将它架在火上。
做完这一切,他摸索着探向她的额头,她的额头越来越烫。
夜深子时后,应笑烧得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
她冷地发抖,像一片树叶在寒风中瑟缩般抖个不停,他只好再将篝火点燃,他找不到足够的枯枝,只好点燃了新鲜的树枝,腾起一股股呛人的浓烟。
他将她挪到篝火旁,他解开腰带,用外衣将她紧紧盖住,把她抱在怀里。
她睡在他的胸腹间,急促的呼吸像抽拉的风箱,他觉得自己快要被她烫伤了。
记忆中,自己的身体也曾这般烧得滚烫,再睁开眼——世界论陷入黑夜,永无天明。
他十几年平静无波的心情,像是忽然长满的春草般,杂乱而生。
他一遍遍摸她的脸,试图记住她的轮廓。
她昏睡不醒。
就算在平常时候,她每次呼吸吐纳都惊人地绵长,但是这时她的呼吸声像停止了一般,明明还有心跳。
他知道动物冬眠就会进入深睡状态,如同假死。
龟息之法?
应笑正在做梦。
在梦中,在被鬼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