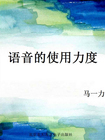冰雪聪明之外,遗世独立。
风姿眷眷,梅骨柔面,而心,是霜冻三尺。
他又能为她做些什么?
眼前的王者坦荡襟怀,隐然背负了国之重任,他亦是英雄情骨,不负江湖侠义,他也不过是帝王的臣子,难道,真的要与他敌对下去?
心念如电,而庐江王依然恭敬拱手等他决策,他舍小我顾大局的王者风范,让他铁树般的心肠突地为之动容。
半晌,逯羽伸掌托住他的臂腕,眸华灼灼:“好,不为你,也不为皇帝,只为百姓与四公子结义之情!”
他为的又何尝不是萧瑶?
那个风雨摧残不去的女子,以倔强的性子,傲骨的眸华,一点一滴无形瓦解了他的冷漠与偏执。
他的眸中平静如水,一丝温华眼底悄泻。
“多谢羽兄。有你相助,是大汉之幸,是我刘劼之福。”庐江王翻腕握住他的手,紧紧一按,掌力遒劲,欣慰与契友之情不言而喻,仿佛昔日的四公子四掌相击,令人豪气万丈,侠骨柔肠百结千缠。
逯羽腕臂微微一震,脱离他的手,胸中有一缕莫名的颤动,自从好友一一消逝他的生活,他好久未曾有过壮士易水潇潇的感觉了。眸里虽冰然与他对视,瞳中分明有了暖意,淡淡道:“我如何助你?”
“请羽兄老实告诉我,你与修鱼翦篁是何种关系?”庐江王低沉一语。
逯羽蹙眉,半晌方清漠道:“我八岁那年,天降巨灾,先是家中失火,父母遇难双亡,接着唯一的妹妹也被人掠去卖了。我为了寻找妹妹,才踏遍大江南北,整整两年却是半迹不见,饥肠辘辘昏倒在修鱼氏门前,被修鱼翦篁救了,她甫时是修鱼氏掌家小姐,对我亲厚有加,视为幼弟,十分维护。而我亦敬重她为长姊,但自有自己处事风格,不妄动本性。这些可够大王中听的?”
逯羽声音淡泊无绪,却依稀漏了一丝稀薄的凄怆,那样不堪的过往着实令人动容,也颇感愧疚。
庐江王恭敬施了一礼:“是刘劼冒渎,让羽兄忆痛。原来羽兄与修鱼翦篁有如此情分在内,如此我总算懂了,为何你肯为她出生为死,却始终不肯违背侠仪剑道。”
“你怀疑长姊是幕后之人?”逯羽冷眸凝他一眼。
“羽兄说呢?”庐江王好整以暇一问。
“骄扬是否长姊所使,我不得而知。但长姊一介女流,未必使得起江南四公子。”逯羽伏犀瞳一抹自负,同为江南四公子,他如何不晓得他们的为人处事?虽然从来不提各为其主,但心性却是相通。
“羽兄是说江南三公子与骄扬各为其主么?多谢羽公子一语惊醒梦中人,我先前只把注意力放在修鱼翦篁身上,倒是忽略其它了。”庐江王舒展俊眉,玉面笑意深深。
“大王不怕我是声东击西,特地替长姊开脱疑影么?”逯羽横了他一眼。
庐江王爽朗大笑:“羽兄也忒不了解我了。既信人便不疑,我深信羽兄是我举世唯一知己,岂有怀疑羽兄高格之理?再则,我是王者,如何不晓得修鱼翦篁这些年以美人财物结交富贾王侯名流之辈?通常一个主内的女子,哪里有如此闲情逸兴积极扩张势力?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做得太过露骨,自落疑影于有心人了。”
“长姊并无多大过错,只是心中有些仇恨未解,假以时日,仇恨消去,一切自不劳大王费心绞力了。你还是去找出江南三公子幕后主人才妥当。”逯羽唇畔扬了别样滋味,他分明还是维护修鱼翦篁的。
也难怪,数年情义,岂是轻易辜负的?
“羽公子,你若见到骄扬,务必请他与我一见,切莫遇上酷吏张汤。”庐江山平复激情,低沉一语。
“骄扬与心爱之人理当隐居海岛,再难踏上中原之路。即便遇上张汤,他亦不会束手被擒。以他性子,宁死也不肯出卖恩人,萧瑶之事,就当石沉大海。”逯羽掌中碧玉箫轻横,仿佛断定骄扬执拗情结,宁死不屈。
那么萧瑶活着,也没有多少人知晓,而晓得的人,要么被修鱼翦篁暗中除掉,要么是她的仇敌,要么是关爱她的人,两者都不愿她入宫,前者怕她受宠,后者担忧她宠尽衰来。
而庐江王绝顶睿智,分明已揣测出苦薏便是萧瑶。
“他恩人是谁?”庐江王半丝漏缝也不肯放过,眸光凝在他面上。
“我不知。”逯羽晃他一目,飞身下了红亭,衣袂飘逸如苍鹰之翅羽,转瞬消失碧林芳菲之中,在假山叠嶂处化为缥缈云烟,似不曾与他会晤过。
庐江王一瞳怅然若失。
逯羽只怕与骄扬一般,都受恩于那个人吧?
她,真的是修鱼翦篁吗?
修鱼翦篁一介女流,觊觎皇家到底想做什么?真的是如逮羽所说因为仇恨?她与皇家有何难解的恩怨?
庐江王剑眉深锁,幽幽嗟叹。
“王兄!”姌玳悄然从合欢树林走出,柔柔唤他。
庐江王一愕:“玳儿,你为何在此?”
想他与逯羽都武功不弱,竟未感觉附近有人。
“王兄莫担心,我离得远,听不清你二人说话。”姌玳粲然一笑,洞悉他心。
庐江王淡笑,抚抚她的肩,温声道:“该回去了,玳儿。母后怕是急了,你我二人都不在宫中,谁来孝顺母后?”
“那你还不赶紧娶了王后回去?”姌玳笑嗔。
庐江王剑眉稍蹙:“我不会娶她。”
“所以王兄正好借江都王之手推了婚事?”姌玳心头一畅,秋波欢喜潺潺。
“聪明太过,未尝是好事一件。”庐江王戳了她额头一指,揽了她的肩,往亭下走去。
姌玳明眸泻去愁烦,原来王兄果然是有目的而来,瞧他刚才与逯羽那般模样,显然二人相交很久了。
“翁主,你瞧见暖雪了吗?”迎面跑来别妍,面上一抹忧急,来不及行礼,气喘吁吁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