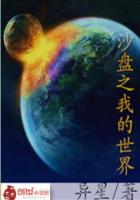习习凉风,伴着他语意森森,夹了碎碎冰棱,眸光仿佛利剑泻下,一泊寒珠。
“黑小怪,莫非你怕欠我人情?你放心,我永不讨债!我忙得很,日日想着挣银子,只恨分身乏术呢。”苦薏莺莺呖声,如青玉弹竹,悠悠雅雅里,有绵秾的梅韵,极是好听,若非那几分莫名的淘气,倒是很让他惬心怡意。
“挣银子?”逯羽语气似霜,凌空而下,黑衣立在眼前,眸光如兽迫着她:“蠢丫头,你月母亲这些年都不管你么?”
苦薏面上一凉,牵了长裙,俏皮笑道:“黑小怪,庆儿拜托你了!我让保母预备下你的饭菜,院里吃些新鲜,都是我们自种的呢。”
末了,转身往山下跑去。
逯羽脚下一挪,伸手拦住她的去路,目光如剑,唇角浮了丝冰凉的情绪:“告诉我,她真的心狠如斯?”
他的双眼冷凝得骇人,似恼似怒,一双寒潭深水似的幽静黑瞳,似蕴了戾气的冷箭,缓缓穿透人心,一丝不肯从她面上撤去,仿佛要噬去她的俏笑与自尊。
苦薏纹丝不动,美如牡丹的眸子渐渐失了笑意,只慢慢垂下眼睑,抿紧眼泪,再抬眸时,扬了扬清丽的下巴,湉湉芊柔道:“我与月母亲虽则五年未见,却是心有灵犀,我们彼此相信这是最好就足够。并非她长伴身旁才是舐犊情深,有时不见胜过相见。”
苦薏伸出双手在他眼前晃了晃,恢复一抹俏皮:“有它,就有活路,难不倒我卓苦薏!”
逯羽眼尖,她粉嫩的手心厚茧层层,有浅浅的伤痕,因皮肤太白,落入眼帘,怵目惊心。本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千金侯主,却为了生存,整日弄花撷草,弄得伤痕累累,若非她会些调理肌肤之术,这双手只怕也是如枯藤般不堪入目了。一介弱女子,独自承受着拘禁人生,若非她幼时的特殊生涯,着实难以度过。
心头突突,剑眉微暖,眸光稍霁,唇边飘过一缕浅浅的色彩,淡得觉不出柔和,只蕴了漠漠道:“我宁肯相信她心狠,也不愿晓得她再来什么苦衷,伤人痛己。”
“月母亲正因为疼我们才放任自流,她心底或许有悲,然而坦荡如斯,你莫怪她。”苦薏口中微苦,明眸烈烈,有艳艳的殷殷情切。
逯羽冷冷一嗤,含了悲色:“薄情原是最深情!危险之地,绝了疼爱才是舐犊情深,真真可笑可叹!坦荡如斯?世间岂有弃情绝爱而坦荡如斯?不过自欺欺人罢了。”
他长衣展展,白发飘飘,人影晃至山顶竹轩,手中多了把黑宝剑,顺手一挥,斩断数十枝湘妃竹,一壁扬了痛彻的声音道:“这湘妃竹云纹紫斑,红如赤血,白似雪莲,你不如做了扇骨笔洗,也是极好的银子,留它碍眼。”
黑衣翻卷,掌中剑挽狂花,仿佛雨线离天,下了一阵翡翠雨,叶落竹断,裂成片片,整齐有序,扬了苦薏裙边一地翠绿鲜红。
苦薏既喜且呆,正有此意,只是苦于没有力气折竹罢了,他的神色有些痴狂,似乎对这湘妃竹充满了怨怼。
果然,逯羽长臂一握,攥了卓庆在腕中,冷冷道:“湘妃断魂,不过一痴耳,男儿练剑,岂能女子泪下独舞?我带你找一个好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