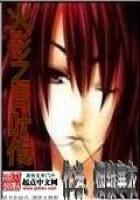且说李德裕出镇浙西,刚到任就接到了一桩刑讼案。原来浙西治所杭州有一座甘露寺,寺院方丈新近任命主持慧空。他接任不久,寺院财物就亏空白银上千两,其他僧人众口一词,以坐赃致罪,告之节度衙门台下。唐代法律本刑、民不分,按照《唐律》理应由节度衙门受理。案成,李德裕依“诸鞫狱者,皆须依所告状鞫之”,提审被告。慧空上堂以无理申辩,甘愿领死罪。李德裕大是奇怪,就训喻说:“《杂律》规定,‘诸坐赃致罪者,一尺笞二十,一匹加一等;十匹徒一年,十匹加一等,罪止徒三年’,汝罪不至死,何以自认死罪?”慧空仍叩头谢罪道:“贫僧无力辩白,故甘愿领死罪。”李德裕又道:“汝坐赃数额巨大,罪不容赦。然汝主事才一月即隐用千金,其金用于何方?”慧空一时无法说出,李德裕心想,此案多有疑窦之处,就命暂将慧空羁押。
李德裕遂提取甘露寺来往账目,见历届主持所移交的账目,移交银两多少,一笔一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他便去走访甘露寺僧,寺僧仍众口一词,都说全被慧空挥霍一空。但德裕想,千金并非小数,一月内便能挥霍得尽,必有大款用项,慧空何得不置一辞?他再去询问方丈,方丈只是说:“未见慧空有使钱处,还望节帅明察!”德裕就更加疑惑,便连夜探监再审。慧空这才说:“众僧都愿意为主持,以往主持都买好僧人,得以推举。为主持后便以寺中银向佃农放债,放出去的是银两,入账的却是空放文书,其银两去向,贫僧并不知晓,引起众僧不满,共相攻讦,贫僧实无力辩白。”德裕又问:“方丈既知内情,何得不言?”慧空道:“方丈其实也不知千金之去向,其若明言既拿不出真凭实据,恐人众口一词委他以诬告罪,又怕众怒难犯,一人难以当之,才愿经公,盼明公明察公断。”李德裕点头不语。
他回到私衙苦思,怎样才能查出真相,为慧空辩冤?后来他忽想到,浙西寺院多沿用南朝的旧习,以金银作为贮币,再使用时可拿出兑换成铜钱或绢帛进行流通,不同的主持,将白银熔成银锭时,各有不同的形状,以示区别,往往有马蹄形、银饼式、通宝式等。第二天他便传唤原告众僧中的十数人,问他们道:“尔等可见过千金之银?”众僧纷纷说:“交割时,贫僧亲眼见一一令慧空过目、收贮。”李德裕微微一笑,令衙役从市上雇来十数个兜子(只有座位而没有轿厢的便轿),命每个原告分乘一个兜子,放下兜子的轿帘,令他们互相看不见,且互相间不能说话,并取来和好的黄泥,命众僧分别依次捏出历届主持移交千金白银银锭的形状。十数个僧人或捏不出,或胡乱做成银锭模型,一一置于兜子之前。凡是做出金锭模型的,令他们分别按历届主持交割金锭的形状,将模型排出,他们便或胡乱排列,或排不出。
李德裕巡视一番后大怒,升堂将他们带上,厉声斥道:“尔等根本不曾见过千金银锭之形,还不如实招来,大刑伺候!”众僧慌忙叩头道:“愿招!”原来历届主持在任主持前,就对众僧许下愿:“只要荐我为主持,我必与师兄弟共享乐。”故在更换主持时,大家就共同推荐他。他任主持后,便将甘露寺的田租等收入,先熔成金锭,到用时再切割成碎银分给众僧,任他们入青楼、嫖私娼、观百戏,尽情享乐,但他们见到的只是些碎银块,并未见过真正整个的银锭。因此李德裕命他等用黄泥做出历届主持所铸的银锭形,他们肯定做不出。
主持和众僧们的所作所为,方丈不可能没有所耳闻,他要顾及甘露寺的名声,就想用换主持僧的办法,从控制钱财入手,只要断了众僧的经济来源,他们自会渐次收敛,无法再去挥霍享乐。不曾想,众僧们已是通通作弊,主持更换后,仍继前胡为。直到后来,方丈看慧空并不与众僧同,便直接命慧空任主持。在交接手续时,慧空见到的只是一些文籍,并不见金银实物,众僧们轮流给他做工作,要他依前历任主持之例去做,慧空不答应。众僧便私下商议,要除掉慧空,计议已定,就共同告发慧空坐赃贪污了甘露寺千金,诬他入狱。等到众僧做不出金锭的泥模,李德裕威胁说要对他们动刑时,他们个个害怕,这才说了实情。李德裕大怒,便仍令慧空为甘露寺主持,凡参与诬告慧空的僧人,通统追回度牒,令他们返俗,回乡种地,以此入奏朝廷。但当时正在享乐的唐敬宗以为此乃区区小事,用不着小题大做,便不予理会。
正在这时,和浙西邻近的徐泗方镇出现的问题,却使李德裕心惊,他敏感地预料到,这事将是国家祸乱的征兆,必得引起朝廷重视,且要审慎处置。却原来徐泗观察使王智兴,见朝廷对河北三镇割据者无可奈何,就心生效仿割据之念。他素来蛮横,却很有心机。原本唐代佛教兴盛,但国家每年对剃度为僧是有严格控制的。贞观二十二年(648),玄奘劝唐太宗度僧以树功德,唐太宗虽采纳其谏言,但下诏京城及天下州寺只能各度五人,弘福寺允许度五十人。全国共有寺院三千七百一十六所,共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这些僧尼全由朝廷发给度牒。自唐太宗起,朝廷对每次度僧尼人数有严格控制,是出于两种考虑:一是要保证有充分的社会生产劳动力,可保证国家税源;二是要保证有足够的兵源,以备征战之需。贞观时,全国人口有四千多万,天宝元年(742)约五千一百万,僧尼所占比例都很小。到了晚唐,人口仅为盛时的一半(其中不乏逃匿户口),而僧尼就已发展到七十万。
王智兴为了便于控制,就想于辖内大肆剃度僧尼,再将寺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于是他借口唐敬宗生日将到,上疏请求在泗州大设戒坛,大度僧尼为唐敬宗祈福。昏庸的唐敬宗十分高兴,欣然允准。王智兴见诏允,狞笑一声,在徐州、泗州一带,大肆招度僧尼,兼并土地,名为“祈福田”。老弱百姓失去土地者,流离失所,哭声震天。
身为浙西观察使的李德裕,闻报大批难民渡淮、渡江而来,忙命沿途州县搭起了粥棚,开仓救济饥民。为了看个究竟,他仅带亲随微服私访,亲到码头去看,见渡江者,大多都是扶老携幼者和僧人。他询问百姓,大家都哭诉道:“凡家中有三个儿子,官府强令其中一人要剃度为僧。凡稍有不从者,官府便申斥道:‘为皇上祈福,谁敢不从?’就强行抓入寺院剃度,然后放火烧了我们的房屋,抢走土地,如今我们无以为家,只得扶老携幼出来逃难。”李德裕大怒道:“自元和后,天下就禁度僧尼。王智兴怎敢如此大胆,竟违律胡行?”百姓见这个四十出头的壮年汉子,一身读书人打扮,竟然仗义执言,反来劝道:“公子噤声,听他们说这是奉了皇上的圣旨,让他们知道了,会招来杀身之祸。”李德裕见不便再说什么,就愤愤起身回衙。
他回到节帅府,立即写了一道弹劾王智兴的奏章,派快马送入丞相府,托裴度上奏。裴度看后大是吃惊,不敢怠慢,立即叩宫求见。正在后宫宴乐的唐敬宗,听说裴度入谒,不敢不见,只得出延英殿宣。裴度拜见后,唐敬宗赐坐,裴度谢坐后双手递上一份奏章,在一旁落座。敬宗问:“卿为何事上奏?”裴度施礼答道:“陛下御览自明。”敬宗开启,见上写道:“智兴为坛泗州,募愿度者人输钱二千,则不复勘诘,晋加落。自淮而右,户三丁男,必一男剃发,规影赋,所度无算。臣阅渡江者日数百,苏、常齐民,十固八九,若不加禁遏,则前至诞月,江淮失丁男六十万,不为细变。”其后署名是“浙西观察使启奏”。
唐敬宗看完后张着两眼,结结巴巴地对裴度说:“王智兴只说诞月为朕筑坛祈福,怎会事至如此?”裴度侧身施礼说:“违律剃度敛财尚且不说,这苏、常等州乃国家财赋重地,若人去地空,王智兴借口因陛下有诏,而庶民避之,财赋无供,自此以后国家税赋尽入王智兴之手,陛下怎处?”唐敬宗大惊,站起身来,结巴着说:“这……这……如何是好?”裴度平静地说:“陛下立即下诏徐泗停止一切剃度,令王智兴招抚百姓回乡,归附其田土,致力农耕。”裴度沉吟了一下,又道:“王智兴此举,恐另有考虑。陛下不妨密诏李德裕整顿兵备,以防不测。”唐敬宗忙说:“就依卿奏!”裴度起身辞出。
却说裴度一入宫,王守澄就得了密报,知道裴度叩宫入谒,并非为寻常细事,就赶紧派人通知了李逢吉。李逢吉不敢怠慢,立即整备入宫,不料在宫门口碰到了出宫的裴度,赶紧笑着上前施礼问道:“端公何来?”裴度一边还礼,一边反问道:“公为何而来?”李逢吉支吾道:“下官进宫问安。”裴度笑说道:“此时进宫问安恐非其时!”说完不等李逢吉回言,就一揖说:“下官失陪了。”说完扬长而去,李逢吉望着裴度的背影,冷笑一声,转身入宫求见。
还在延英殿独自寻思的唐敬宗听小太监报:“端公李逢吉求谒!”唐敬宗忙说:“赶快宣!”李逢吉笑着走进,躬身施礼道:“臣特来请安。”唐敬宗不等说完,就连说:“罢了,罢了!”接着就把李德裕弹劾王智兴、裴度所奏的对策,一股脑地告诉了李逢吉,又问道:“爱卿以为如何?”李逢吉一直躬身表示洗耳恭听,此时眼珠一转,心想:正可一箭双雕。接着缓缓说道:“裴公所言有理,陛下除诏命李德裕防范外,兴元是徐泗通京师的咽喉要道。如徐泗有变,兴元还需一员重臣镇守。臣以为裴公名震朝内外,镇守兴元非裴公莫属。”唐敬宗立即说:“就依卿奏!”
李逢吉满心欢喜地出宫,心想:真是天赐其变!这一来,让李德裕守浙西,在南面防备王智兴,一时休想回朝。再让裴度镇守兴元,在北面防备王智兴,让他离了朝廷,我岂不是耳根清净?接着又转念想道:且慢,何不将裴、李二人所奏,弹劾之事告诉王智兴,逼他不反也得反。苏、浙一带战事一起,裴度、李德裕两人不但回不了朝,迁延日久,恐怕还劳而无功。对!就这么办,不过此计尚不可让王守澄知道,防他坏我大计。
果然,唐敬宗诏令裴度以同平章事、充山南东道节度使、临汉监牧去镇守兴元,裴度出朝后李逢吉更肆无忌惮,他并不将自己一箭双雕之计告诉王守澄,只略略说了李德裕弹劾王智兴,皇上以防不测,令裴度去镇守兴元。王守澄何等狡猾,心知让裴度出朝必是李逢吉所为。不过李逢吉这样做,和自己的心意是一致的,他听后也不说破,只是一笑了之。李逢吉就派心腹暗中到徐州去,把李德裕如何弹劾王智兴的,裴度又是如何谏言对付王智兴的,唐敬宗不日将要下诏禁止王智兴继续剃度,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王智兴。不过李逢吉怕有把柄落在别人手里,并不写只字片言,只是派人传言而已。王智兴心中打什么主意,他当然比谁都清楚,听了来人的传言,正道着自己的心病,自然不会不信,但对于裴度之谋,他又不能不有所顾忌。
听说王智兴将为乱,又得知裴度出朝,可惊坏了韦处厚,他连忙进宫去见唐敬宗奏道:“徐泗若有事,朝内外正要仰仗裴公处置朝政,陛下怎可令其出朝?徐泗一旦有变,朝廷处置稍有不妥,为害不浅。”唐敬宗吃惊地问道:“何至如此?”韦处厚道:“近闻沧景也颇不安宁,徐泗可得裴公阻其北,沧景又靠谁去阻遏?”唐敬宗大惊道:“沧景事为何不听李逢吉提及?”韦处厚道:“李逢吉久欲排挤裴度出朝,其若再提及沧景事,其奸可得施行?”唐敬宗跌脚道:“李逢吉误朕,今当如之奈何?”韦处厚沉吟良久说:“成命已下,岂可又废,不可使陛下失信于文、武。姑且使裴公留于兴元,以观徐泗、沧景之动静。一旦有变,陛下可立召裴公回京,无论如何,裴公都不可在外久留。”唐敬宗闻言,才真正舒了一口气,但他腐化享乐的旧性却没有根本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