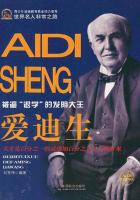关于真话与谎言的思考
在我有时还读一读的几本书中,我最喜欢的是古罗马作家普鲁塔克的作品。我从中也获益最多。这是我童年读的第一本书,也将是我老年读的最后一本书。几乎可以说,让我每次开卷总有所得的作家,就他一人而已。前天,我翻开他有关道德的论著,读那篇论文《如何从敌人那里汲取益处》。同一天,我在整理一些人寄给我的一些小册子时,偶然发现里昂皇家科学院院士罗齐埃神甫的一篇日记,标题下面印了几个字:献给献身于真理的人罗齐埃敬献(卢梭有句箴言“献身于真理”——译者)。这些先生们的手法我是太了解了,眼前这一个我也绝不会弄错。我明白,他以为用这种彬彬有礼的方式,毫不留情地反讽了我一句。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要这样来讽刺我呢?我难道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吗?为了用上善良的普鲁塔克的教诲,我决定在第二天散步时,就撒谎这个问题对自己来一番审视。我终于更加坚定了已经形成的观点:希腊特尔斐城的德尔福神庙上那句箴言“你要通过自身去认识自己”,并非那么容易奉行。我在《忏悔录》里认为容易,其实是大错特错。
第二天,在散步的路上,我开始执行先天的决定。刚开始反省,头一个念头,就是想起幼年可恶地撒过一次谎(卢梭小时曾诬一个女佣偷了主家的一根小丝带)。我这辈子一直为这件事所折磨,到老我这颗屡遭不幸长期忧伤的心还为此深感内疚。那次撒谎本身就是很大的罪过,而且,由于它引致的后果,这罪过就更加严重。我虽然一直不知道它引出了什么后果,但内疚使我尽可能把后果想象得十分严重。不过,如果撇开其他因素不谈,只说我那时的心情和处境,那么这个谎言其实只是一次羞愧难堪的后果,我根本没有任何伤害那个姑娘的企图。我可以对天发誓,就在我因极度羞耻,说谎冤枉她的那一刻,我也愿意把那后果揽过来,由我独自承担,就是让我抛尽热血,我也乐意。可是我只能说,那终究只是一个愿望,就如此刻我感觉到的一样,因为在那个时刻,我那害羞的本性压下了内心的任何愿望。
回想起那个不义的行为,以及它给我留下的难以抹灭的内疚,我就对撒谎生出强烈的憎恶。在下半辈子,我也许会因此而避免重染撒谎这种恶行。在我选定那句座右铭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天生就是献身真理的材料。读到罗齐埃神甫的日记之后,我做了更为严格的反省,我不怀疑自己配得上这么一句座右铭。接下来,我更加仔细地剖析自己,竟意外地发现自己编造了许多事情。我记得,在我以热爱真理而自豪,并为此牺牲了自己的安全、利益乃至人身的那个时期,我是把它们当做真理来宣传的。当时我那种客观和公允,我在任何人身上都不曾见过。
最让我吃惊的是,当我回想起编造的那些东西时,竟没有生出一丝真正的内疚。我从来就憎恶虚伪,在我心里从来没有弄虚作假的一席之地,我这个宁可遭受酷刑拷打,也不愿以撒谎来躲避的人,这个为了童年一个谎话而五十年来备受内疚折磨的人,是出于什么奇怪的理由,才会这样既无必要又无好处地撒谎呢?要怎样自圆其说,我才会撒了谎而不感到愧悔呢?我向来不能容忍自己的错误;我始终听从道德本能的引导,我的良知一直保持着最初的完美,即使在它因为屈服于我的利益而变坏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但是,在出于痴迷欲望,起码会为自己的缺点短处辩解的场合,人们尚能保持正直,独独在没有任何理由要撒谎而且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失去正直呢?我明白,这个问题能否得到解答,取决于我对自己的评价是否公正。经过认真反思,我终于解答了这个问题。以下就是我的解释。
我记得在哪本哲学书里读到:撒谎就是把应该揭示的真相掩盖起来。由此可以推论,一个不必说穿的真相,不说出来不算撒谎;但是,在同样情况下,一个人不但不说出真相,而且还编造假相,那他算不算撒谎呢?按照这个定义,我们不能说他撒谎,因为,如果有个人,并没有借与他一文钱,而他却给此人一块假币,那当然是欺骗此人,但他并没有窃取此人的财产。
这里有两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需要思考:第一,既然并非任何时候都得讲真话,那么,应该在什么时候,又是怎样来对人讲真话呢?第二,有没有可能发生无意中骗了别人的情况?第二个问题非常清楚,这点我很明白,书里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书中最严格的道德并不会叫作者付出什么代价,而社会的回答却是肯定的,因为在社会上,书中的道德被视为无法实行的空谈。因此,就让那些权威们打嘴仗去吧,我还是努力用自己的原则自己来解答这些问题。
普遍的、抽象的真理是最宝贵的财富。没有它,人就成了瞎子;它是理智的眼睛。人就是通过它而学会引导自己,做应做的事,朝自己的真正目的前进。特殊的、个别的真理却并不总是财富,有时甚至是一种祸害,但经常是一种无足轻重的东西。一个人不但应该知道,而且为了自身幸福必须了解的东西也许为数不多;然而无论多少,都是属于他的财富。他不管在哪里发现这种东西,都有权要求得到。谁剥夺他这种权利,就是犯了最可耻的盗窃罪,因为这种东西属于公产,把它交出来,使之流通的人并未丧失它。
至于那些在教育和实践方面毫无用处的真理,它们甚至都算不上有用的东西,又怎么会是财富呢?何况财产只有建立在实用的基础上才算财产,没有用场的财产就算不得财产。人可以要求得到一块土地,尽管它十分贫瘠,也至少可以在上面居住,但是,一件无关的、对谁都不起作用的事实,无论真假,谁都不会对它感兴趣。在精神上没有用的,在肉体上也没有用。无用的东西,不论是什么,都不是不可或缺的,一件东西必须有用,或者可能有用,它才是人所需要的东西。因此,人们需要的真理就是和正义有关的真理。如果把真理用在对谁都不重要、认识它毫无益处的无谓事情上,就是对真理这个神圣名词的亵渎。真理如果毫无用处,就不是人所需要的东西。因此,不说真话或者隐瞒真相的人算不上撒谎。
但是,那些根本得不出结果、以至于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毫无用处的真理是否存在呢?这是另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等一会我再来谈。现在,我们来探讨第二个问题。
不说真话和说假话,是有天壤之别的两码事,然而,却可以产生同一种作用。因为只要这种作用是乌有的,那么结果就肯定是一样。无论在哪里,只要真理是无关紧要的,那么,作为真理的对立面,谬误也就同样是无关紧要的。由此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在相同情况下,说出与实话相悖的话去骗人,并不见得比不说实话去骗人更不公正。因为,就无用的真理而言,谬误不见得比无知更糟。我认为海底的沙子是白是红,不见得比我不知道海底的沙子是什么颜色更重要。既然要给人造成伤害才能叫不公正,那么,没有伤害别人又怎么能说是不公正呢?
但是,如果就这样简单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而并不预先作出详细而必不可少的说明,以便让人将之正确地应用于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那我就还不能付诸实践。因为,如果讲真话的必要仅仅是建立在有用的基础上,那么我又怎样判断它是不是有用呢?一个人的优势往往造成另一人的劣势,个人利益几乎总是与公共利益相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样做人呢?在交谈中,应不应该为了对方的利益而牺牲不在场的第三者利益?一番真话,有利于一方而不利于另一方,应不应该说呢?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是否应该衡量?是用公共利益这个天平来衡量,还是用公平分配这个天平来衡量?对于事物的各种关系,我是否确有足够的了解,只需根据公正法则去运用所拥有的知识就行了?此外,在反思怎样对他人的同时,我也反思怎样对待自己、怎样对待真理吗?我骗了别人但没给他造成任何损害,就说明我也没有给自己造成任何损害吗?只要没做不公正的事,就总是清白的吗?
这么多伤脑筋的问题。要摆脱它们其实很容易,只要说这么一番话就行了:“不管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永远都要保持真实。正义本身就存在于事物的真实之中。谎言总是不正义的,谬误总是骗人的,因为你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按规矩是不应该做的和不应该相信的。只要你说的是真话,无论会引出什么结果,都无可指摘,因为你没有往里面塞私货。”
不过,问题到此是说清楚了,但并没有解决。我们并不是讨论永远说真话是好还是不好,而是要探讨是否非得要永远说真话,据我的思考,似乎答案是否定的,同时还要分清必需说真话的情况,和可以不失公正地避而不谈或者不算撒谎地稍加掩饰的情况。因为,我发现这些情况确实存在。因此,现在的问题就是找出一条认识和确定它们的可靠规律。
但是从哪里去找出这条规律并证明它是正确无误的呢?我总是认为,与其用理性的光芒,不如用良知的意愿去解决此类难以解决的道德问题。道德本能从未欺骗我,它至今仍在我心中保持纯洁,足以得到我的信赖。在我的行为操守上,它虽然偶尔在我的痴迷欲望面前沉默,但我记得事后它又重新控制了我的行为操守。我就是这样严格地审判自己,就和去世后将接受的天主审判一样严格。
根据人的演讲所产生的效果去评判这些演讲,往往会作出错误的评判。因为演讲的效果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感觉和了解,而且它们跟演讲的场合一样在不断变化。能够据以评判演讲的,唯有演讲者的意图,只有它才能确定演讲坏;坏到什么程度,好也好到什么程度。只有怀着欺骗的意图去讲假话,才算撒谎。即使是欺骗的意图本身,也并不一定和损人的意图有关,有时甚至还完全相反。不过,要说一个人撒谎是无辜的,并不是害人的,光说他并没有害人的意图还不够,还必须肯定一个前提,即他给对方造成的错觉无论如何不会危及他们本人或别人。不过很少人确信能做到这一点,再说做到这点也委实不易。因此,完全无辜的撒谎也同样少见,亦同样难得。
为自身利益撒谎,那是诓骗;为他人利益撒谎,那是诈骗;为了损害别人而撒谎,那是造谣中伤;以上几种是最坏的撒谎。而对自己与他人都无害亦无利的撒谎,则算不上撒谎。那只是虚构。带有某种道德教育目的的虚构,叫做寓言或神话。因为其目的只是或只应是:用易于感人、令人赏心悦目的形式来包装有用的真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根本不会努力掩饰事实上的谎言,因为它只是包裹真理的装束。无论如何,只把寓言当寓言的人并不是撒谎。
还有一些纯属无聊的虚构,譬如一些故事与传奇小说。它们大多数不含任何真正的教益,仅以消遣取乐为目的。由于这类虚构作品没有任何教益,要评判它们,只能根据作者的意图。如果作者把这些虚构说成是真的,那就无法否认那是货真价实的谎言了。然而,有谁曾对这种谎言表现得非常不安呢?有谁又严厉指责过这种谎言的炮制者呢?譬如说,就算孟德斯鸠的作品《克尼德神庙》具有某种道德上的教益,它也被其中的淫荡细节和色情描写给遮蔽和败坏了。作者为了给内容涂上一层质朴的色彩,做了什么呢?他欺骗读者说,他这部作品是从希腊文稿中翻译过来的,并以最能使读者信以为真的方式,编造出发现这份文稿的故事。如果这还不算谎言,那么,请告诉我,什么才是谎言呢?然而,有谁想到要拿这个谎言向作者兴师问罪,并因此而把他当做骗子呢?
有人也许会说:这无非是开个玩笑,作者虽然肯定了故事的来源,却并不希望让人们相信这是真的。事实上,也没有谁相信这是真的。公众一刻也没有怀疑这部所谓的希腊作品是出自他的手笔,他只不过把自己打扮成翻译者而已。但是这样说是没有意义的。我将回答,毫无目的,开这样一个玩笑,那只是小孩子做的荒唐事,傻得可以。撒谎者肯定自己是说真话,尽管无人相信,但他此时同样是在撒谎。应该把受过教育的读者与头脑简单、易于轻信的读者区别开来。对于后者,一位貌似真诚严肃的作者编的故事就能把他们欺骗。只要把毒药下在一只古式酒杯里,他们就会毫不担心地把它一饮而尽。如果把毒药下在一只新式酒樽里捧给他们,他们或许还会生出几分戒心。
无论书本里是否做过这种区分,每一个真诚对待自己、不愿受良心责备的人心里都是做过这种区分的。因为,为自己得利而说假话与为损害别人而说假话一样,都是撒谎,虽然前者的罪过没有那么大。把好处给予不该享有的人,就是扰乱公平的秩序;不顾事实,把一个可能引来赞扬或指摘、招来控告或者需要辩解的行为归在自己或别人身上,那就是做不公正的事情。因为凡是与真理相违背,无论以何种方式损害正义的事情,就是撒谎。这就是明确的分界线:有些事情,虽然有悖于真理,但与正义毫无关系,那就只能算虚构。我承认,如果谁把一个纯粹的虚构当做撒谎来责备自己,那他的良知肯定比我要高明。
被人称作善意的撒谎是真正的撒谎,因为,为了好处而撒谎,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都是不公正的,不会比为了损害别人而撒谎好。不顾事实赞扬或者批评别人,不管是谁,只要这是个真实的人,他就是撒谎。如果涉及的是想象中的人,那他尽可以说出想说的一切,而不算撒谎。除非他是从道义上来评判他所编造的事实,除非他是做出了虚假的判断。因为,他虽然在事实上没有撒谎,但他违背了道义上的真实,而这道义上的真实比事实上的真实更可敬百倍。
我见过一些被上流社会称为诚实的人,他们的全部诚实都用在无聊的闲谈中,诚实地列举时间、地点、人物。他们不许自己作任何假设,对任何情况都不加修饰,不做夸大。凡是与他们无涉的事情,他们都以最可靠的忠实娓娓道来。可一旦涉及到与他们有关的事情,谈及某个触犯他们的事实,他们便用上所有色彩,把事情尽可能说得漂亮,以获取最大的好处。倘若撒谎于他们有利,他们决不会禁止自己撒谎。不过他们说得巧妙,让人家能够接受谎言,而又没法怪罪他们。谨慎需要他们这样做:别了,真诚。
我称为诚实的人与他们显然不同。在完全无足轻重的事情上,虽然别人那么看重真实,他却对真实毫不在乎。他无所顾虑地编些故事,让大家开开心。那些故事无论对生者还是对死者,都不带任何不公正的评判。任何言论,不论对某人有利还是有害,是尊重还是轻蔑他,是夸奖人还是贬责人,只要与真理和正义相违,都是谎言,绝不会从他的心灵、嘴巴或笔下流出来。尽管他在无聊的闲谈中很少炫耀,但他确实是诚实的,甚至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他的诚实表现在他不试图欺骗任何人,无论是指责他还是赞誉他,他都依据事实,绝不弄虚作假。他绝不会为了自己的好处或者为了损伤敌人而撒谎。因此,我所说的诚实人与别人的区别就在于:任何真理,只要不需要自己付出代价,上流社会的诚实人就会忠诚不二,但不会越出雷池一步;而我所谓的诚实人,从来都是在必须为真理作牺牲时,才那样忠诚地为它效力。
但是,有人也许会问,怎么把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与我颂扬的真理之爱统一在一起呢?如果掺杂了那么多别的成分,这种爱岂不是假的?其实并非如此,这种爱是纯洁而真实的,但它只是正义之爱的流露,虽然常常也有虚构的成分,但它绝不愿意是虚假的。在诚实人的脑子里,正义和真理是两个同义词,此即为彼,没有丝毫分别。他心中热爱的神圣真理,并不在那些无足轻重的小事和毫无意义的名称上面,而在于严格地依照事实办事,该谁的就归谁,是什么事就什么事,指责也好,贬斥也好,荣誉也好,表扬也好,该怎样就怎样,该谁得就谁得。他不会为了反对别人而弄虚作假,因为正义感不许他这样做;也不愿意为了自己而不公正地伤害别人,因为良知阻止他这样做;他更不会盗窃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他尤为看重的是自尊,这是他最割舍不下的财富。为了获得他人的尊重而牺牲自尊,他认为是真正的损失。因此,他有时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会毫不犹豫地说些假话,他认为那不是撒谎,因为那绝不是为了害人或害己,也不是为了利他或利己。而在与历史事实有关的事情上,与人的行为、与正义、与人的社会关系准则、与有用知识有关的事情上,他会尽可能使自己和别人不犯错误。在他看来,在这个方面以外,任何撒谎都不算撒谎。如果《克尼德神庙》是一部有益的作品,那个译自希腊文稿的故事就只是个于人无害的杜撰;如果那部作品是有危害的,那个故事就是谎言,应该遭受处罚。
这就是我判定谎言与真话的规则。在我的理智接受这些规则之前,我的心灵就已经在无意识之中遵循它了。仅仅凭着道德本能,我的心灵就会把它付诸实践。我那次有罪的撒谎,让可怜的玛丽蓉受到伤害,它给我留下了永难抹去的内疚。在我的后半生,它不仅使我杜绝了这一类谎言,还使我避免了任何可能触犯他人利益和名声的谎言。由于我极力排斥撒谎,也就不必去权衡孰利孰害,以及在有害的撒谎与善意的撒谎之间划出明确界限了。我把这两种撒谎都看做有罪,一概加以禁绝。
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一样,我的气质对我的处世为人准则,更确切地说对我的习惯有很大影响。因为我几乎不按规则办事,或者说,我在任何事情上都只是率性而为。我从未事先在脑子里编造好谎言,也从未为私利而撒过谎。不过,我思维迟钝、谈吐贫乏,有时为了把交谈继续下去,不得不借助于虚构。没话找话来摆脱尴尬,出于羞耻,我常常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顶多和我个人有关的事情上编些谎言。当我必须说话,脑子里又不能尽快想出招人喜欢的真话时,我便胡乱编造一通,以免沉默。但是,在编造故事的时候,只要做得到,我尽量注意不使这些故事成为谎言,也就是说,不损害正义和真理,只是一些于人于己无害的杜撰而已。我的本意是至少以道义的真实代替事实的真实,也就是要在其中表现人心中的自然情感,并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一言以蔽之,使之成为道德故事。但这需要比我更聪敏的头脑和更健谈的口才,才能从交谈的絮语中引出教益。我的思想往往跟不上谈话的速度,因此,我几乎总是来不及思索,说出一些傻话。它们一出口,我的理性和感情就觉得不妥不宜,但已经无法将它们收回,通过理性的审查而予以纠正。
还是受这种气质原始的、不可抑制的冲动驱使,我在一些出乎意料的瞬间,常常因为害羞和胆怯而说谎。其实那并非出自本意,而是因为必须立刻答话,不得已而为之。可怜的玛丽蓉那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使我得以避免说出可能伤害他人的谎言,但并没有阻止我为了摆脱困窘,在只与我本人相关的时候撒一下谎。当然,撒这种谎和撒那些可能危害他人命运的谎一样,都是违背我的良心和原则的。
老天作证,如果能马上把为我开脱的谎话收回,说出将使我承担责任的真相,而不会使我再次受辱的话,我一定会尽心尽力这么做。但是,发现自己有错的羞耻心阻止了我,我虽然诚心诚意地悔过,但没有胆量去改过纠错。有一个例子,可以更清楚地传达出我想表达的意思,证明我撒谎并不是为了私利,也不是出于自尊,更不是由于嫉妒或恶意,而常常是出于难堪和羞耻,虽然有时我很清楚,这种假话肯定会被当做谎言,对我决没有半点好处。
不久前,我应富尔吉埃先生之邀,破例偕同老伴(卢梭当时同黛莱丝是同居关系,并未正式结婚)去瓦卡珊太太的饭馆,与他和他的朋友伯努阿聚餐。老板娘带着两个女儿也跟我们同席。大女儿已经于不久前出嫁,身大体胖,吃饭的时候突然盯着我问道,我是不是有过孩子。我一脸通红,答道,我还不曾有过这种幸福。她望着大家狡黠地笑了笑,其中的意思并不隐晦,连我也能体会出来。
显然,这个回答并不是我本想作的回答,虽说我或许是想让大家接受这个回答。因为,当我望着满桌宾客时,心里就已经意识到,我的回答肯定改变不了他们在这一点上的看法。他们指望我作出这个否定的回答,甚至为了享受逼我撒谎这种快乐而激起我这样回答。我并不麻木得连这点都感觉不到。过了两分钟,我才想出一种说法,而这本来就是我应作的回答:一个年轻女人,向一个尚未娶妻的老年男子提这样一个问题,显然不怎么审慎。这样说,我就既没有撒谎,也不会因没有承认事实而脸红,还会叫所有的嘲笑者都站在我一边,而且给了那女人一个小小的教训,从而不敢再那么放肆地向我发问。但我什么也没有做,该说的没说,不该说的,于我无益的,反倒说了。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我那个回答,并非出自我的判断,也非出自我的意愿,而是在窘迫之中,无意识作出来的。从前,我不觉得窘迫,能够以更加坦率的态度承认错误,而不觉得多么羞耻。因为那时我不怀疑别人看到了我的诚意,也不怀疑我内心的感受。但后来恶意害得我情绪失常,窘迫不安。我变得更为不幸,也变得更加羞怯。而我从来都只是因为羞耻而撒谎的。
我天生憎恶撒谎,在写《忏悔录》的时候,我更是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憎恶。因为,在写作时,只要我的倾向稍为偏向这方面,撒谎的念头就会不时地、强烈地冒出来。然而对于应由我承担责任的事情,我却并没有沉默或者加以文饰。出于一种说不清道不明,或许是不想仿效别人的想法,我觉得自己被驱使在相反的方向撒谎,因为我不愿过于宽宥自己,而是过分指责自己。我的良心向我保证,有朝一日我将受到的审判,不会比我自己已经做过的审判更加严厉。是的,我是由于心灵高尚,才这样说,才有这样的感受。我在《忏悔录》里倾注的真诚、真实和坦率,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感到我的善多于恶,所以我乐于把一切都说出来,我也说出了一切。
对于发生事件的场合,我从来没有少说,有时还多说几句。但对于事实却并不多言。这种类型的谎言与其说是出于意愿,倒不如说是出于想象中欲望的效果。称之为撒谎甚至是错误的。因为这类添枝加叶的话都算不上谎言。我写《忏悔录》时,人已经老了。那些虚浮的人生乐趣,我都尝试过了,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我只是凭记忆去写,但记忆常常不足,或者只让我回想起一鳞半爪的往事。于是我便用想象的、但并不违背事实的细节去弥补。我喜欢在一生的那些幸福时辰上流连,有时用深情的怀念来修饰它们。对于忘却的事情,我就把它们写成我觉得应该是或者实际上可能是的那样,但绝不与我的回忆唱对台戏。我有时会给真实的事情涂上种种奇特的色彩,但从未用谎言来掩饰恶习或者给我安上种种德行。
有时,我也没有想到,竟在无意之间,不自觉地遮掩自己丑恶的一面,而描绘自己美好的一面。不过这种缄默又被另一种更加奇怪的缄默完全补偿了。由于这种缄默,我隐自己的善比隐自己的恶更为经常。我的本性就有这样一个特点。读者不相信是情有可原的。但它尽管令人难以置信,却仍然是真的。我经常毫不留情地讲出我的恶,而讲到我的善,却总是有所保留,经常还闭口不谈。因为那会过于夸赞自己,好像我写《忏悔录》就是为自己歌功颂德。我描写童年的我,但并不炫耀心灵的优点,甚至还把过于衬托这些优点的情节略掉了。此时我想起童年的两件往事。写《忏悔录》时,我也曾清楚地回忆起了它们,但由于刚才提到的唯一理由,我把它们放在一边,没有写进书里。
那时我差不多每个星期天都到法济先生家去玩。法济先生娶了我的一个姑母,开了一家印花棉布作坊。有一天,我在轧花机房晾纱布,望着轧花机底部的铸铁轧辊,觉得那光泽十分好看,就把手放了上去。我快活地摸着那光滑的轧辊。这时,小法济钻进大飞轮,灵巧地将它转动了一点点,刚刚压着我两根最长的手指尖。指尖当即被压住了,两片指甲也一样。我一声尖叫,小法济立即把飞轮倒过去,但我的指甲已经留在轧辊上了。鲜血从我指尖涌出来。小法济惊慌起来,赶忙跳出大飞轮,抱着我,央求我别叫喊,还说这下他可完了。我虽然极为疼痛,但他的痛苦感动了我,我便忍住哭叫。我们来到作坊,他帮我洗净手指,又把苔藓捣碎,敷在指头上止血。他流着泪求我不要告发他。我答应了,并恪守了诺言,以至于过了二十多年,也没人知道我两根手指上是怎么落下的伤疤,因为那以后疤痕就没有消失。我告诉大家,我的指头是被天上掉下的大石头砸伤的。我在床上躺了三个多星期,有两个多月没法用手拿东西。
高尚的谎言,
难道不是可爱的真话?
然而,这个事故让我困守家中,无法行动,使我感到很不自在。当时,当局组织平民进行军事训练,我与三个同龄的孩子编成一行。我本来应该和他们一道,加入街区的连队,进行操练。听见连队敲着锣鼓从窗下经过,想到那三个伙伴也在队伍里,而我却不得不躺在床上养伤,我心里就十分难过。
还有一件类似的事件,发生在我稍大一点的时候。我和一个名叫普兰斯的伙伴在普兰宫玩槌球。游戏中我们发生口角,动起手来。他抡起槌棒,往我头上敲了一下。我没戴帽子,挨了这一棒,顿时倒在地上。这一槌还不算重,如果再加点劲,就会把我的脑浆打出来。可怜的小家伙看见鲜血从我头发中涌出来,吓得要死,那个惊骇模样,我从未见过。他以为把我打死了,便扑在我身上,紧紧地抱着,一边吻,一边呼唤,泪雨滂沱。我也哭着,也使出全身气力拥抱他,像他一样陷入既惶惑又略感甜蜜的不安之中。最后,他开始来给我止血。由于我们的两块手帕都不够用,他就把我领到他家。他家里附带了一个小花园。他母亲见我这副模样,差点晕了过去。但她打起精神替我包扎。她细心地把我的伤口洗净,敷上用烧酒泡过的百合花,这是我们家乡常备的治伤良药。她和她儿子的眼泪流进我心里。有好长时间我都把她看作亲妈,把她儿子看作兄弟。直到后来分居两地,天各一方,我才渐渐把他们忘了。
我把这两个事故都埋在心里,不对外说。类似的事故我一生中发生了不下一百次。我写《忏悔录》时,也从未打算告诉读者,因为我并不想极力突出我从自己性格中感觉到的好处。不,即使我说过与所知道的事实不符的话,那也只是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上面,或者更可能是由于讲话的窘迫,或图一时的笔头快乐才那么做,而绝不是出于任何谋私利或利人害人的动机。如果谁有可能,公正地读了我的《忏悔录》,一定会感到,我在书里承认的实情比承认一桩更大的但说出来不会这么丢人的罪恶还要困难。他还会感到,我之所以没有说出恶行,是因为我从不曾做过歹事。
从这些思考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我说自己诚实,主要是基于正直而公正的感觉,而不是基于事情本身,在对待具体问题时,我更多是遵循良心上的道德标准,而不是真与假的抽象概念。我经常编些趣事奇闻,但很少撒谎。根据这些原则,我不免会贻人许多口实。但我没有伤害任何人,也没有谋取不该得的好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才认为讲真话是一种美德。换了任何别的方面,对我们来说,真话就不过是一种超感觉的东西,从中产生不出任何善恶。
然而,对这样的划分,我觉得我的心并不怎么满意,所以不相信自己是完全无可指责的。在我仔细思量可能在什么地方亏负了他人的时候,有没有充分检查对自己的亏负呢?既然应该对别人公正,也就应该对自己真实。这是诚实的人应该还给自己的一种尊重。当我由于无话可说而用无辜的虚构作补充时,就已经错了,因为我不应该为取悦别人而贬损自己。当我为写作的乐趣所驱使,用编造的东西修饰真实的事情时,就更错了,因为以假话修饰真话,其实就是歪曲真话。
不过,使我更不可原谅的,就是我选定的那条座右铭(献身于真理)。它迫使我比任何人更注重说真话。光是到处为此牺牲个人利益和爱好还不够,还必须牺牲自己的弱点和羞怯的天性。在任何场合都必须有讲真话的勇气和力量。一个人的嘴和笔既然献给真理,就不能从那里流出任何虚构和无稽之谈。我在选定这个座右铭时就应该这样告诫自己。而且,只要我敢于坚持这个座右铭,就应该不断告诫自己。我撒谎从来不是因为虚伪,而是因为羞怯。但这并不能完全为我开脱,因为羞怯的人至多不会作恶,而大胆的敢作敢为的人才敢于张扬美德。要不是罗齐埃神甫的启发,我大概永远也做不出这些思考。要把这些思考拿来作用,大概已经为时太晚,不过,要纠正我的错误,让意愿重守规则,至少还不太迟。因为以后这一切都取决于我自己了。由此及彼,梭伦的箴言是适用于任何年龄的人的。从别人那里学习,甚至是从敌人那里学习,做个明智、真诚、谦虚,至少不那么自负的人,是永远不会太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