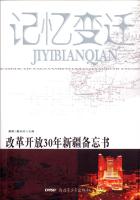田樾,1952年2月出生,辽宁辽中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诗集《情依然》、《记忆与浮雕》等,曾获第七届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现居北京。
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是一轮慢慢消隐的落日
只是那不被西风吹走的铃音和茶香
深深地嵌入峭壁山崖
茶马古道一路都是蜿蜒的情歌
只是那最断肠的一首
被牵马的情郎带进了孤寂天涯
一队队马帮驮着沉重呼吸
在高原这头,在峡谷那头
走过夏至,又走过冬至
客栈的墙壁上
依旧挂着勇士的弯刀
旗幡下依旧燃烧通宵的篝火
时光的拐角处
听得见远处飘来缠绵的歌儿
看不见古道上走来对情歌的人
那瘦削的马匹和蹄音
那古老的寨子和落下的烟尘
都衬出了历史雕凿的背影
我只是迟来的探访者,在茶马古道
我看见有位藏人捧来酒杯和哈达
以至高礼节,迎接走进茶马古道的客人
对峙的山水
此时
山空着,水空着
两张空椅子
相互对视如负重的弯弓
相互对视在阴阳的倒影
在山与水之间
一些画面被时间折射
犹如近距离的梦
宁静的原色,在山水中沉淀
时间被切割成一道道缝隙
语言在水流中慢慢干涸
胶着的岁月,被山水尘封
记忆的棱角上
正在开出缄默的花朵
临风而立
山水是一段错落的梦
在撞击中开始,在撞击中终结
山体从高处落下
水流从低处上升
苍苍秋水
刻下两双明亮的眼睛
时光的墙被山水打开
房屋已在侧面久久闲置
而岁月一直在烟雨中行走
而我一直没有看清立体的方向
山重水复
大寂犹听轰鸣
此时我用回旋的音画作山水浮雕
面向最简单的色彩
任凭一双瘦削的手
正把心室掏空
灰墙里的彩陶
潮湿而骚动的火光
被时间挤去水分
抽象的花枝
像停留在窗帘后面的女人
偶尔,飘过一点点留香
一点点剥落,像风化的果壳
一点点被抽去声音
静默附在陶器表面,
而躯壳已经开裂
汁液从高空滴落
睡姿被梦幻反复淘洗
花朵正在泥土中衰竭
残墙裹着孤独的眼睛
叶片的血色在夜晚消隐
在一阵狂风里
有谁听见岁月的啜泣
是什么隔开了油彩与服饰
尘封的荔枝,冷藏的柠檬
历史在空白的庭院缓缓移动
一条河流开始沉默
紫檀也收起久远的幻象
花落之中
命运变得无声无息
荒原
一双眼睛在远处凝视
在更高的地方
太阳躲入蜂巢的黑洞
只有鹰翼反射着火光
一个猿人在河岸徘徊
看狼群出没
看野花开放
五万年踅回孤独的脚掌
此刻
是谁在寂静之地
打造尖叫的陶器与钢铁
让天籁之音窃听今夜的思想
雨水还没有退去
风化的残垣正在剥落
蛛网密布的闪电
在一扇窗子上忧郁地流浪
我仿佛住在里面了
住进一间没有时间的房子
而且像橡树下的原始动物
梦境在体内无声地呼吸
又忽然像火舌般一跃而起
在更高的地方
我被冰冻在苍黄的角落
血液在坚硬中隐隐炸裂
最初的幻象也从此消失
无眠的康西
在音乐的边缘,你是
驶向关隘的
渐行渐远的马蹄
打马北上,总听见
一阵阵雁鸣在空旷中惊起
这么多原始的篝火
让千年古城,也微微颤动
这么尖锐的瞳孔
仿佛一直凝视
游移的天空
沿着草野的河谷
有毡房的体香被鬃毛扬起
把鞍鞯卸在水面,把梦
浮游在草原
让我在这月光的驿站
为烈酒醉成骁歌一曲
也在音乐上游弋
在空无睡意的夜晚
走过塞外和花朵
走过一生爱情的荆棘
一副弓箭搭上肩臂
而我已远离原始草原
而这里的风情只叫做康西
走过瑶里
徽州古道的驮铃还在响着
河边的水车还在转着
从深山到深山
一条路远比一条河更显得弯曲
一座座古窑址,还未冷却
漫山遍野长着瓷片和兰花
它们穿着民间服饰
它们正在讲述什么
古镇里的作坊好像只停息了片刻
我的眼前依旧浮现着挑瓷器者的身影
窑火通红,焚身炼火的女子
把每一件瓷器都贴上龙凤的图形
从宗祠到宗祠,从寺院到寺院
走进走出的都是梦幻与风尘
而瑶河水始终那样清澈
山里的恋歌始终那样动人
石板路的青苔还在长着
连接徽州古道,连接明亮的瓷土
民居沉淀在岁月深处,而只需轻轻召唤
便有别样风情呼之欲出
青石
河流上镌刻的文字
已从高空跌落
沉淀于光滑台阶
凝结成细碎脚步
埙声悠远而空廓
像日晷的余晖
在紫丁香中慢慢消隐
坚硬的火
吞没城池后面的裂痕
古籍堆积在宫阙细部
在幻灭的波光里
有胎动的女人孤单地走过
而青石沉默
没有响亮的声音
时光挤出尘世的脐血
挤进喧嚣的缝隙
青石只是一种荣耀的侧面
久久掩埋于历史深处
冰美人,双人冰舞
红叶飘落,蝴蝶飞起
旋转的火焰,穿越俄罗斯以及北美
穿越欧亚大陆明亮的水域
溜冰鞋搭成了看台
此时此刻,世界睁大了另一只眼睛
深邃的形体,演绎出
一曲蔚蓝,一曲紫红
一浪高过一浪的伦巴、卡门
在波涛中,穿越纱裙
是谁用炽烈的爱情,为柔韧写真
也是素描,但一定有速度的曲线
必须胶着,必须重叠
必须伸入磨合的内部
在胴体的巅峰
留下音乐环绕的身影
美艳之吻,何止两片花瓣
在乐曲休止之际,呼哨的焦点
还在起伏,更有一路潮湿的黑马
把最终的皇冠,戴上那
激扬青春
因为鹰
因为有个影子倏然掠过地面
我看见了天空盘旋着的鹰
因为看见了一只,又看见了
离它不远的另一只,因为有正午阳光
我看见了鹰的影子,也看见了
同时在天空盘旋着的两只鹰
同时我看见了它们锐利的目光
因为它们更早地看见了我
只是鹰没有发出声音
我也没有发出声音
我的目光伴随鹰的目光移动
由此我也发现了一条蛇,还有一只
比蛇狡猾的狐狸,只是它们
几乎同时钻入了洞穴
因为我正走过一片山地
长着一些阔叶,也长着一些荆棘
那里的地貌足以让它们侥幸藏身
因为鹰盘旋了一会儿飞走了
阳光也渐渐暗淡下来
我心情忽然感到莫名地失落
但只是片刻,我又忽然发现
漫天霞光把大地映得一片通红
——因为鹰
我又看了看自己留在地面的影子老巢(1962-)
老巢,原名杨义巢,出生于1962年,祖籍安徽巢湖。出版有诗集《风行大地》等。现居北京。
我的态度就是时间的态度
在你的句子里等你
看泡在杯中的绿茶一片片
沉入底部
客厅亮着
卧室与书房的灯
开与不开你到了再说
飞翔的鱼游泳的鸟
这种说法一点也不涉及
天空与海洋
作为老巢
我的态度就是时间的态度
来了去进了出
是早晚的事
用花朵死一次
用花花的手心长刺
心的花朵开花
花朵的牺牲是无知的开始
用花朵死一次
像春天死于花朵
用水澄清水中的水份
水份中的异己分子
当澄清由动词逐渐静止
水死于大海停顿之处
用水牺牲一次
像水死于老巢
老巢也是杨义巢
在一首诗的起笔时死
躺在家门口的宾馆里想家
这两天我住的宾馆
与我家之间
打的起步价就到了
家里人知道我回来了
就在这个城市
和一些他们不认识的人
干一些离他们很远的事情
我知道他们已做好了饭
等我回家吃
而我外面的酒还没有喝完
我的酒量已不如从前
我怕他们看我醉得不成人样
他们认不出我
具体的水
我在水中兑进别一种水
夜脱下我们的身体
我们用一盏灯
控制一房间的夜晚
用所有的灯
控制所有的夜晚
灯是水里的门诊
灯亮着我们就有救
水上过夜被身下具体的水
取消我们日常的权力
夜越深我们越有症状
在灯里点亮另一盏灯
我们被消毒
某种程度像我
生前我很孤独
孤独得想死
就掏出心
搁毒日下烤
搁泪水里腌
九月结出颗扁豆
某种程度像我
某种程度太理性
像我太俗气
比喻真是危险
聪明女人把婚姻当作鞋子
合不合适脚知道
鞋垫一般要有的
或单或棉
或薄或厚或药物
由脚在鞋里留下的
空隙而定
更聪明的男人
很自然同意这个比喻
并把鞋垫看成了
婚外恋情
舒不舒服脚知道
比喻真是危险
其实与脚体贴入微的是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