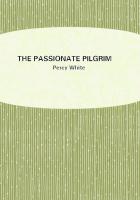安定规模虽少疏,然却广大着实;如陈古灵文字极好,尝见一丰碑说孔子之道,甚佳。此亦时世好,故此辈人出,有「鲁一变」气象。其后遂有二先生,若当时稍加信重,把二先生义理继之,则可以一变;而乃为王氏所坏。
幸有王氏,若早信重伊川,久已北辕东海矣。
问:「当时如此积渐将成,而坏于王氏,莫亦是有气数?」曰:「然。」
惟王氏未大被其害,惜救弊不胜耳。
胡安定、石守道诸人说话虽粗疏,却尽平正;如古灵文字都好,只如谕俗一文,极为平正简易。
为文字得此四字,可爱,为人、为治得此,更可爱。
孙、石辈忽然出来发明一个平正道理云云。孙明复恶胡安定。石守道只是粗,若其名利、嗜欲之类,直是打迭得伶俐。
连味数段,胡、石、孙大约胜周、程,大约未染禅宗,去道未远。惜其学无人传,不获见其详耳。安定之学则得孔子之正传矣,孙先生恶之,则别是一派也。
胡安定于义理不分明,然是甚气象。
试看孔子之门,「性与天道不可得闻」,惟以「三物」与及门「学而时习之」。宋人发明义理,正是达么义理之宗也。先生议安定于义理不分明,岂知正是安定过于周、程处乎?
「安定讲论今有传否?」曰:「并无。薛士龙尝以书问之,回书云『并无』,如当时取湖州学法以为太学法,今此法无。今日法乃蔡京之法。」又云:「祖宗以来,学者但守注疏,其后便论道,如二苏直是要论道;但注疏如何弃得?」
安定说得义理平正明白,无一些玄妙。近有一辈人别说一般惹邪的详说话,禅亦不是如此。只是不曾见那禅师,便是被他笑。
方叔珪称「本朝人物甚盛,而功业不及于汉、唐,只缘是要去小人」。先生曰:「小人如何不去得?自是不可合之物,观仁宗用韩、范、富诸公是甚次第。只为小人所害,及韩、富再当国,前日事都忘了。富公一向畏事,只是要看经念佛,缘是小人在傍故耳。」
人物甚盛,而功业不及汉、唐,有此理乎?或其所谓人物,非真人物也。又谓「只缘要去小人」,仆更伤心矣。世有恶衣菲食,昼夜焦劳,为社稷生民办边疆、选兵将之小人乎?世有袖手吚唔,不习行一业,不斡旋一事,间谈间着,在下在上皆苟安忍耻,岁币媚敌之君子乎?
陈烈【字季慈。】行甚高,然古怪太甚,使其知义理之正,是如何样有力量?惜其只一向从一边去。
季慈行高,使朱子目为「古怪太甚」,则其为学必有异于人;若知先生辈之义理,早为无用人矣,乌能佐十五太尉起兵匡济乎?
陈好行古礼,其妻厌之而求去。
元不才,勉行古礼四十年,妻妾无异辞,每以其无志期作女圣为憾。今见季慈之妻厌礼求去,乃觉天之福我妻妾之可幸矣。
神宗与群臣说话,往往领略不去。才与介甫说,便有「于吾言无所不说」的意思。可惜有「咸有一德」之君臣,而宋人之成习反胜。卒致大谋不就,三百年痼疾莫之或疗,殆天祚辽、夏、金、元而祸时夏,非人之所能为也。
何万着论云:王文正公当国以来,庙论主于安静,凡有建明,便以生事归之。英宗要改作,神宗尤欲更新天下,难得恰好却又撞着介甫出来承当,所以作坏得如此。
看是作坏。朱子亦不解此。
「荆公遇神宗,可谓千载一时,惜渠学术不是」。曰:「渠初来要做事,到后为人所攻,便无去就,不观荆公日录,无以知其本末,它直是藐视一世。」
宋家一世原该藐视。只有程明道、常彝甫颇晓此中滋味,而担当骨力又不足。
明道、横渠初见时,皆许以峻用。
明道、横渠在宋儒中原有可爱处,只不幸而生于宋,亦被人坏耳。
富韩公当再用时,与韩魏公在政府十余年,皆无所建明,不复如旧时;若范文正公当此,定不肯回。
弼原无本领,只是念佛人耳。看在政府十余年,一无建明,本色见矣。文正亦第文人之雄,非有为之人也,观办西事可见。
荆公作参政,第二日便措置理财,徧置回易库以笼天下之利,谓周礼泉府之职正如此。却不知周公之制只为天下之货有不售云云,初未尝以此求利息也。
孔明治蜀、交吴识力,人都不晓,只子敬颇略见的,孙权、周瑜皆梦昧如隔山。神宗、荆公苦心高识难为宋人道,故托周礼泉府法为之。其实一朝臣子,二百年南北史官,皆梦想不到肯綮处,皆开间囗,睁冷眼,指摘热肠人举动。呜呼伤哉!
国家百年承平,其实规模不立,特幸其无事耳,若有大变,岂能支耶!
既知如此,而不以荆公为是,何也?
新法之行,虽明道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但王氏行得来有害,若使明道为之,必不至恁地狼狈。
他处朱子皆明道、伊川为一,当时作史者亦无明文,不知大程与二程已是两家,与朱子更两家。但史书与宋儒书皆与荆公冰炭,吾亦谓明道亦犹伊川、朱子矣,见是编乃知明道不以新法为非。故荆公当群阻新法之时,独与明道议,特用为条例司。朱子既抹倒荆公经济,因明道望高,又不敢非之,故又为「使明道行之不至狼狈」之说。噫!古今是非,尽由书生之囗哉?
新法之行,荆公用明道作条例司,皆是望诸贤之助。想见其意好,后来尽背初意,所以诸贤不从。明道行状不载条例司事。
为何不载?书生之心,蔽偏甚矣。
神宗尝问明道云:「王安石是圣人否?」明道曰:「『公孙硕肤,赤舃几几』,圣人气象如此。王安石一身尚不能治,何圣人为?」曰:此言最说得荆公着。
观神宗一问,明道一对,吾许公为三代后第一人,殆不误矣。
圣人之问,以其德行、经纶兼优也;「公孙」之对,以其遭阖朝挠阻,不及周公处流言之变,不失其常度也。神宗之问固推拟过分,程子之对亦止言其非圣人耳,非贬斥也。
荆公德行,学则非。
直囗许荆公德行,朱子亦有不得不服荆公处;但学术不合,遂非之耳。岂知自己学术更非耶?
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正如医者将砒霜与人吃,云云。
荆公所办,正是宋家对症之药,即治疮之砒霜,破块之巴、黄,犹之治虚劳之参、苓也;惜为书生妄谈医理所乱耳。
因语荆公,陆子静云:「他当时不合于法度上理会。」语之云:「法度如何不理会?只是他所理会非三代法度。」
朱子只向文字囗纸上理会,亦是不理法度的;只与象山拗,便如此说,若遇荆公,他又囗说「正心、诚意」了。
问:「荆公节俭恬退,素行亦好。」曰:「他当时作此事已不合『中』,如孔子于饮食、衣服之闲,亦岂务灭裂?它当初便只苟简,要似一苦行然。」
当宋时,与宋君、宋臣而言「中」,便是乡原话。一代君臣,先生辈道学,并不曾上正路头去走,并言不得「过」、「不及」,更何从与之言「中」乎?荆公苦处只自知耳。吾友法干王氏为吾辩宋儒,明尧、孔旧道,怒叫曰:「兄真王安石也。」予曰:「然。荆公,赵家社稷生民之安石;仆,孔门道脉学宗之安石也。」如今世盈世章句、帖括,静坐、著述,文人耳;曾无一人在「三物」道上。只与讲「去囗笔,为习行」,「去禅宗,为经济」,尚敝舌无用,又何暇言莫紧「过」,莫漫「不及」乎?
荆公学术之谬,见识之差,误神庙委任。
若使公遇朱晦庵,必亦谓其学术谬,见识差,误孔子学脉,误宋朝士风。吾阅是编,敬服宋儒中两人矣。朱子心目中一人容不下,吕东莱却包得朱、陈两派,俱厚交终身。程伯子虽未能直接周、孔,而能陆王、朱许两派道学俱宗之。王荆公经济之儒,亦识见政事同志同才,能于乾坤中包括三路,岂可与书生、文人冒儒道者,同日语哉?
介甫心术隐微处都不曾攻得,却只是把持。
先生是另一等把持耳!
龟山长于攻王氏。
以无用学究误经世君子,杨时之罪上通于天,朱子偏称他「长于攻王氏」。吾人生两间,不思习行圣道,不去经世济民,只去囗舌攻人,孔门罪人也,不愧朝廷币聘哉!
王氏新经尽有好处。
凡朱子称许,皆是荆公短处。朱子乐与己合也。
陈后山说:「荆公学唤作转般仓」云云;东坡云:「荆公之学未尝不善,只是不合要人同己。」此皆说得未是。荆公之学自有未是处耳。
其未是处,亦是染于宋家文人、书生瘟疫也。朱子却正憾其不尽合宋人,指其是处为未是也。
荆公作字说,解佛经二段。
作字说,解佛经,荆公大谬处也。吾不遑问其是否,只做此工夫,便谬。
唐埛力疏荆公,对神宗前叱荆公,云云。初,埛附荆公,荆公不收用,故后诋之。埛初欲言时,就曾鲁公借钱三百千,后得罪逐,曾监取其钱而后放行。
埛真小人,疏荆公当朝恶数,称快腐儒之心矣。神宗不能斩之,不及桓公之任仲父远甚,乌能成一匡之烈哉?
荆公、坡公之学皆不正,但东坡之德行那里得似荆公。
朱子服荆公德行,亦有时服他学问,盖荆公大半与朱子同,惟到强宋,遂千里矣。
荆公后来全不用许多儒臣,也是各家都说得没理会。如东坡以前进说「要出来整理弊坏」,后来荆公做出,东坡又却尽的翻转云:「也无一事可做。」如拣汰军兵,也说「怕人怨」,削进士恩例,也说「士人失望」云云。
文人常态也。道学人无能为,又信囗翻转更甚。故孔子复生,亦以先变文人、书生、禅宗之习,而后人才出;亦必不听文人、书生、伪学之言,而后事功【以下阙。】
礼文手钞
序【颜元钞录家礼序作为礼文手钞序。】
子朱子曰:「凡礼有本有文。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则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其本也;冠、昏、丧、祭仪章度数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体,固不可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纪纲人道之始终,虽其行之有时,施之有所,然非讲之素明,习之素熟,则其临事之际,亦无以合宜而应节,是亦不可一日而不讲且习焉者也。
「三代之际,礼经备矣,然其存于今者,官庐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于世。世之君子虽或酌以古今之变,更为一时之法,然亦或详或略,无所折衷,至或遗其本而务其末,缓于实而急于文。自有志好礼之士,犹或不能举其要,而困于贫窭者,尤患其终不能有以及于礼也。
「熹之愚盖两病焉,是以尝独究观古今之籍,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于其闲,以为一家之书,大抵谨名分、崇爱敬以为之本,至其施行之际,则又略浮文,敷本实,以窃自附于孔子从先进之遗意。诚愿得与同志之士熟讲而勉行之,庶几古人所以修身齐家之道、慎终追远之心,犹可以复见,而于国家崇化导民之意,亦或有小补云。」康熙三年岁次甲辰八月戊寅后学颜元谨识
卷一通礼【此篇所著,皆所谓有家日用之常礼,不可一日而不修者。】
祠堂【议就四龛,当以高祖考妣居中,而曾祖考三龛以昭穆分列于侧后。考古礼官师祭二世。今世王制亦云士民祭二世,品官方许祭四世。宋儒所谓虽善不尊,况并列四龛,制亦不善乎?元家祠惟祖龛南向,祢龛侧设,二世而已。】
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祠堂之制三间,外为中门,中门外为两阶,皆三级。东曰阼阶,西曰西阶,阶下以屋覆之,令可容家众叙立。地狭者止立一间,不立库厨。东西壁置两柜,藏遗书、衣物、祭器亦可。】为四龛以奉先世神主。【祠堂之内以近北一架为四龛,每龛内置一桌。大宗及继高祖之小宗,则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继曾祖之小宗,则虚高龛;继祖之小宗则虚曾龛;继祢之小宗则虚三龛。非嫡长子不敢祭其父。】旁亲之无后者,以其斑祔。【伯叔祖父母祔于高祖,伯叔父母祔于曾祖,妻若兄弟若兄弟之妻祔于祖,子侄祔于父。皆西向主椟,并如正位。侄之妇自立祠堂,则迁而从之。程子曰:「无服之殇不祭。下殇之祭,终父母之身;中殇之祭,终兄弟之身;长殇之祭,终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无后者,其祭终兄弟之孙之身。此皆以义起者也。」补注按:祔位有一祔祭,有二盖。四龛神主,以西为上,四亲以次列之。其祔位皆西向,以北为上,此合男女而言也。至于祔祭,小小祭祀只就其处,四龛神主不动,但祔祭神主则以东西分男女。祭伯叔祖考祔于高祖考,西边,东向。祭伯叔祖母祔于高祖妣,东边,西向。祭伯叔父祔于曾祖考,西边,东向。祭伯叔母祔于曾祖妣,东边,西向。祭兄弟祔于祖考,西边,东向。祭兄弟嫂妻妇祔于祖妣,东边,西向。若大祭祀,则出四龛神主于堂或正寝,惟高祖在西边,南向,高祖妣在东边,南向,曾祖考、祖考与考皆西边,东向,曾祖妣、祖妣与妣皆东边,西向。祔祭神主,若伯祖则祔于祖考之上,叔祖则祔于祖考之下,伯祖母则祔于祖妣之上,叔祖母则祔于祖妣之下,伯父则祔于父之上,叔父则祔于父之下,伯母则祔于母之上,叔母则祔于母之下。正位神主与祔位神主皆分男女而言也。】
【置祭田法贵多其道。近世子孙分居者,祖父母、父母有养老地,卒后可因以为祭田。富而贤愿入田为祭田者,或立家法、入学中、入会、出仕,各置祭田若干。或族人无后者,当以其产为之立后,如人不愿,或无可立,则以为祖祠祭田。】置祭田。【初立祠堂,则计见田,每龛取其二十之一以为祭田,亲尽则以为墓田。后凡正位、祔位皆放此。宗子主之,以给祭用。上世礿未置田,则合墓下子孙之田计数而割之,皆立约闻官,不得典卖。】具祭器。【床席椅桌,盥盆火炉,酒食之器,随其合用之数,皆具贮于库中而封锁之,不得他用。无库贮于柜中。不可贮者,列于外门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