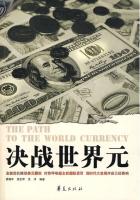第三回 吊故交闺阁间意 游竹林二士争风
话说荷花拿灯一照,只见菊英面如土色,牙齿紧咬,说道:“不好了。妹妹,你是怎的?”叫了半日,菊英方才略好些。睁目看见荷花在侧,眼目流泪说道:“姐姐,吾命休矣!”荷花说:“你觉的怎样?”菊英道:“方才吾见一个鬼,手提绳锁来索吾命,想来不可复生矣。”言毕哽咽。荷花遂将此事告于主母,素娥也觉凄惨。到次日,菊英遂气绝而死,素娥命人买棺木葬埋不提。
这素娥因作了夏姬,住了二载有余,遂生一子,名唤征舒,字子南。只因御叔是个好色之徒,朝朝相狎,夜夜欢淫,又加素娥有采战之法,精力渐渐耗散,容颜渐渐枯槁,又住了数日,遂一病不起。那日见夏姬在旁,遂含泪道:“卿有这等容颜,日后必不寂寞,但恨孩儿年幼,无人照管,恐不能独立成人。”言毕,伏枕而泣,遂命夫人叫了孩儿来。夏姬命人叫到。御叔嘱咐了些言语,又向夫人说:“此儿气宇非凡,日后要将此儿托于契友孔宁,使他照管他成人,至卿能守则守,不能守,任卿所为便了。”夏姬道:“相公放心,相公万在不虞,奴家决不再嫁,以玷门风。常言说:‘忠臣不事二姓,烈女不更二夫。’奴决不作负义之人。”御叔闻言,不胜欣悦。夏姬遂请名医给御叔调治。
忽一日,医生诊脉道:“此病不可治矣。”遂辞别而去。夫人闻之,号泣半晌。到了次日午时病故。夫人穿孝服,治办丧具,一面报灵公,一面报于各衙门。孔宁得了报,又暗喜悦道:“夏姬每日见我,常有恋恋之意,只因他丈夫在,未敢启齿。今御叔已死,少不得这肥肉是我口里的了。”遂急换了素服,去夏家吊丧。
一路走来,进了大门,直哭到内室,夫人亦哭。哭罢,夫人遂向孔宁道:“丈夫临终之时,曾向奴家说过,说他终身契友惟大夫一人,小儿征舒年幼,全仗大夫照管他成人。
一切丧具亦仗大夫料理。”说罢,遂嗑下头去,孔宁忙还了礼,说道:“吾嫂放心,此事全在小弟身上。”说罢,遂出外代理丧事。
到了日落西山之时,就在夏家住下。夏姬闻之,就命荷花送出一铺盖茶酒来。这孔宁心已久,坐在书斋正思勾搭夏姬之计,忽然荷花送茶酒出来,孔宁见他有一股风流体态,遂满心欢喜。迎着荷花,笑嘻嘻道:“谁叫你送来的茶酒?”荷花本是个伶俐风骚,惯与主母做脚线揽主顾的,遂笑容可掬说道:“主母叫我送来的。”那时又将秋波一转,颇带着送情的光景,惹的个孔宁欲火上升,且喜四顾无人,遂赶上荷花,抱在怀中亲了一个嘴。那荷花恐怕人来不好看,就抽身去了。孔宁此时怅怅如有所失,是夜一宿不寐,想出一条巧计来。自己笑道:“呀!可访着一条妙计,自古说的好,人不图财,谁肯早起,我明日与荷花些财物,他自然依从我了,我何愁他主母不到我手?”主意已定。
到了次日,绝早起来,走到家中取了些簪环首饰回来,仍旧替办事。到了晚间人静时候,荷花又送出茶来。孔宁喜的抓耳挠腮的笑道:“我的荷花姐姐。”荷花道:“叫我又吩咐何事?”孔宁道:“你服侍殷勤,无物可赠,我见你头上首饰稀少,特取些来与你可好么?”荷花道:“礼当服侍,怎敢要老爷的东西。”孔宁遂拿一个金漆盒递给荷花。接来打开一看,见有许多金珠东西。遂带笑说道:“
大夫赐贱妾如许东西,多谢了。”孔宁道:“不须谢,你进前来,与你说话。”荷花往前走了几步,孔宁搂到怀里,欲求云雨。荷花道:“此事等贱妾打发主母睡下,方敢私出。”孔宁遂放他去了。果然到初更时候,荷花黑夜走来,孔宁遂迎他进去,掩上房门,俱脱了衣裤,就在椅上分开两腿。灯光之下,看两乳高耸,孔宁用手拿尘柄照里一耸,这荷花是经过人事的,但未曾生育,虽不甚紧,亦不甚松,三抽两送必欲到根,渐渐深入,觉得荷花里边鸡冠兜裹,尘首如吞吮之妙,花心乱动,又紧抱孔宁之腰不住哼哼。孔宁只得按定那处,左摆右揉,弄的荷花淫声浪语无所不至。觉浑身酸麻,连着数次,又将嫩舌送过。孔宁吮之,舌尖一点冰凉,便知荷花尽兴,自己畅美,也就泄了。二人起来,从新睡在绫被中,共枕偎抱。
孔宁才托转于主母入马之事,荷花一并应承。孔宁道:“若要事成,重重的谢你。”荷花道:“我与主母悄悄说知,到起更的时候,我来叫你。”说完,天已五鼓,荷花说:“贱妾不敢久留,我要去也。”遂披衣开门,人不知鬼不觉,回到自己房中去了。
到了次日,果然将孔宁私通之事告诉主母。夏姬问道:“你曾与他交媾否?”荷花遂将夜间之事说了一遍,又将孔宁送他之物与夏姬看了,夏姬本是风流之女,那有不应允的,遂点头应诺,到了日落,孔宁仍旧住在书房,至起更以后,荷花果然出来,引他到绣房以上,夏姬恐人知觉,并未点灯,荷花引他床边,孔宁手一摸时,知夏姬仰臣就要上,不觉淫兴大动,尘柄昂然,即刻脱去衣服,翻身上床,夏姬用手搂抱孔宁就将偎到下边,觉得紧凑难入,如处女一般,半天方才进去一半,孔宁道:“奇怪,此人年已四十,又生过儿子,如何这等?
向夏姬问道:“娇娇,你是甚法,宛如处女?”夏姬道:“神人传的法。”孔宁暗自惊讶,说着,夏姬迎凑上来,直弄了一夜方歇。夏姬向孔宁道:“征舒已长成,做事不便,不如郎君领他在外从师读书,我回居株林,咱二人方可长远。”孔宁连声应诺。到了天明窃绣裤而穿,又住了几天,丧事已毕,孔宁遂将征舒领去,从师读书。夏姬退归株林,二人常相往来,无一人知觉。
一日,见了同事官仪行父,饮酒中间,遂将夏姬之事告诉于他,又将所窃绣裤释示于他。这仪行父与孔宁都是两个幸臣,素事灵公,耽于酒色,随主游戏,原是个酒色队里打锣鼓的。当日闻听此言,不觉心痒意乱。回到家中费了一片心机,以厚币结交荷花,求其先容。夏姬平日窥见仪行父,身材长大,相貌伟丰,也夙有其心。遂遣荷花约他私会。仪行父迎来助战,春药以媚夏姬。故夏姬爱之倍于孔宁。仪行父向夏姬道:“孔大夫有绣裤之赐,亦欲求一物为表记,以见均爱。”夏姬笑道:“绣裤彼自窃去,非妾赠。”因附耳说:“虽在同床岂无厚薄。”用自解所穿碧鸡襦送于仪行父,仪行父大悦。自此仪行父往来甚密,孔宁不免少疏矣。有古诗为证:
郑风何其淫,桓武化自渺;
士女竞私奔,里巷失婚姻。
仲子樯欲,子充性偏狡;
东门忆茹虑,野外生蔓草。
青衿萦我心,驾车去何杳;
风雨鸡鸣时,相会密乃巧。
扬水流束薪,谗言莫相扰;
习气多感人,安能有美好。
这仪行父得了碧鸡襦,也夸示于孔宁。孔宁私叩荷花,知夏姬与仪行父相好甚密,心怀妒忌,无计拆散。忽一日,偶在夏姬花园中散步,想出一妙策来。须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梨花园使女作媒 栖凤楼佳人增美
话说孔宁忽然想出一条妙策来,说道:“有了,我想灵公性贪淫乐,久闻夏姬之美,屡次言之,相慕甚切,恨不到手。不如引他入马,陈候必然感我。况陈有个暗疾,医书上名曰:‘孤臭。’点曰:‘腋气。’夏姬定不喜欢。我去做个贴身帮闲,乐得从中调情,讨些便易,使得仪大夫不便常来,出了我这点燃酸的恶气。”
“好计!好计!”
遂独见灵公,闲话说及夏姬之美,天下绝无。灵公道:“寡人亦久闻其名,但年纪已近四旬,恐三月桃花,未免改色矣。”孔宁道:“夏姬熟房中之术,容颜鲜嫩,如十七八岁好女子一般。”灵公闻之,不觉欲火上升。遂问孔宁:“卿有何术,使寡人与夏姬相见?”孔宁又奏道:“夏氏所居株林,是幽雅茂密,可以游玩,主公明早只说幸株林,夏氏必然出来相迎,夏姬有婢名荷花,颇知情事,臣当以主公之意达之,万无不谐之理。”灵公笑道:“全仗爱卿作成。”
次日传示,驾车游株林,只叫大夫孔宁相随。孔宁遂送信于夏姬,叫他珍馐相候,又露其意与荷花,使之转达那边。夏姬也是个不怕事的主顾,此时预备停当。灵公一心贪慕夏姬,把游玩当个名头。正是:
窃玉偷香真有意,观山玩水本无心。
不多时候就来到夏家。夏姬穿礼服相迎于厅前,拜谒致词道:“妾儿征舒出就外传,不知主公驾临,有失迎候。”其声如新莺巧语,呖呖可听,灵公视其容貌,真天仙一般,六宫妃嫔罕有其匹。遂向夏姬道:“寡人偶尔闲游,轻造尊府,幸勿惊讶!”夏姬对道:“主公玉趾下临,株林增色,贱妾备有蔬酒,未敢献上。”灵公道:“既费庖厨,不须礼席。闻尊府园亭幽雅,梨花正茂,愿一观之。主人盛馔就在园亭相扰可也。”夏姬道:“自亡夫去世,荒园久废扫除,恐屈圣驾,贱妾预先告罪。”夏姬应对有序,灵公心上愈加敬重,命夏姬换去礼服,引宾人园中游。夏姬遂卸了礼服,露出一身淡妆,如月下梨花,雪中梅蕊,别是一种雅致。
夏姬引至后园,却有乔松、秀柏、奇石、名葩、池沼一方,花亭几座,中间有一高轩,朱栏绣房甚是阔畅。此乃宴客之所,左右俱有回郎,轩后曲房数层,回郎周折,直通内院。园外有马厮,乃是养马之处。园西空地一片,俱是梨花馥郁缤纷,香气袭人。正一所好花园也。
灵公观看了一回,轩中筵席已备,夏姬执盏定席,灵公赐坐于旁,夏姬谦让不敢,灵公道:“主人岂可不坐。”乃命孔宁坐右,夏姬坐左。今日略去君臣之分,便好尽欢。饮酒中间,灵公目不转睛,夏姬亦秋波送盼。灵公酒兴带了风情,又有孔大夫从旁打和鼓,酒能畅怀,不觉其多,转瞬日落西山。左右进灯,洗盏便酌,灵公大醉,卧于床上,鼾鼾睡去。孔宁私对夏姬说:“主公久慕容色,今日此来立要求欢,不可执谬。”夏姬微笑不答。
孔宁由他便易行事,出外安置随众歇宿。夏姬整备缎衾绣枕,假意送于轩中。自己却香汤沐浴,以备召幸,只留荷花侍驾。少须,灵公醒来,张目问:“是何人?”荷花跪而应曰:“
贱婢乃荷花也,奉主母之命服侍千岁爷爷,因持酸梅醒酒汤以进。”灵公道:“此汤能为寡人作媒乎?”荷花道:“贱婢不会为媒典,颇能效奔走。但不知千岁爷爷属意何人?”灵公道:“寡人为汝主母神魂俱乱矣。汝能成就,吾当厚厚赐汝。”荷花道:“主母贱体,恐不足当贵人,倘蒙不弃,贱婢即当引入。”灵公大喜,即命荷花掌灯引路,曲曲弯弯,直入内室。
夏姬明灯独坐,如有所待。忽闻脚步之声,方欲启问,灵公入房内。荷花便将银灯携出,灵公便拥抱入帷,解衣共寝,只觉夏姬肌肤柔腻,着体欲融,欢会之时宛如处女。灵公怪而问之。夏姬道:“妾有传法,虽生子之后,不过三日,花房充满如故。”灵公便道:“寡人虽遇一面人,亦不过如此矣!”论起灵公尘柄,本不及孔仪二大夫,况又有狐臭之气,更没甚好,只因他是一国之君。夏氏也未免惧三分势力,不敢择嫌于他。枕席上百般献媚,虚间奉承。恐怕灵公气弱,叫灵公仰卧,自己骑在灵公身上,将两股夹紧,一起一落,就如小儿口吃樱桃的一般,弄得个灵公浑身麻痒,一泄如注。二人遂抱着共寝。须臾,灵公淫兴复作,挺枪又战,一夜之间,云雨七次。灵公浑身如散,四脚难举,力伴而睡。睡至鸡鸣,夏姬推灵公起身。灵公道:“寡人得交爱卿,回视六宫,犹如粪土!但不知爱卿有分毫及寡人否?”夏姬恐灵公知孔仪二人往来之事,乃对灵公道:“贱妾实不敢欺君,自丧先夫,不能自制,未免失身他人,今既得侍君候,从此当永谢外交,不也复有二心,以取罪戾。”灵公道:“爱卿平日所交,系何富贵?原爱卿悉述,不必隐讳。”夏姬道:“孔仪二大夫因抚遗孤,至于乱,他实未有也。”灵公笑曰:“怪的!孔宁说卿交接之妙,大异寻常,若非亲试,何以知之,但既告寡人,卿其无疑,惟愿与卿常常面见,此情不绝,其他任卿所为,不汝禁也。”
夏姬道:“主公能源源而来,何愁不常常而见乎?”须臾,灵公起身下床,夏姬抽自己贴身汗衫与灵公穿到身上,道:“主公见此汗衫,如见贱妾矣。”荷花遂由旧路送至轩下。天明后,厅上已备早膳,孔宁率众车驾伺候。夏姬请灵公登堂,登车问安,庖入进膳。从人俱有酒食犒劳。孔宁为灵公御车回朝。百官知陈侯野宿。于是,俱集朝门外伺候。灵公令免其朝参,迳入后宫去了。忽然重宫中闪出一员官来,叫了一声:“孔兄远来,我有话与你讲。”孔宁回头一看道:“呀!原是你。”要知此人为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陈乎国公堂戏谑 仪行父潜地杀忠
话说孔宁认的,是仪行父,见孔宁走来,遂一手拉住孔宁,走到隐僻之处,附耳问道:“主公在何处射猎?今夜在何处住下?以当实情告我,勿得隐瞒。”孔宁见不能讳,只得直言。仪行父知是孔宁荐,顿足说道:“如此好事,如何让你去做?”孔宁道:“主公十分得意,第二次让你做好事便了。”二人大笑而散。
到了次日,灵公早朝礼毕,百官俱散,召孔宁至前,谢其荐举夏姬之事成。召仪行父问道:“如此乐事,何不早奏于寡人,你二人却占先头,是何道理?”孔仪二人奏道:“臣等并无此事。”灵公道:“是美人亲口说的,卿等不必讳矣。”孔宁道:“譬如君有味,臣先尝之,若尝而不美,不敢荐于君也。”灵公笑曰:“譬如熊掌,奇味就让寡人先尝也不妨。”孔仪二人俱大笑不止。灵公又道:“你二人虽曾入马,他偏有物送我。乃脱下衬衣示之,“你二人可有么?”孔宁曰:“臣亦有之。”孔宁遂撩衣,现其绣裆。道:“此非美人所赐乎?不但臣有,行父亦有。”灵公问:“行父是何物?”行父解下碧鸡襦与灵公观看。灵公见之,大笑道:“我三人随身俱有证见,异日同往株林,可作连床大会。”一君二臣在朝堂戏谑。
这话早传出朝门外。恼了一位正直之臣,咬牙切齿的道:“朝廷纪纲之地,都如此胡言乱语,是何道理?陈国之亡,屈指可待矣。”遂复身入朝门进谏。正是:
自古忠邪难并立,徒怜比千志节高。
却说一君二臣正地朝堂戏谑,忽见一人执笏赶进朝门。三人瞪目视之,见是泄冶。孔仪二人素惮泄冶正直,今日不宣自至,必有规谏。遂先辞灵公而出,灵公抽身欲起御座,泄冶连忙上前拉其衣而奏曰:“臣闻君臣主敬,男女主别。今君臣宣淫,互相标榜,失君臣之敬,无男女之别,沦灭已极亡国之道也。君必改之。”灵公自觉颜汗,随曰:“卿勿多言,行且悔之矣。”泄冶辞出朝门,孔仪二人尚在门外打听。见泄冶怒气冲冲而出,闪入人空中避之,泄冶早已看见。将二唤出责之曰:“君有善,臣宜宣之;君有不善,臣宜掩之。今子为不善,以诱其君,而又在朝堂扬其事,何以为训,宁不羞乎?”二人不能措对,虽谢教。泄冶去了。
孔仪二人又来见灵公,述泄冶责备之语。遂道:“主公日后不可游株林矣。”灵公道:“卿二人还往否?”二人笑道:“彼以臣谏君,与臣无涉,臣等可往君不可往。”灵公奋然曰:“寡人宁得罪于泄冶,安肯舍此乐地乎?”孔仪复奏曰:“主公若往株林,恐难当泄冶强极之谏。”灵公道:“二卿有何策,令泄冶勿言?”孔宁道:“除非使他不能开口。”灵公道:“彼自有口,寡人难禁之不言。”仪行父道:“孔宁之言,臣知其意,夫人死则口闭。主公何不传旨,杀了泄冶,则终身之乐无穷矣。”灵公道:“寡人不能。”孔宁道:“臣使人刺之何如?”灵公曰:“卿可自为。”
二人出朝,一处商议,行父道:“昨日有司奏一犯罪的强盗,秋后处决。吾见其人凶悍异常,若能赦他死罪,再赏他几两银子,他必欣然愿为。”孔宁道:“此人叫甚名字?”仪行父道:“名张黑夜,因独自进楼院,杀了看家的家丁,因此犯罪,若用此人,必能成功。”到了次日,孔宁见了灵公说:“有一犯罪强盗,主公赦他的死罪,他必能去杀泄冶。”灵公沉吟一时,遂写旨一道,递于孔宁。孔宁接旨,出了朝门,到了仪行父家中,将旨递于仪行父,即着人传旨,速提张黑夜至此处听审,不多一时,将张黑夜提到仪行父堂下。行父命左右回避,与孔宁亲解其缚,用手扶起附耳说道:“如此,如此。”到了次日早朝,百官毕上,张黑夜遂伏于半途扼要之处,专候泄冶不提。
却说泄冶朝罢退出朝门,忽然一阵头昏,目跳肉战,自己也不知何为,有跟随的一个家人,名唤李忠,见主人这等光景,遂问道:“相公是怎的?”泄冶道:“吾亦不知?”李忠道:“
莫非家中有事。”李忠遂急扶泄冶上马。正走之间,忽见一人自松林内跑出,一手将泄冶扯下马来,举刀便砍。李忠看见大声喊道:“你是何人?辄也行凶?”黑夜看李忠渐渐赶到,即回手一刀,将李忠砍到在地。泄冶见把李忠杀了,早已魂飞天外,三舞两弄被黑夜一刀砍倒。割下头来,用布包好,匿于怀中,来见行父。行父大喜,赏银五十两。纵使归家。此时只有孔仪二人知道,外人俱不得知。二人又私奏陈候,陈候亦喜。泄冶死,国人皆认为陈候所使,不知为孔仪二人之谋。史臣有赞曰:
陈丧明德,君臣宣淫;簪缨组服,大廷株林。
壮哉泄冶,独天直音;身死名高,龙血比心。
自泄冶死后,君臣更无所惮,三人不时同往株林。一二次还是私偷,以后习以为常,公然不避国人。作株林诗以讽之。诗曰: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
征舒字是子南,夏人忠厚,不曰夏姬,而曰夏南也来也。陈候君臣三人,和局间欢。未知将来如何,下回分解。
朝朝相狎,夜夜欢淫,
回廊周折,直通内院,
荒园久废扫除,俱是梨花馥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