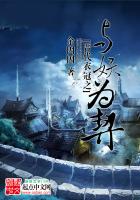且说章秋谷在莫愁湖亭上徘徊了一回,看着那几朵开残的莲花,赏玩一会。又看着中山王和莫愁的小像,细细的端详一回。只见一个是白面长须,英姿照日;一个是风鬟雾鬓,倩影惊鸿。秋谷见了,不免也有些心中感慨起来。在湖亭上泡了一碗茶,坐了一回,直到红日西斜,晚风吹袂,方才慢慢的回来。又在寓里头过了几天,已经到了八月初旬的时候。秋谷到了这个时候,便也未免要抱抱佛脚起来,把那些带去的书籍翻出来,略略的看了一遍。知
这一天正在寓里头静静的坐着,忽然又来了一个同乡朋友叫作黄少农的,要拉他去钓鱼巷吃酒。秋谷心上狠有些不愿意去,只推说身体有些不快,不能出门。黄少农不由分说,拉着就走。拉到钓鱼巷一个韩家老班里头,便有一个倌人出来应酬,秋谷抬头看时,只见这个倌人生得圆圆的一个脸儿,觉得团头团脸的,也晶评不出什么好歹。黄少农却得意洋洋的指着那倌人对秋谷说道:“这是南京有名的韩家小翠子,你看他生得怎么样?”秋谷又细细的打量了小翠子一眼,觉得虽然没有什么奇形怪状的丑相,却也没有什么娇娆袅娜的姿容,不过勉勉强强的看得过去罢了。看了一看,没本事说他不好,只得勉勉强强的说一声“好得狠”。黄少农听得秋谷赞他的相好,心上二十四分的高兴。小翠子也扭扭捏捏的扭捏出许多的身段来。秋谷看了,只是暗暗的好笑。斋
黄少农略坐一坐,便取过笔砚来,写了几张请客票,叫了男班子的掌班进来,身边摸出一块钱来,连着请客票一古脑儿都交给他,口中说道:“这一块钱是给你的车钱,快些去给我请客。”那男班子答应一声,接了过去。章秋谷看着,已经觉得二十四分的诧异。正要开口,忽然又见小翠子抢步过来,斜着眼睛把那男班子手里头的请客票看了一眼,半笑不笑的对着黄少农道:“你请的客人狠多,给他一块车钱只怕不够罢?”黄少农听了点点头,连忙又拿出一块钱来交在那男班子的手内。只把一个章秋谷看得心上更加诧异,真个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古
一会儿客人到了,排上席来。黄少农见秋谷没有相好,想要荐个相好给他,秋谷再三再四的推辞。黄少农那里肯听,不由分说,硬硬的荐了一个什么薛亚仙给他。章秋谷举目看时,只见这个薛亚仙生得矮矮的一个身材,匾匾的一个脸儿,眉眼不甚周详,鼻梁有些四塌,也是个中等以下的人材。秋谷见了,把眉头皱了一皱,也不言语。黄少农却指着薛亚仙向秋谷道:“你不要轻看了他,这也是南京地方大名鼎鼎的人物。”秋谷听了,不觉鼻子孔里“哼”了一声。黄少农又对着薛亚仙道:“这位章老爷在上海的时候,嫖界里头狠有声名的,你须要好好的应酬,将来我还要吃你的喜酒呢。”古
薛亚仙听了,把手帕子掩着嘴笑了一声,回过头来,上上下下的把章秋谷不住的打量。章秋谷被他看得不耐烦起来,别转头去。原来薛亚仙见了章秋谷这样的少年英俊,气宇非常,心上倒着实有些垂涎,便存着个屈身俯就的意思。见章秋谷只是淡淡的不理他,便故意找些话儿说出来和章秋谷讲,章秋谷也只得随随便便的应酬几句。一会儿,竟撒娇撒痴的拉拉扯扯起来,对着章秋谷不住的扭头掉颈,卖弄风骚,做出无数的丑态来。章秋谷看了他这般做作,不由得心中暗暗好笑,觉得甚是肉麻,周身的鸡皮疙疸都森森的直立起来,心上二十四分不愿意,只得假托腹痛;出了席去躺在榻上。无奈这位薛亚仙紧紧的跟着,问东问西,十分的献勤讨好,直把一个章秋谷拘束得如受桎梏,如坐针毡,又好笑,又好气,却又说不出来。好容易巴得薛亚仙走了,方才如释重负,畅快非常。黄少农糊里胡涂的,还对着章秋谷把大指一竖道:“何如?我荐给你的人不错么?你们两个人初次相逢,就是这般的要好,论理该应谢谢媒人才是。”古
章秋谷正含着一块烧鸭在嘴里还没有咽下去,听了黄少农这番说话,再也忍不住,“扑嗤”的一声一口气冲上喉咙,要笑出来。口中的这块烧鸭就留不住了,“扑”的从口中直飞出来,刺斜里飞过去,直飞到一个十四五岁的雏妓面上。说也凑巧,刚刚不偏不倚的直中在他鼻梁上面。大家都哄然大笑起来,秋谷自己也觉得十分好笑。连忙看那雏妓时,原来是一个姓杨的客人叫的,却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正默默的坐在那里,不提防一块烧鸭劈面飞来,刚刚飞在鼻梁上面,躲闪不及,只得把头一偏,那块烧鸭就落在地下。那雏妓出其不意,倒吃了一惊,连忙用手巾往脸上按了一按,身边取出镜子腮了一照。见面上油了一块,连忙讨盆脸水抹了一把,口里头喃喃呐呐的说了几句,也不知说些什么。斋
章秋谷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等他抹过了脸,便走过来对着他就是深深的一拱到地。那雏妓倒吃了一惊,口中说道:“这是怎么!这是怎么!”章秋谷立起身来,口中说道:“方才一个不小心,把一块烧鸭直飞在你的脸上,特地来和你陪个礼儿。“那雏妓微微一笑道:“这也算不得什么大事,何必这般客气?”章秋谷听了那雏妓说话的声音十分圆转清脆,不由的抬起头来把他打量一下。只见他高高的挽着一个云髻,淡淡的画着两道蛾眉,檀口含朱,横波挹翠,身材纤小,骨格停匀,虽然不是什么倾城倾国的佳人,却狠有些宜喜宜嗔的丰态。比起那小翠子和薛亚仙来,直是天壤云泥,相差甚远。秋谷看了,不由的心中动了一动,暗想:这个地方一般也有这样的人材,可见天地生才,原是不拘资格的。想着,便故意上上下下的把那雏妓细细的看,看得他脸上红起来,啐了一口道:“你上上下下的看些什么?难道要和我画个小照,回去供在家堂里面么?“秋谷笑道:“你不要见怪,像你这样的标致人儿,就是多看一会,也是前生修来的福分。”斋
看官听着,原来天下的女子,只要听得别人赞他貌美,心上总是高兴不过的,何况是个堂子里头的人物?听了章秋谷这几句话儿,不知不觉的酣迷迷、软洋洋,钻进心坎里去,登时春风满面的对着秋谷道:“你不用这般混说,像我这样的一个人,那里合得上你们的眼睛?”章秋谷笑道:“阿唷,你不用这般客气!若再要这般的谦让起来,把这里的房子牵得坍掉了,却不与我相干。”那雏妓斜着眼睛瞅了他一眼道:“算是你一个人会讲话,快些去坐了罢。”说着,便轻移莲步,慢慢的走过去,刚刚和章秋谷擦肩挨过。章秋谷趁着众人不见,暗暗把他手拉了一把。那雏妓秋波澄澄的也不言语,只把嘴对着那姓杨的客人努了一努,又摇了一摇头。主
秋谷会意,便也慢慢的归座,悄悄的问黄少农:“这个雏妓叫什么名字?”少农大笑道:“你敢是看上他么?他叫银喜,就是这里韩家本班的。我来和你们做个介绍人,转一个局就是了。”秋谷听了,便回过头来看了那姓杨的一眼。只见那姓杨的满面怒容,正襟危坐,只当没有听见的一般。秋谷知道那姓杨的醋劲发作了,连忙朝着黄少农连连摇手。黄少农看了姓杨的这般模样,料想这个媒人不是轻易做得成的,便也笑了一笑不说什么。只凭着这个章秋谷和银喜两个人在席上眉黛传情,秋波送睇,案底之莲钩暗蹴,尊前之宝靥轻回。大家都在搳拳吃酒的十分热闹,却没有看见他们两个人的这番情景。只怕自此以后,竟是这般的暗渡蓝桥,私谐鸳侣,也未可知。知
这且不必去说他,只说章秋谷在寓里头休息了几天,准备着秋风一战。到了初八日进场的那一天,秋谷进了号舍。那跟进去的家人把号帘挂了起来,钉好了号围,又把食篮收拾好了,笔砚纸墨都取了出来,方才出去。秋谷在号里头没有什么事情,便立在号门口闲看。看了一回,忽然见隔壁号里钻出一个人来,赤着膊,盘着辫子,一张漆黑的脸儿,两个绝高肩膀,粗眉糙目,一部大大的连鬓胡须,走出号舍,刚刚和秋谷打个照面。秋谷鼻子中间,就觉得有一阵汗臭和着那一股狐腋的臊气直冲进来,秋谷连忙别转头去掩面不迭。主
只见这个人走出号舍东西张望了一回,忽然又走进号去,捉出一个绝大的鸭子来,左手拿着一把明晃晃的牛耳尖刀,右手把那鸭子紧紧的捺在地下,那鸭子还叫个不住。章秋谷看了觉得十分诧异,不由得走近一步细细的看他。只见这位宝贝左手拿着刀,调转右手,照着那鸭子的项下就是一刀,鲜血直冒出来。那班同号的朋友见忽然有人在这里杀起鸭子来,也觉得甚是诧异,大家都赶过来看他。只见他揎拳掠袖的,向号军要了一瓤热水,把鸭子的毛持得干干净净。又拿出一个瓦罐,生起一炉火,把那鸭子慢慢的煮起来。正是:斋
出门一笑,秋风吹桂子之香;下笔千言,璧月吐奇葩之彩。主
未知以后如何,请待下回再行交代。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