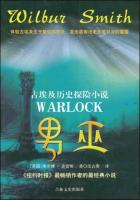界平感觉自己像拉磨的驴,两眼蒙住,兜着一个地方转,一转就是八个小时。她往宿舍走着,鞋跟有节奏地敲打着水泥路面。街道悠长地伸进了橱窗的侧镜里,这种虚幻的延伸像电影镜头般演绎着大街上的故事:一辆从左向右经过的汽车会陡然消失,街道沉着地等待着它,可它不再出现,如掉进了黑洞一般;另一辆汽车,从相反的方向突然开来,也消失在镜子里。
镜子的幻影混乱了她的思维,她想理清马柱的问题,可大脑混浊得像泥浆。很长一段时间,她聆听内心纷纷扬扬的雪片,滋生心底的寒气冻结着发梢。生的困惑、身体的欲望以及心灵的贫血,让她迷失了双眼。路边是新华书店,她像只觅食的小鸡,隔着玻璃窗向里斜溜一眼,抬脚拐了进去。
这里人少,安静,飘着淡淡的油墨香味。界平随手翻着一本散文。书架拐角处,一位军人也在翻书,那翠竹般挺拔的身材,劲松般坚毅的形象,还有那专注的神情,界平内心突然波澜翻涌,周身如电流激荡。任何一位挺拔的穿军装的男人,都会让她毫无防备地想到高顿。界平惊诧于浑身涌动的舒爽、陶醉,她痴迷地沉浸在军人英武的幻觉里。现实和幻觉纠缠着她的神经,蹂躏着她的血脉,她感觉双颊发烧,手心出汗,双膝发软。
书店里爆发出尖锐的争吵声,原来一位八九岁的小男生买了一本漫画书,出书店时被服务员拦住了,漫画书里还夹杂着另一本书。服务员指责他是小偷,小男生脸红得像晚霞,强辩说他表哥刚才替他交了书费的。
饿汉是聋子,强词有时可以夺理。
“你表哥呢?不会没出生吧?”服务员质问着。
解放军放下手里的杂志,走到门口,“您好,老总。”
服务员听到这天外飞来的头衔,受宠若惊,殷勤趋奉。解放军拍着小男生的肩膀说:“小强,怎么不等着我。”
小强含泪望着付费的解放军。
军人的侠义之举犹如新出炉的烤地瓜,香气迅速弥漫。界平悄悄拿起解放军放在柜台上的书,似乎有靠近军人的错觉。那是一本国际时事杂志。她毫不犹豫付了账,不管是否喜欢,今天,她买的是感觉。
拿着那本透着油墨气息的杂志,走在青石板路上。一位拉二胡的艺人正专注而悠扬地拉着《二泉映月》,音乐悠扬而凄美,灰白的山羊胡子,起了毛边的中山装,以及那和善而无原则的五官,给人一种同生同乐的亲切感。老人坐在马扎上,一把陈旧的二胡支在腿上,微闭双目,如痴如醉,身子随音乐起伏着。不时有行人驻足丢下一些零币,他并不理会,也不在意,依旧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中。这行云流水般连绵起伏的旋律,犹如在倾诉人世间的辛酸苦辣、坎坷不平。界平掏出仅剩的五角纸币,放在艺人前面的生锈而发黑的铁盒里。
一位十七八岁的脸上有刀疤的男子走到拉琴的老人面前,推开界平,弯腰拿起铁盒,一把抓净纸币,随后又将硬币像倒豆子似的倒进自己的衣袋里。
抢劫老人,真卑鄙。
“喂,放下!不然我打断了你的鼻子。”界平还没开口,一位中年男子一把扯住了刀疤男子的衣服。
“小心他打断你的腿!他是我爹,会少林拳!”
老艺人睁开了蒙眬的眼睛,冲中年男人点了点头。围观的人群散开,该干吗干吗去了。
界平觉得那音乐不再那么美了,尽管整个过程老艺人都没中断《二泉映月》的旋律。
“人是世上最好和最坏的动物。”回家的路上界平这样想。
济南的盛夏,清冽甘美的泉水从地下涌出,汇为河流和湖泊,家家泉水,户户垂杨。趵突泉、黑虎泉等汇集的护城河,深不见底,清澈甘甜,垂柳依依,荷香四散。
界平的内心像风景般的秀丽,那杂志像抛光过的玉石,由于无法想象的原因,在界平的手里熠熠发光。她抱着杂志,像抱着一个陌生的小世界。界平依在被子上翻着新买的杂志,那火药味十足的东南亚局势、新奇的异国风情,吸引着她。突然,一幅照片让她把眼珠子差点瞪出来:高顿陪美女站在阳光灿烂的游艇上,高顿穿着军装,搂着穿着黄色连衣裙的美女,他们脸上荡漾的笑容海洋般湛蓝透明。
界平所有的坚强像海浪冲击的沙堡,瞬间粉碎了。妹妹的冤死,自己未婚先孕的艰难,以及孩子夭折的悲痛,终于像灼热的子弹,击穿了她的胸膛。她没发觉流下泪水,她倒希望能淌尽最后一滴血。她羞愧、煎熬、惴惴不安,仿佛身体里沸腾着疼痛的火山,正烧灼着她的青春和生命。她终于丧失了对肉体、精神和梦想的全面掌控。
长篇通讯报道了高顿如何练就成了军事人才、战争英雄,顺带介绍了他一见钟情的婚姻,女方是部队文工团的演员。
界平由着自己滑入痛苦的深渊,谛听深渊里坠落的风声、死亡的哀鸣和种种破碎的响声。她曾坚信他的爱,给他的离开编造了许许多多可信的理由,只要他能出现,她依然会毫不犹豫地扑向他的怀抱,抛弃所有怨怒和悲伤。然而她期望的正是他稳如磐石的弃绝、遥无音信的背叛、卑鄙的操行。她一点也没有想到,花容月貌,风魔人心,爱情已走出她的生命。她看着杂志上被记者偷拍的照片,心好似炮火轰炸后的土地,硝烟还没有散尽,默默不作声的蜘蛛,已在暗地里结网,侵占了内心的每个角落,吞噬了她所有的欲望。
可以丢掉一切,但绝不能动摇希望。高顿一直是她坚强的希望,是她生命的氧气。她可以不要历史,不去回忆艰辛的过去,可以忽视养父猥亵的摧残,忍受马柱的恐吓,甚至,忍受命运赐予她的一切灾难。她相信有一天高顿会突然回到她身边,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而今,他的爱情果然碧海蓝天、星光灿烂,甜蜜得像五月的花海,幸福得像雨后的彩虹,可女主角却换了别人!
绝情绝义!
再没有比打碎希望更残酷的事情了。希望是蛋壳,壳不存,蛋清和蛋黄必然随之消亡。那天夜晚,在刘紫荆甜美的酣声里,界平想到的都是各种各样的悲惨故事,包括那位拉二胡艺人的不孝儿子……
这世界还真是在病中!这不是她梦想的世界,但这就是世界。手放在钢琴上并不意味着音乐,拥有过爱情并不等于拥有爱人。今夜,天空和她一起精神错乱。她额头滚烫、脚踝发软。那美好的爱情,将永远埋葬在过去的时光里。真情换回的是猜疑和谎言,然而从他的世界离开又是多么困难。她巴望着变成一滴雨,消失在河流里、淹没在夹缝里。
泉城一夜暴雨,夜深的风像巫婆的披风,惊雷滚滚似炮火轰鸣。黑暗中影影绰绰,摇曳披拂,忽儿竖直,忽儿倾斜,仿佛巨大的黑浪,翻滚向前。河流暴涨,街道似川,狂风得意忘形地肆虐着,仿佛这是人间地狱。
钟的秒针奔跑着,就像一只凶狠的藏獒,扑向垂涎已久的时刻。界平影子般急匆匆钻进了暴风骤雨里,像射向靶心的箭,奔向护城河……雨,雨……只有那淋漓的雨才能冲刷她的烦恼……只有那狂暴的风,才能席卷她的愤怒……
杨柳疯狂地抽打着,河水像发狂的魔鬼拍击着巨浪,溅起凶恶的愤怒。小船斜翻在浪涛里,转瞬不见了踪影。界平站在护城河的桥上,双手紧紧握着护栏,狂风撕扯着她的头发和衣衫,像要剥夺她仅存的尊严。她意识到这承受风雨的洗礼不是今天才决定的,而是在很久以前,当她站在妹妹的墓前、当高顿离开、当失去婴儿的瞬间,她都曾想让淋漓的暴雨洗净自己的骨骼和灵魂。闪电在夜空炸亮,天地通明,高高的桥头上,界平火红的衣裙、披散的长发和晶亮桥面、愤怒的河水,成了独特的风景画。
“每个人心里都有自杀的种子,但绝不是我!”
突然,惊雷炸响,狂风吹得护栏咔咔作响,界平来不及撤离,随着破碎的护栏,被卷进了滚滚的浊流里。
天漏泉城,大街小巷积水如川,商店、教室雨水倒灌,地势低洼的房屋像沙堡似的倒坍了。
军队紧急行动,抗洪抢险。一支连队沿着护城河向低洼居民区冒雨急进。突然,白光光的闪电劈开黑云。一个红衣人坠入河里,像电影镜头,赤红的颜色随着惊雷,没入黑暗中。连长张连喜收住脚步,喊了句“救人”就跳入了湍急的水里,瞬间没了踪影。另有一位叫崔加的战士,也像鲤鱼似的没入水中。
河水浊浪滚滚,势如破竹,凶恶地扫荡着一切。战士们焦急地望着河面,不见张连长和崔加。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水系的黑色偶然,模糊不定的波浪突然出现又漠然消失,一轮轮地涌来抹去,好似魔鬼的戏法。
一分钟、五分钟……绝望蹂躏着战士们的心。
突然,在洪水翻卷的岸边,露出了三个人头。士兵们像看到太阳一般惊喜,从张连长和崔加的手里接过了昏迷的女人。
界平被战士们送到了就近的部队医院。
愤怒的天空终于恢复了平和的性格,露出了热情的笑脸。阳光清新而热情地照耀着泉城,幸存的鸟儿欢快地在枝头鸣叫,凉爽的南风越过千佛山,扑面而来。仿佛昨夜不过是一场没有色彩的梦。
界平一直昏迷不醒。时间是失踪的面具,现实生活如同宏伟的海市蜃楼被风雨扯破了,背景弥散,露出水雾的原始形态。
张连长也不知道这女子叫什么、哪里的人,那入水的一团红色,是被风吹的还是自己跳下的?
界平慢慢睁开了眼睛,梦游似的看着前方。草原尽头,月亮升起,又圆又红,一队人字形的大雁从月亮上飞过,片片云影像彩带,浮在月亮周围,左遮遮,右露露,月亮终于升到清冷冷的天空,白晃晃一片晶莹,朝泉城洒下一片皎洁,高顿站在桥头上……
“高顿……”
界平的手微微抬向张连长,张连长迟疑地接过她苍白的手指。错乱的界平感觉那已不是自己的手了,两颗泪珠滚下眼角。她像看到一线希望,在未来摇摇晃晃,又像发现了一枚火红的柿子,孤独地挂在枝头。
“高顿……马上就到!”张连长安慰着陌生女子。
监护仪突然报警,心脏骤停,病人再次昏迷。护士按了急救铃,医生们推着仪器拥进来,立即进行电除颤,心脏注射三连针。被安排陪护的崔加吓得面色苍白,仿佛该急救的不是那女子,而是心律狂乱的崔加。他见过人的死亡,初中时,老师要崔加站起来背诵课文,他刚刚站起来,老师就心脏病发作倒下了。他被死亡的迷雾弄得晕头转向,储存在膀胱里的废水不受控制地顺着腿温暖地流了下去。
看到医护人员在急救,崔加第一个反应就是憋住水管,以免再尿湿裤子。对他来说,忍受别人的病痛比忍受自己的小便容易得多。
女性的病态有不可言传的美妙,崔加有生以来,还是头一回玩味,他从来没领略过这种雅致的昏迷、美丽的五官、睡鸽似的姿态。他哪里知道,他尿急的反应正是因为床上这位如诗般的女人。一想到如此美丽的女孩,却差点以惨剧收场,而军营里那些粗糙的战友,却嘲笑他的看护任务,就愈发感慨造物者的残酷。他日夜陪伴着她,想象着牛郎陪着织女、宝玉陪着黛玉……无际的幻想让崔加走火入魔。
马主任接到界平自杀的电话着实吓了一跳。界平差点被洪水冲走。如果“威胁”这个词不露出伤人的射线,马柱也不会那么自责和恐惧。那小小的阴影像快速挖开的坟墓,散发着令人惊慌的恶臭。
被人误解为自杀,界平不知道自己是该哈哈大笑还是痛哭流涕,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该认倒霉。她一心一意活在幻想的世界里,仿佛一位即刻行刑的死囚,不拿未来搁在心上。
她终于明白一个人只能走在上天设定的宿命之路上。
她以一种无所畏惧的从容,开启了另一种生存状态。
界平像一座高压变电站,马柱再也不敢靠近,再也不敢伸出多情的手了。国王也有禁忌,何况一个车间主任。
月亮羞羞答答地升起,又圆又白,缓缓移动着步子,向泉城洒下片片月华,大大小小的泉眼喷勃着晶亮的快乐,穿城而过的河流承载着道道银光,这些白光好像一条条无头蛇,遍体明鳞,盘来盘去,一直盘到河底。
明晃晃的河道里银波流窜。
河水很健忘。
她还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站在一大群人当中,又是音乐,又是舞蹈。她的痛苦化作一股对世界、甚至对自己盲目的怒火,这反而增强了独自面对孤独的勇气。暴雨之夜似乎已经离她很远,仿佛相隔了半个世纪,中间到底出了什么事,使前后的自己如此陌生。界平小心翼翼地不让任何表情泄露内心的痛苦。这些人挥霍如王侯,一腔没有着落的野心和荒唐无稽的狂热,旋转在舞池中间,骄傲得不可一世。界平想离开,希望自己和牲畜待在一起,也像牲畜一样喑哑、安详。
张连长拦到她面前,邀请她跳舞。这个人救过自己,无论如何她都不好拒绝。张连长被评为“抗洪抢险英雄”,事迹在各大报纸上连载。他们随音乐进入了舞池,她僵硬地挪动着身体,像被绑架了似的,努力调整着情绪,尽可能露出温和的笑容,可连自己都感觉虚假。她的手被握在张连长手里,觉得又生硬、又颤抖,如同一只鹦鹉,虽然被捉住了,还试图飞走。
窗子打开,微风灌了进来。一股独特的气息向她飘来,高顿身上特有的气息,瞬间唤醒了冬眠的欲望,混淆了长梦与记忆的细微区别,好像记忆还有一种深沉、持久的呢喃,驾驭声音的呢喃之上。
看向张连长的目光软化了,他英武的侧影,和善的表情、放在她后背有力的手掌,悄悄地感染着界平。玫瑰红的色彩伴随着浪漫的音乐,和着习习香风,好像一阵狂飙,吹遍了她的灵魂,氤氲了她深藏的欲望。她有些微醉,有些眩晕,像喝了酒。
“你冒充了小强的表哥,替他付了书费吧?”
“那你也是小强的表姐,你也做过小强的算数题!”
“也许你怂恿了一个小偷。”
“孔乙己怎么说的来,窃书不能算偷也。”
有了这段序曲,两人似乎跳得更和谐了,像老朋友似的。她的手是温暖的,这温暖让他回忆起别的场景,虽然有些感觉永远埋藏在心里。二人笑容拘谨,仿佛在睡眠里,梦境汇合在同一领地,与外部声响隔绝。
“谢谢你!”
“谢什么,我连猪都救了……”张连长感觉比喻得不恰当,不好意思地笑了。
两个一百八十度旋转,张连长把界平带出了舞池中心,慢慢晃到角落里。他不想让人注意他们的谈话。
“你曾把我当高顿!”
“我也曾把你当雷锋!”
一层乌云飞过界平的脸颊。他哪里知道,“高顿”这个名字不但是界平的毒药,也将是让他足以发疯的毒药。
很多人不敢爱,是因为太多的事情,太多的过去与未来纠缠不清,而她不同,她只有现在。他们聊起了中越即将开始的战争,聊起了风吹落叶似的命运。
“没有人能毫发无损地走过战争,这必然是一场恶仗。你赌高顿,我赌战争!说句掏心窝的话:我没打算活着回来,因为老天不会给我这种奖赏!”
“我在和将死的人跳舞吗?”
“别忘记了,是我救了你。”
“我正努力记着,我在想该怎么救你一次。”
“你上演了一出可怕的悲剧。”
“你刚说什么来着……没有人能毫发无损地走过战争……”
空气里有一种怪味,好像米饭变质,变酸了一样。界平不敢看他的脸,伏在他的肩头默默望着人影晃动的舞厅。两人都没发现,他们彼此靠近了,几乎是衣服贴着衣服。
张连长的灵魂将置于炮火之上,战争将他推到另一条路——血流成河的艰难之路。说到底,战争就是肉体扼杀肉体的艺术。在这条血腥之路上,无论是不是英雄,每位提着生命冲锋的战士,都已超过了人与梦想之间的深壑。界平望着这张男子汉十足的脸,她想记住他,甚至用这张脸覆盖另一张让她痛苦的脸。她知道,她稍表现温情一点,就会把自己毁掉,也就是说,就会把自己跟他联系在一起,拆不开了。
他们谈话时所体验的沉重心情至今没有离开她。经过很长时间的间隔,她忽然感觉到悲伤的并不单是她自己,还有那些即将上战场的战士们。内心的感觉疲沓了,甚至停顿了,心里仿佛堆满了垃圾,很难清扫出去。
他们慢慢舞着,任何语言,此时,都是第三者。
从界平进来的第一秒钟,崔加就成了俘虏,目光被她牵着,心思被她带着。这位让自己差点尿失禁的病人,成为整个青春期、乃至在整个战争时期滋润着他的柏拉图式的爱情源头。真理让猪吃掉了。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精力旺盛地迎接一天了。天真而多情的他开始了孤独的狩猎生涯,慢慢地将她理想化了,为她写诗。把一切不可能的美德和想象中的情感全部归附于她,称她仙女、天使……可除了远远地看她,他什么都不敢做,不是怕尿失禁,而是怕心失禁了。
崔加像地下党似的一首一首地写情诗,可没有一首敢送到界平的手里。有一次,他将美女比喻为月亮的诗誊写得干干净净,郑重地装进信封里,虔诚地守在纺织厂的门口。可当远远地看到界平走来时,他竟然双膝发软,差点摔倒,不得不扶住老槐树。当界平高傲的身影消失在人群里,他的膝盖才像大脑似的灵活起来。被爱情俘虏的他像被捉住的小野兽,茫然失措地往四下里张望。
多年以后,当他试图回忆界平的模样时,却发现无法将她从那些诗化了的意念中分离出来。
人们都说张连长从河里捞了个漂亮媳妇。
界平曾经历过骤然来临的爱情,仿佛九霄云外的雷霆,电光闪闪,颠覆生命,狂飙吹过心灵,席卷意志。然而那璀璨的爱情像流星,光芒四射地划过天际,短暂而美丽,从此却坠入永夜的黑暗、无尽的痛苦深渊。而张连长的温暖却像冬日的阳光,虽不热烈,却能驱除冰寒,虽不耀眼,却能照亮长夜。发自灵魂的热乎乎的温暖,踏实而厚重的感觉,让界平答应嫁给这个军人!
意有所舍,心犹未甘,她只好把高顿放在超凡的境界。她已经不思念他了,他安放在她心灵深处,比埃及国王的木乃伊在陵墓里还有尊严,还要安静。这伟大的爱情如同加了防腐香料,只能在沉重的金字塔下散发出迷人的柔情蜜意。
听见张连长的脚步,她就心跳加速,但两人久坐在一起,心就沉了下去,像多年的老夫妻,少言且默契。自从决定嫁给张连长的瞬间,界平感觉心头卸下了全世界的重量。有了这张油亮的烫金红纸,她成了有家的人,成了有人关心、有人在乎的人,也因为有了这场婚姻,那些贪婪的、流氓的目光或酒后试图乱伸的手,就会自动离她而去。
当崔加得知张连长要和界平结婚时,他突然感觉自己全身的骨头都碎了。仿佛张连长是魔鬼,抢了本属于他的新娘子。崔加被幻想的痛苦压得喘不上气来,和吃了不洁食物的战友们一起病倒了。战友们吐空了肚子后便恢复了健康,他却搭乘着食物中毒的幸运之车,痛痛快快为爱情死去活来了一回。在病床上,他每时每刻都想念着她,为她而痛、为她而吐、为她而失眠。眼泪是必不可少的润滑剂,有了它,他一厢情愿的爱情就有了足够的戏剧效果。他试图为爱情牺牲生命,感动于自己伟大的真情。自此,他诗歌的主题由对爱情、生活的歌颂,变成了对恶势力的诅咒、青春的伤感和未来的幻想。
因为是战前,又是英雄的军婚,总是低调行事的界平无意中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作为英雄故事的女主角,身体已风化成形象,灵魂变得透明。婚姻只是途径不是结局,媒体相信这喜庆的照片,相信神奇的力量会在亿万民众的心里发酵。界平感觉自己的鞋子还沾着过往的泥浆,就被推到了明星婚礼的红毯上。当读到报纸上战前军婚的报导,界平感觉自己像偷了东西被当场揭发了一般,说不出多狼狈。
爱情是比欲望更强烈的东西,也是抵制诱惑的唯一理由,而婚姻不过是用来抵制欲望最脆弱的武器,就如同拿着玩具枪对付老虎。明白这一点,需要付出很多眼泪或心血。
在商店试新娘装时,界平从镜子里看到了面色苍白、神情忧郁的自己,一个并不开心的出嫁姑娘。
镜子里突然出现了高顿的形象,界平无声地笑了,这笑容背后的苦涩,只有自己知道。界平不在意时间,不在意闹钟的嘀嗒,感觉那些逝去的时间沉淀出冰冷的分量,而未来依然终结在冰柱上。时间停留在那特定的一天,那天战友们和工友们有酒喝,有糖吃,可以放肆地跳舞。在时间的边缘游走,界平感觉被永久地困在这里,困在军营里,困在一种规则里。这是她选择的婚姻,她渴望喜庆的红光能渗透她,驱赶她灵魂的阴霾与寒冷。许久以来,从贝地城那个男人不辞而别开始,没有东西能温暖她的灵魂了。
在商店,界平被人撞了一下,撞她的小青年泥鳅似的溜进了人群里。回到宿舍界平突然发现包里有个信封,抽出折叠的信纸,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我的女神!你不能嫁给张连长!!!
界平以为是某个战士在和连长开玩笑。她哪里知道崔加为了这几个字一夜无眠,闻着被窝的臭气,借着手电筒的光亮,写了三十几页的情书,十多首情诗,可打包准备寄给界平时,又退缩了。他既怕被张连长发现,又怕被战友们嘲笑。天亮的时候,才在战友们的酣声中,用左手匆忙写了那句话。
崔加已跋涉过,在无爱的生活里游泳。如果没有爱,每一块石头都会失去自己的影子,每一棵白杨都会枯萎,每一眼井的水都会被人从源头下毒。他坐在美好生活的废墟上,几乎被痛苦击垮,因绝望而不知所措,因痛苦而茫然。“今天必须把爱留在心里,否则我怎么活过每一天。”
界平往玻璃窗上张贴红喜字,张连长从后面抱住了界平,轻轻地在耳边问道:“亲爱的,开心吗?”
难道他看出了界平的忧郁?或者感受到了界平的不安?
界平转过身来,捧着他的脸,像审视一块做衣服的面料,把头埋在准新郎的肩头。
不论什么时间问她在想什么,她总是说,在想事情。看到这情景,他总是不由自主地现出那种唯命是从的奴隶般的忠诚。
“我会让你幸福的!”
这话好耳熟,当年,高顿也说过。
界平用阅读的双手,已把高顿翻译成自己的书。
张连长闻着她身体散发的香味,喜形于色。她的整个体态、她的头、脖子和双手,他每次看到都为之倾倒。他觉得人生从没这样好过,他真希望生一群孩子,没有战争,洞天福地,有界平在的地方就是世外桃源。
崔加知道自己无法阻止那场军中的婚礼,溃败的感觉连呼吸都变得异常艰难。他感觉会死一百次,然后再一百零一次地爬起来爱那个女人。当全连都为连长的婚礼而喝彩时,他提请去站岗值班,远远地躲开那欢庆的音乐、喜庆的笑脸和飘香的美酒,更远远地躲开绝望的深渊。他甚至觉得为心爱姑娘的婚礼站岗放哨,既伟大又痴情,既无私又郑重。
多情的风把婚礼的喧闹残酷地送到崔加的耳朵里,他不得不咬住舌头,以免骂出臭气熏天的话来。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站岗时莫名其妙地哈哈大笑,笑声里包含了对整个世界的嘲弄。
军队领导主婚,纺织厂领导讲话,战士和纺织女工们为这革命意义的联姻,狂热地兴奋着,仿佛今晚他们也入洞房似的。记者们在讨得喜糖之后,抓紧赶写战前婚礼的报导,这具有特殊意义的婚礼,昭示着军队和整个社会对战争的信心和激情。
界平穿着火红的新娘衣裙,戴着红头花,像一朵精致的玫瑰。
大厅里推杯换盏、欢声笑语,祝福的话一箩筐。新郎被战友拉去喝酒,稍得喘息的新娘到院子里透透气。内心有一个冰点,似乎别人的欢笑与她无关。当事人总是明白得那么晚,缺乏必要的敏感,在理解珍贵的、优雅的和美丽的东西时,总是那么迟钝。虚妄的欢乐已封闭了心灵的窗户,生活中充满了令人窒息的静止。
她向灯光照不到的院子走去,突然收住了脚,惊得魂飞天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