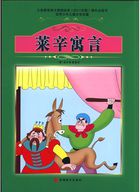是在二零零四年的十月份,建新又回到了我们中间。
他操着听上去十分古怪的普通话,对一切都充满好奇。不过就是几年没回来,张城已经变成这个样子啦!建新一边东瞅西看一边感叹道。他在这个城市唯一的大学附近租了一套房子,两室一厅。当我们在他的邀请下,过去登门拜访时,不由得感到惊讶。要知道我们那时候都还没过上好日子,租的房子一律都是城中村的简易房,我们其中许多甚至都还没坐过电梯,没有坐过出租车,连抽水马桶,都让我们感到手足无措。我们在建新的房子里,对自己的鞋子在木地板上踩出的鞋印感到万分不好意思,每个人的动作都显得十分生硬。
建新仿佛预料到我们会这样似的,他得意扬扬地看着我们。我们这些平时说话习惯了大嗓门的家伙,扭扭捏捏地试着让自己优雅起来,避免在这房子里显得过于突兀。有明亮的落地窗、巨大的软硬适中的沙发,还有抽油烟机,这一切都让我们感到十分陌生。
更让我们意外的是,在我们端坐在沙发上,试着像建新那样小口小口地喝了半天茶水后,突然,靠近走廊的一间卧室的房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睡眼惺忪,还穿着睡衣的女人。她高大的身材,旁若无人的神色,不由得就让我们感到十分压抑。建新站起来,拉住那个女人的手向我们介绍,这是他的女朋友。我们嫉妒得都快发疯了,怎么也平静不下来自己的心情。每个人都往后缩,以免露出自己裂开缝了的皮鞋、皱巴巴的劣质西装,还有满嘴的大白菜气味。就这样,沮丧笼罩在了每个人头上。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女人是旁边那个大学的代课老师。当我们终于让自己放松了下来之后,大家急切地向建新打听,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建新笑眯眯地坐在我们中间,一丁点消息都不给透露。在那个时候,我们中间有好几个,都有自己的女朋友。但是和我们接触的女人,一律和我们一样,眼神里闪烁着畏缩的目光,经过装修豪华的大商场时,连双腿都感到发软。当然,也有些例外的,比如麻子的女朋友,她穿着总是可以露出肚脐的紧身衣,头发黄得像乱麻一样,大冬天,她还穿着丝袜,抹着浓烈的口红,在大街上自以为是地走过。多么不一样,我是说建新的女朋友,没有人反对我的意见。
建新带我们去吃自助火锅,可以肯定的是,建新是第一个给我们展示真正的城市生活的人。虽然之前我们大部分已经在这个城市待了不下四年,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地消费过,下的馆子一律是拥挤狭小的城中村街道边的大排档,一顿饭一碗面就可以把我们交代掉,偶尔控制不住也顶多搞盘凉菜,炒个过油肉而已。一个人三十八块,建新毫不在意地从口袋里掏出钞票付了账,我们连小声交谈都觉得心虚,安安静静地坐着,尽量不发出嘴巴狼吞虎咽的声音。
相信别人跟我一样,接下来好多天,连做的梦都比以前多了许多内容。我女朋友李玲比我受到的刺激还要大,在冬天刚刚到来的时候,她死活要去买一件价值三百多块的羽绒服。你不想让我看上去更像样一点么?她这么问我。我当然想,有好多次,当建新的女朋友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总是控制不住地对李玲感到厌烦和自卑。那件羽绒服李玲穿起来后,就再也没有脱下来过,如果条件允许,我想也许她会在睡觉时候都穿着它。我从来没见她对什么东西那么认真细心过,甚至可以因为我不小心坐在她的羽绒服上,她就跟我大吵大闹。
毫无疑问,建新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他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不确定起来,当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人像以前那样投入地胡撇海侃,每个人脸上都出现了焦虑不安、随时都想站起来干点什么的表情。我们觉得,就在这一会儿,我们显得多么游手好闲,一定有什么东西,一定有敞开的机会大门,正在迅速地消失,我们得抓住它。
在这里,我也许得给你介绍一下我们都是些谁,我们都是些什么玩意儿了。当然,最先得从建新开始,建新只比我们大一岁,他是我们的初中老师,教英语。我们每个人都得感谢这个家伙,尽管他学历仅仅是初中,但这并不妨碍他当一个恰当完美的老师。也许他朝我们每个人的脑袋上都扇过巴掌,有时候暴跳如雷时,他也许还拿脚踹过我们的后背。但是,不得不承认,建新对付我们的方法是对的,在他的课上,我们全都集中精力,以免一不注意,黑板擦啊什么的就会砸向你的脑袋。尽管我们私底下讨论建新时,都是一副咬牙切齿的模样,但当我们跟别人谈论起学校生活时,只会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建新。你能想到么?一个初中毕业生,刚毕业一年就回来教初中,还是英语,并且比所有其他老师都教得好。
你能想到么?当你老师听说了那些被开除了的家伙把你逼在墙角落里,让你交出了零花钱时,他在讲台上暴跳如雷,居然鼓动你们说,下次不论什么人敢这么做,就拿起砖头砸上去吧!教室里到处都是砖头,用来垫桌子的,用来暖手的。如果你做不到这点,尽管砖头就在手边,你还是不敢,低头流下眼泪,建新就会出现,尽管他身材和我们差不多,尽管他瘦得跟玉米棒子似的,但是他没有丝毫犹豫,就冲上去了,当然,手里真的拿着砖头。
你能想象到,一个你的老师,和你们躲在宿舍里赌博么?当望风的人打起事先约好的暗号,告诉你有别的老师来查房了的时候,建新就会走出去,装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跟那个人聊上半天。当然,不得不承认,建新打扑克实在是太烂了,我们从来不记得他有赢过。输到后来,他的脸色就会变得很难看,愤怒地把扑克扔在地上,发誓再也不会赌钱了。可惜的是,这样的誓言从来一点作用也没有。没几天他就痒痒起来,在宿舍里围观了半天后,还是坐到了牌局中间。
你绝对想不到,建新在我们初二时做的那件事,他在我们那里见到了一个美国人,这个美国人刚下车,建新就扑了上去,不一会儿,他又返了回来,跟我们要了纸和笔,然后我们就看见他跟美国人钻进了轿车,然后就失踪了。过了一个星期建新才回来,他告诉我们,美国人是去旅游的,建新自作主张给他做了导游,并且不收钱。建新拿出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布满英文字母。他对我们说,跟美国人聊了一番,他才知道自己的英语多么可笑。
那是在九七年,我们还从来没见过外国人。建新走上前去,比那个美国人低了整整两头,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跟对方交谈了起来。我们那么多人站在操场上,感到这一切多么不可思议,又为建新感到不好意思,和美国人相比,他显得多么的简陋。真的,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样。
当建新被学校开除的那天,我见到不下十个人流下了眼泪。当天晚上,我们在宿舍里根本没有睡觉,那是我们第一次体会到一种叫做友谊的东西,这么概括也许太过简单,但是,你还能怎么说呢?我们第一次货真价实地谈论建新,谈论建新的未来,我们为建新感到担心,他能干点什么呢?难道跟别人一样,去下煤窑么?难道跟别人一样,去砖厂背砖么?这些不适合建新,我们当时觉得,建新和我们认识的所有人都不一样,所以,他不应该干和其他人一样的事情。
最起码有半年的时间,我们一直期望着建新回来,哪怕是露上那么一小面,我们都觉得,即使建新不回来看看我们,他也应该回来看看李露。李露就是建新被开除的原因,她是我们的同学,看上去极为普通,我们宁愿和建新一起躺在他办公室的人是另外一个女的,比如长相漂亮、身材丰满的西亚,哪怕是比我们都高过一头,让我们觉得自己是小鸡的程菲也行。但是,建新的口味太独特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要知道当他和我们在宿舍里聊起来时,从来没显得不同过,他对大乳房大屁股的兴趣,比我们每个人都要激烈。当李露的父母带着校长,撞开建新的办公室门时,听说李露吓得大哭起来。她马上就把责任全推给了建新。还好的是,通过大家的说情,这件事情最后私了了。建新没有跟我们任何人打招呼,就离开了我们。
二零零四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建新把我们一个一个从被窝里拉了起来,要我们穿戴整齐,对我们说,今天,我带大家去开开眼。建新满嘴的酒味,之前我们大部分人都还没喝过酒。建新醉态的吆喝让我们感到十分不安,就跟一群小鸡跟着母鸡似的,我们跟在建新身后上了街。这确实是个值得出来遛一遛的日子,大街上到处喧闹非常,尽管寒风挤着我们的身体,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我们逐渐兴奋起来。看看吧,建新对我们说,圣诞节。这个节日我们听说好多遍了,但是从来没觉得它跟自己有什么关系。现在,建新要我们好好地打量商场门口的圣诞树,要我们仔细端详圣诞老人的模样,这个遥远的、来自西方的、打扮古怪的、莫名其妙的家伙,尽管毫无心跳的迹象,还是把我们盯得坐立不安起来。
有很长一段时间,建新是我们的主心骨。是的,我们需要一个为我们做主的人,带领我们的人,他有勇往直前的勇气,他敢于打开麦当劳、夜总会的玻璃门,他敢于和每个擦肩而过穿着光鲜的人们对视,就好像眼睛里有一双坚挺的拳头,他还敢于在名牌专卖店里一件接一件地试衣服。当然,还有一点,当他抬起胳膊拦出租车的时候,动作是那么的自然,他能让我们安下心来。
那天,建新跟我们说了许多话。我们在歌厅的大包间里,南腔北调地唱遍了所有会唱的歌,建新不停地叫服务员给我们端上啤酒来,然后和我们一起举着瓶子,撞得咣当乱响。当喝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建新突然做出了我们谁都没有想到的举动,他把服务员叫进来,大声吆喝,来,给我这些哥们儿一个人来一个小姐。我们马上变得鸦雀无声起来,扭捏的神态再次回到我们的骨头里,不对,它就没有离开过。建新一点都不在乎我们假惺惺的反对,固执地领着一排高低不一的女的站在了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