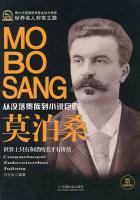就在江隆基到任的当月,北大迎来了第一位苏联专家古马青珂——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授。那天他去教育部开会,副教务长侯仁之、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张友仁和总务长蒋荫恩也坐他的车去教育部,他们三人的任务是去接古马青珂。第二天江就将侯、张、蒋等有关同志召集到校长办公室,详细询问对古马青珂的安排,研究如何正确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问题,并嘱咐张友仁一定要主动地汇报教研室的情况,主动听取专家的意见,主动处好关系。不久,又将古马青珂聘请为北京大学的顾问,搬到校长办公楼,专门指导帮助三个教务长制订各类教学文件。古马青珂是个典型的俄罗斯人,个头不高,戴深度近视镜,一派学者风度,人也谦和,工作中善于听取周培源、侯仁之、严仁赓三位教务长的意见,不以专家身份指手画脚。江隆基对他十分尊重,不卑不亢,相处十分得体。他一再教育下属,学习苏联,不要忘记总结中国历史上好的经验,也不要排斥别的国家有益的做法。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正确运用苏联经验,目的是办好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学。
但最初两年,高等学校在学习苏联经验中普遍出现了要求过高、改革过急、任务过重、工作过于忙乱的状况,北大也不例外。教育部曾推荐过东北某大学的经验,该校提出“苏联专家的每一句话都要贯彻落实”,教学中实行“六小时一贯制”(即一堂课讲六小时)。江隆基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是形而上学,绝对化。在校务会议上坦率地说:“依靠苏联专家,并不是每一句话都要贯彻落实,事实上也不可能贯彻落实。北大老教师多,谁能一口气讲六节课?”他提出“教学改革要稳步前进”的精神,引导大家通过修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减少或缓教一部分课程,根据学生程度调整班次,减少学生社会活动等措施,缓解了因压力过大而影响教学效果和师生健康的问题。
1953年10月22日,江隆基在一次正式报告中,再次强调“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要照顾到我国过渡时期的特点,不能要求一切都很完善,都很正规,都整齐划一和标准化”的问题,刊登在校刊上的讲话提要如下:
为了贯彻学习苏联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精神,需要注意两点。(一)学习苏联必须照顾到过渡时期的特点;(二)学习苏联必须照顾到各专业的不同情况。
当前学习苏联的一个主要环节在于认真钻研苏联的教学大纲、教材,并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不断地去修订教学大纲,不断地搜集中国的材料去补充苏联的教材。在钻研苏联教材中,必须注意它的思想性和科学性,注意它的组织结构、材料的提炼以及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等方面。这样反复地修订补充,过几年以后,就可以把苏联的大纲、教材变成我们自己的,逐步形成我们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体系。
这些讲话精神,古马青珂是赞同的,并未以专家的身份居高临下,颐指气使。两年之后的1954年夏天,古马青珂任期已满要回国,江隆基在颐和园设宴欢送,合影留念。古马青珂对北大,对江隆基、周培源等领导赞许有加,依依不舍。
古马青珂高高兴兴地走了,另一位专家诺沃德拉诺夫来了。
这位苏联专家与一位中国专家之间的关系,却让江隆基费尽了周折。
这名中国专家就是两度赴美两度回国的傅鹰教授。
傅鹰是1954年从石油学院调来的。一家愿放,一家愿要,两厢情愿,调动很顺利。调北大后任化学系胶体化学教研室主任。然而这位傅先生换了环境却改不了秉性。他学术造诣很深,事业心很强,就是不善处人。说话很尖刻,张嘴便是讽刺挖苦,常常弄得别人下不了台。化学系的教师提起他就皱眉头,老教师惹不起躲得起,年轻人则亲也不对疏也不对。诺沃德拉诺夫也是胶体化学专家,也是教授,工作只能在胶体化学教研室。傅鹰先生就很瞧不起这位苏联专家,认为没学问,有意在公开场合散布说:“他只配做我的讲师!”由于他的人缘太差,诺沃德拉诺夫很快知道了,两人反目,关系十分紧张。诺氏还兼任北大专家组组长,便以专家组长的身份上访校方,上纲上线,要求以“抵制和破坏苏联专家的工作”论处。放言如不处理,将上告中国教育部直至中共中央。
傅鹰和诺沃德拉诺夫闹到这程度,就超出了孰高孰低和个人恩怨的范围,成了政治问题,江隆基很懂得这种由个人关系而带来的后果,不能不认真对待。他不厌其烦地找二人谈话,苦口婆心地做和解工作。
经周培源介绍,江隆基已经知道了傅鹰的学术水平和人生经历。他被同行称为“美国留不住的化学家”,第一次回国时年仅二十九岁,抱一腔“科学救国”的宏愿;第二次回国时年近半百,动因竟是解放军炮轰英国“紫石英号”战舰事件。江隆基是从解放区来的高级干部,自然知道这一事件的始末,感觉找到了与这位脾气古怪的自然科学家沟通的共同语言,也似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路径。首次约谈,江隆基不说其他,只介绍了“紫石英号”事件。他说事件发生在1949年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前夕。4月20日,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的“紫石英号”战舰不知什么原因突然闯入镇江渡口,遭到正在准备渡江的解放军的猛烈炮击,“紫石英号”遭重创而搁浅。当晚,英国海军调遣“伴侣号”“伦敦号”“黑天鹅号”紧急支援,双方激烈交战,三天后被击退。随后双方就此事件开始谈判。4月30日深夜,修复后的“紫石英号”摸黑出逃,谈判也随之终止。此次交战双方都有很大损伤,解放军阵亡二百五十二人,英军死四十五伤九十三人,当时解放军的装备不足以对付战舰,又是出于预料的恶战,所以损失惨重。他介绍说,谈判中双方都采取了克制的态度,英方强调是误入,不是针对解放军的;中方强调不管什么原因只要进入内陆,就是侵犯主权。江隆基说:“‘紫石英号’事件所产生的意义是重大的,宣布了自1840年以来炮舰政策的终结,结束了西方国家随意进入中国内河的历史。”
傅鹰饶有兴致地听了江的介绍,如实坦言,当时美国报纸把这件事渲染得很厉害,他从报道的字里行间感受到的是解放军的强大,能用土枪土炮击垮现代化的战舰,断定解放军一定能解放全中国。周恩来就此事发表的严正声明让他深受鼓舞。更没想到的是,1950年1月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可见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所以当即决定回国,连乘坐的轮船“威尔逊号”也是有意选择的。江隆基热忱地肯定他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正义感,又补充了一个傅鹰肯定不知道但很有趣的事实,说这次事件后,没有当过海军没有接触过战舰的二十三军军长陶勇当上了东海舰队司令,是毛主席亲自点的将。毛主席风趣地说,你会用土炮打人家的战舰,你去当海军司令吧。江隆基接着谈到正题,说中国人民是站起来了,但现在还没有现代化的军舰,也没有当海军司令的人才,造军舰的技术和当司令的前提是要有人才;人才靠培养。“科学救国”不是喊口号,是要付出艰苦努力的。傅鹰当然明白江说此话的良苦用心,便坦诚说,回来后让他大失所望,石油学院条件简陋,连最基本的实验条件都不具备,还叫什么大学?又要教授参加什么思想改造,他实在想不通,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他也承认自己生性急躁,石油学院那种环境更使他无法控制自己。江解释说,石油学院刚刚成立,条件是差一些,但好的条件要靠创造,再过若干年,说不定会成为一流的专业学院。北大这边化学系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但也排不到世界前几名,能不能达到世界一流,就要依靠你们这些专家来提升,你和夫人张锦都是有名的化学教授,就看你们怎样工作了。傅鹰当即提出,他需要一个密歇根大学那样的胶体化学实验室。江的回答也很痛快,具体找周培源教务长谈,正在筹建风洞实验室,如有可能,一起打报告申请资金,一起建。
再次约谈,开题就谈诺沃德拉诺夫。傅鹰坚持自己的看法:学问不大,不够专家资格。江隆基则说,学问有大有小,即使同一档次的学者,也还有高低之分。他强调学习苏联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尤其留学英美的人更应向苏联学习,取长补短,为我所用。他几乎是警告式地告诉他:“工作中有意见分歧是允许的,但决不许讽刺挖苦,不许闹纠纷,如果产生不良后果,你要负全部责任。”
向来桀骛不驯,在国内化学界除侯德榜之外再难瞧得起几个人的傅鹰,倒出奇地对江隆基十分尊重。严格要求,晓之以理,几经和风细雨的谈心,他也承认对苏联专家态度冷淡,表示愿在北大、在胶体化学上“滚一辈子”,江充分肯定他这种态度,在各种会议上公开讲出去,借以消除紧张的人际关系。傅鹰调北大一年后的1955年,北大建成全国第一个胶体化学实验室,又推荐他当选科学院学部委员。
对诺沃德拉诺夫,江隆基几乎是代傅鹰受过,检讨其自高自大,对专家不恭,校领导照顾专家不周等等。同时也指出,傅确是有真才实学的化学家。访谈中,他看到诺氏的办公桌太小,为其换了一张大写字台,这件小事也深深地感动了诺氏。后来诺沃德拉诺夫也承认:“傅鹰教授确实是一位权威学者,我很钦佩他。”
1956年7月,诺沃德拉诺夫任职期满,准备回国,同期回苏的还有五位。北大为他们举行了欢送会。江隆基注意到,两位昔日的冤家对头同坐一桌,握手言好,谈笑风生,相互赠送礼品。在诺氏代表专家组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之后,傅鹰即兴赋诗一首,赠别诺氏。他站起来高声朗诵那首七言律诗,最后两句是:
二年绛帐春风暖,
桃李盈庭一手栽。
1956年2月,江隆基率中国高校代表团访问苏联,先后考察了列宁格勒大学、基辅大学、萨拉托夫大学,最后一站参观访问莫斯科大学。访问考察期间,江隆基全面了解了苏联的教育制度、课程设置、教学工作、科学研究,以及学校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等各方面的情况,做了厚厚一本笔记,回国后撰写出《关于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几个问题》一文,将他1953年提出的两个原则问题做了详尽的阐述。文中提出的一些基本观点,不仅在当时克服了“一边倒”的倾向,而且放在几十年后改革开放时期,也不无可取之处,不妨摘录一段:
我们学习苏联,一是必须要照顾到过渡时期的特点。过渡时期的特点,就是旧的还未完全改掉,新的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新旧斗争和新旧交替是贯穿在整个过渡时期的。如在专业设置上,我们就不能看苏联大学有个什么专业,我们也设置个什么专业,而要在国家建设事业需要和当前可能的条件相结合的原则下去考虑问题;在教学计划的修订上,不能照抄苏联的教学计划,而应根据我们的师资条件作必要的伸缩;在教材内容上,凡苏联教材可用的,我们就要尽量采用,没有可采用、可参考的,只有自己努力另行编写,某些有益的旧教材也可以斟酌采用;在教学方法、教学制度上,也必须根据我们目前的状况灵活地采用,不能生搬硬套。总之,学习苏联应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就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方针。二是必须照顾各专业的实际情况。如自然学科各专业,一般都可以采用苏联的教学大纲、教材及参考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专业,除去某些基本课程可以采用苏联的教学大纲、教材外,其他专业的课程主要可以学习苏联的观点、方法,采用一部分教材;至于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等专业,只能学习苏联有关专业的观点、方法。
1956年为筹备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周总理约江隆基谈话,了解情况。
总理问:“北大有多少教授?”这个数字他知道,一口说出来了。又问:“有多少副教授?”江一时语塞,半天想不出来,如实地答:“这个数字我没记住。总理,我工作没做好。”周总理发觉了他的窘态,笑着说:“你这个大学校长和我这个总理―样,我也只知道国务院的正部长,副部长就记不全了。”
回来后他将副教授的数字立即作了补报,之后大会小会讲这件事,检讨自己:“我工作没做好,受到周总理的批评,真应该引为教训。”此事他不讲,也没人知道,更不会引起议论。他这么一讲,引起的议论是他襟怀坦白、严以律己的精神。
是年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会议是全国科学教育文化界的盛事,在新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后,毛主席在中南海连续两次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征求意见。
这些会议,江隆基大都亲自参加了。这种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局面,正是他从出任西安二中校长起从事教育二十年来热切期盼的。
这一年,北大召开第二届党代会,江隆基当选为党委第一书记兼副校长。
又经周总理亲自提议,周培源出任北大副校长,与他成了左右手。
全国解放后,北大党组织由地下转为公开,1951年2月召开第一届党代会成立党委,在江之前有两位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