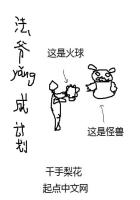在这条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马路上,刘志章的自行车开始加速,他必须在那声粗暴的汽笛声响起之前闯进前面的那扇大门。昨晚他睡得太晚,都零点了,金丽的脑袋还在他的胸脯上蹭。金丽说,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一般的人,一般的人怎么能把那种异常的声音从乱成一锅粥的噪声中提取出来呢?金丽曾是一家制药厂的化验员,提取、分离这样的词汇用起来十分顺手。她接着说,我去过你们厂,我听过那些机器的声音,正常的声音和异常的声音就像针扎了手疼得喊一声和做爱来了高潮兴奋地喊一声一样,是很难分辨的。但你分辨出来了,我知道,也只有你才能分辨出来。金丽的这种比喻令刘志章本巳高涨起来的困倦又一次退潮了,他对着金丽的耳朵说,你说得没错,因疼痛喊出来的声音和因快感喊出来的声音真的很难分辨,和你做的时候你一叫我就懵,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你的声音太像疼得受不了才叫出来的。金丽说你真笨。刘志章说我不笨,不信咱们再来一次。于是就真的再来了一次,时间就这样不可救药地滑到了下半夜。等早晨一睁眼,已经是七点钟了,刘志章顾不得洗脸吃饭,他胡乱穿了衣服就走。
自行车冲进大门的一刹那汽笛就响了,它冗长的尾音和身后自动铁栅栏延伸的声音联合起来,组成了一种新的声音,有些像昨夜他家那张不堪重负的双人床发出的声音似的,既杂乱无章又一丝不苟。这家工厂给刘志章印象最深的就是这种声音,按分贝来比较,尽管这种声音远不及厂房里众多的机器发出的声音洪亮,但这种声音以它独有的威慑力轻而易举地突破了其他声音的包围,以锐利无比的形式深人了他的骨髓。无论什么时候或什么地点,只要听到这种声音,甚至只要想到这种声音,刘志章都会感到脊背一阵阵发麻,一颗本来平静的心即刻会像遭遇了石击的水,激起一柱冲天浪花来。
此时厂院里的行人已经寥寥无几,没有特殊情况,谁也不愿把自己搞得如丧家犬一样仓皇。刘志章把自行车存进车棚后,没有像往常一样去班组,而是径直朝分厂的办公室去了。今天对刘志章来说的确与往常不一样,尽管阳光还是那样的阳光,厂房还是那样的厂房,但今天的阳光和今天的厂房一样对刘志章将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刘志章走进分厂厂长办公室之前还特意仰头看了一眼无处不在的阳光和高大灰暗的厂房,他知道,这个日子无论如何都是值得纪念的。
然后,刘志章推门进屋,迎着分厂厂长老孙惊愕的眼睛走过去。老孙和刘志章一样都是四十出头的汉子,二十年前,他们在同一天肩膀挨着肩膀迈进了这家发电厂的大门’这之后老孙一步一个脚印走进了这间办公室,刘志章则原地踏步了二十年,仍然是值班室里的一名普通工人。刘志章对此感慨颇多,而老孙却认为这十分正常,刘志章嘛,他永远都不适合做领导,尽管他的风头曾经比领导还大,但那所谓的风头正是升职的大忌,认识不到这一点,刘志章虚度二十载就是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你怎么不去接班呀?老孙用开玩笑的口气说,你不会是到这里来接我的班吧?刘志章苦笑了一下说,这种事情只会在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日子里发生,可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想出让地球反转的办法来。见老孙开心地咧着嘴笑起来,刘志章也嘿嘿地跟着笑了两声,他知道老孙不是一个随便施舍笑声的人,除了对他刘志章,老孙还没跟几个工人开过玩笑。从这一点上讲,老孙还是对刘志章高看一眼的。
过去的情形暂且不论,现在的刘志章有足够的理由对老孙的施舍受宠若惊。他知道这种玩笑不宜开得过长,就话锋一转切人正题,他说,我来找你是汇报一个重大情况的,昨天我在生产现场作交接班检查时发现了一种奇怪的声响。刘志章拉了一把椅子坐到了老孙的对面,他想说有一台运行的发电机组的轴瓦发出的声音本应该像女人叫床的声音,是充满愉悦的,可现在变成了女人被针扎了一下后发出的声音,是充满痛苦感的。他觉得金丽咋晚的比喻十分生动也十分贴切,这样讲应该很便于老孙理解。但话到嘴边了他还是一使劲咽了回去,他突然想起老孙是个很反感用男女关系开玩笑的人,自己这样讲会闹个事倍功半的效果,就不划算了。临时改词,嘴上就显得有些结结巴巴,刘志章的目光在这一瞬间绕过老孙有些迫不及待的眼神,落在了他身后的窗户上。刘志章看见窗外有一簇月季花正在盛开怒放,他知道办公室外面有一个小花园,他还知道小花园的院墙后面是厂里三产的养猪场,他甚至还知道养猪场的后面有一个个体养殖户的羊圈。刘志章突然就不结巴了,他说轴瓦发出的声音本应该像羊叫一样咩咩咩的,而不应该像猪哼一样吭嘛吭哧的,问题是现在轴瓦发出的声音就像猪哼一样是吭哧吭哧的。
老孙觉得刘志章啰啰唆唆的比喻十分滑稽,就又啁嘴笑了起来,但笑纹刚刚漫上五官他就意识到了什么,于是赶紧收敛笑容,努力使自己变得严肃一些。由于笑容与严肃交接得比较仓促,呈现在脸上的表情就十分生硬和怪异,他就腆着这副怪相大声问刘志章,你是说轴瓦运行的声音出现了异常?刘志章十分肯定地点了点头。
老孙是工程师出身的分厂厂长,对这些技术参数有着十分敏感的神经,轴瓦声音异常意味着什么他比谁都清楚,也就是说能发出异常声响一定是轴与轴瓦之间的接触出了问题,这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情。轴瓦磨坏了就得停机停产,这对于一个容量为三十万千瓦的大型发电机组来说损失是惨重的,值班人员下岗回家自不必说,就是他这个分厂厂长恐怕也当不成了。老孙觉得脖子后面凉跑遞的,就是脖子上压把刀,那感觉也不过如此。
老孙瞪大眼睛问刘志章,你敢肯定这种声音的确是异常的?刘志章也瞪大了眼睛说,我也没有喝酒,我不会拿这么大的事情来和你开玩笑。老孙说,好,你先去接班吧,我一会儿就去现场。老孙说罢就起身开始换工作服,刘志章转身离去的时候瞥了老孙一眼,他觉得刚才的老孙还是一棵被阳光晒蔫的无精打采的植物,经他这一刺激,这棵植物一下子就挺直了腰杆,变得生机勃勃了。说白了,老孙和他刘志章也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屁股下面的椅子都不是铁打的。这样想过之后,一种失而复得的信心就又回到了他的脸上。
刘志章重新走到厂院里的时候如释重负,一个蓄谋巳久的计划终于在这个看似平常的日子里开始实施。他知道这个“终于”得来不易,它浓缩了许多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现在,更确切地说是在不远的将来,他终于将缔造一段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了。在走进厂房的一刹那,他甚至得意地吹起了口哨。
厂房里的巨大噪声像一只巨鳄吞吃一只小虾一样吞噬了刘志章的口哨,这种噪音是一种合唱,是由众多的性能各异的机器设备一起歇斯底里喊出来的合唱。这些机器都不是合唱队员,它们一个个理应都是独唱高手,有的声音像飞机启动时螺旋桨发出的巨大声响一样轰鸣如雷,有的声音则是几百个钢球滚在一起相互碰撞发出的,足可以震裂你的耳膜,有的声音尖利,像一把锋利的刀尖划过一块巨大的玻璃。每一种声音单独响起来都是一首绝唱,而这些声音混合在一起会是什么效果呢?它足可以令一个没有玲听经验的人双手捂耳、抱头鼠窜的。
刘志章迅速从这种“歌声”中穿过,他来到值班室的时候交接班仪式已经结束了,值班长老郭气呼呼冲着他嚷道,都时候什么了你才来,是不想干了吧?老郭比刘志章小两岁,若干年前他是绝对不敢这样对刘志章讲话的,但现在情形不同了,他不但敢这样对刘志章说话,而且还敢对他手下的二十几个值班员中的任何一个这样说话。对于老郭和许多比老郭级别还髙的头儿们的这种骄横态度,刘志章经过了坚决抵制、不习惯、习惯的过程。要在其他的日子里,刘志章会低眉顺眼,编一些可以蒙混过关的理由来搪塞老郭的,但今天显然是个不同于往常的日子,刘志章觉得有必要用不同于往常的态度来回敬老郭一下。他笑了笑然后说,你说得不对,不是不想干了,正因为不是不想干了,所以我才这么晚来接班。老郭皱起眉头说,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刘志章说,你现在听不明白没关系,一会儿会有人叫你听明白的。老郭问谁。刘志章说,可能是分厂厂长老孙,也可能是老孙的上级苏总工程师,也可能是苏总工程师的上级高总。老郭用鼻子哼了一声,然后说,'我这一百多斤也不是吓出来的,你不用故弄玄虚。老郭嘴上虽依然强硬,但行为上已经露怯了,他说过这话之后,破天荒没有再追问刘志章的迟到问题,而是找了个借口干别的去了。
刘志章顺利地坐到了自己应该坐的位置上,因为免去了老郭的许多废话他感到十分开心。他的前面是操作盘,操作盘的上面是仪表盘,值班室的全称是机组控制室,发电生产的科技含量比较高,所以摆在眼前的尽是些仪表和电脑突屏。和刘志章并排坐着的有七八个人,他们各司其职,又相互协作。刘志章不时扭头瞧一瞧同伴们的脸,因为心里高兴,他很想和他们说一些什么,可说什么呢?这些人都是一些沉默寡言的人,或者用感觉迟钝来说他们更贴切一些。如果他说的话没有足够的吸引力,是很难将他们那一张张比仪表还呆板的脸改变的。刘志章曾不止一次跟不同的人讲过,他说人跟机器待久了,是很难不使自己变成机器的。
你们知道大朱那个人吧?刘志章歪着头冲着大家说,看他那双眼睛贼溜溜的好像蛮机灵,其实是个呆鸟。刘志章很喜欢用呆鸟这个词来形容他不喜欢的一些人,其实呆鸟这个词用在他的这些同伴身上才是最恰当的,但此时他只好把这个词送给大朱。他见大家都转过眼珠看他,兴致就陡然高涨起来,他提高声音说,大朱是个声盲,你们听过色盲、文盲没听过声盲吧,今天就让你们听一听好了,什么是声盲呢?就是对声音缺欠一种基本的分辨力,比如把钟声听成了锣声,把狼嗥听成了狗叫。最有意思的是大朱居然听不懂女人的叫声,你们都记得他曾处过一个对象是女护士吧?他们第一次上床,做到兴奋处女护士就嗷的一声叫了起来,大朱立即停止了动作,女护士说继续呀,大朱说看你疼得这个样子我怎么忍心继续呀?女护士说没事的,你只管继续吧,于是大朱就继续,片刻,女护士又一次嗷的一声叫了起来,大朱的动作就又停止了。这次女护士再让他继续他怎么也不继续了,他说我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听你的叫声都那么悲惨了,我还忍心继续我还是人吗?这一次之后,气得女护士就和他吹了。
刘志章说到这身边终于响起了稀稀拉拉的笑声。这个故事显然是刘志章临时杜撰的,也可以说是受了昨夜金丽的那个恰如其分的比喻的启发而编出来的。刘志章有这个本领,其实除了这个本领之外刘志章还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本领。只要刘志章高兴,这些本领就会像小鸟一样自由自在地飞起来,不受任何规则限制地给他带来快乐和好处。
笑声还没有完全落下去,值班室的门就被一伙人撞开了。率先进来的是老孙,他的身后跟着分厂的工程师、技术员等一班人马。老孙冲着每一个脸上漾出笑纹的人厉声喝道,笑什么,是不是都物色好新的单位了,不想在这干了?笑波立即消失,每个人都迅速地戴好了那张刻板的道具,一丝不苟地盯住前面的仪表盘。不想在这干了是老孙最具威慑力的一句话,老孙很满意这句话的使用效果,所以使用频率就相当高。要在以往他不会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就善罢甘休,但今天不同,今天他显然是冲着刘志章来的。他走到刘志章跟前,尽量把疑问在脸上无限扩大,他说我刚从那个轴套跟前过来,我怎么没听见那种猪哼一样的声音呀?
可我明明听到了。刘志章说,猪哼和羊叫绝对不会是一种声音,只要你用心听,应该能听得到的。老孙说,你是说我没用心听?刘志章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种声音真的存在。老孙摇摇头说,可我没听出来。他说罢指了指身后的那一串人,说,他们也没听出来呀,我看这毛病好像不是出在机器上,而是出在你的耳朵上,你的听力是不是出了问题?刘志章急得几乎跳了起来,他从椅子上挺起身体,一边比划一边大声地嚷,这怎么可能呢?我的耳朵怎么会出问题呢?我们可以一起再去听一次。老孙摆摆手说,不必了,如果真异常的话,我们这些人一个听不出来两个听不出来不能人人都听不出来,我劝你还是去医院检査一下自己的听力吧。老孙说罢带着一伙人就离开了值班室。
声盲。有一个同伴开口道,我看老刘你才是声盲!他的声音未落,值班室里即刻炸开一片笑声,那一张张刻板的道具在这一瞬间都被大家抛掉了。
没有谁否认过刘志章是个聪明绝顶的人,就连老孙那种自视很高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刘志章脑瓜冲,是个人物。若干年前,刘志章在厂里的知名度是老孙无法比拟的,提起刘志章,人们立即就会想起那个相貌堂堂、衣冠楚楚、走路永远高昂着头的小伙子。人们说,刘志章嘛,那小子的脑袋可没白长,稀奇古怪的念头能掏出一车皮来。人们说这话时都一脸的真诚,是真正的有感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