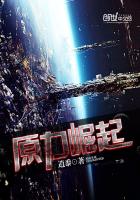更深露重。熏香似以往一般,缭绕迷离。
若宗轻轻从背后抱住她,下巴轻轻磕在她肩上。她越来越瘦了,令人心惊的消瘦。
他想起白日里显清哥对他说的,不仅起疑,“我不在家时,母亲对你可好。”
她稍稍瑟缩一下,几乎那话就要脱口而出,我不好,一点都不好。可是她又能怎么样呢,说出之后让他去跟他母亲争辩吗?拆散这个家庭,让林府上下鸡犬不宁吗?还是让他周旋于两个女人之间?
她不能这样。她早就知道她没了在教坊时那样的孤勇和果断决绝,现在的她,浑身都是软肋。
“好。”她妥协了。
林若宗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仿佛听到了期待的答案,脸上立刻变得欣喜起来。
“那乐谱练的可好,弹给我听听吧。”他温热的嘴唇轻轻在她脖颈出呵气。
她的身体一僵,垂下眼眸,“有些累了,就不练了罢。”
若宗停下动作,不解的看着她,他感觉有些看不懂她了。她得了乐谱后欣喜地样子还刻在他脑子里,怎的突然就变卦了。
他喉中像梗了一根鱼刺,说不出话,只觉得胸闷,猛地站起来去桌边灌了一口茶。那广陵止息曲谱确实难寻,他在宫中看到时也是惊喜万分,因不能整部拿走,每每间隙时,便一字一字的拓了去。想到这里不禁苦笑,如今看来,是没什么用了,就连琵琶也不见踪影。
她想要什么呢?他不懂。
他今早去向母亲请安时,母亲的话还停留心中。“你们的事我虽不干涉,但毕竟,你与她出身悬殊。她不像是肯安心待在家里的贤妻,也估计是受不惯拘束。你要上点心才是。”
他突然变得烦躁了。回头愤愤的扳住她的肩,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她咬着牙看着他,眼中含泪,“实在...抱歉。”
“算了,睡吧。”她的眼泪又一次很成功的刺痛了他,也让他的心烦恼怒。
背对背,一夜无话。
“好像要走到尽头了,但如果没有他的话,那该怎么样呢?”她想不出。
早晨起来时,若宗摸着她的棉枕,仿佛要湿透一般。心下一惊,她或是哭了一夜吗。他急忙出门去寻她。看到站立在雾中的瘦小的她,他急忙奔过去搂住她,有些战栗,紧紧的,仿佛要融进他的身体里,害怕真的有一瞬间会失去她。“怜儿,可不可以不要再这样了,我们好好地好吗?”
她的脸上布满泪痕,紧紧攥着他的袖口,混着泪水转身吻住他的唇,但吻得好难过,心好像也要碎掉了。她用力的咬住他的唇,直到若宗的一丝血迹从嘴角溢出,尝到一丝甜腥。“永远不要抛下我,我只有你一人了”,她踮起脚,在他耳边轻轻的说。
清晨的迷雾中,他们紧紧拥抱着,就像是已经知道了结局,但还是不肯早日放手。
她的余光落在烟雨阁下的桃树旁,一个身着白衣仿若鬼魅的人正在盯着他们,她总觉得那个人的目光淡漠又轻蔑,如同迷雾般难以看清。
“你刚刚为何看我?”她站在雨烟阁高高的台阶上,问着那个仍然站在树下的少年。
那人仍是没有表情的盯着她。
她忘了,那人本是个哑巴的,怎么会回她的话呢。
她几步走下台阶,站到了他的面前。这才仔细的看清了他的样子。那少年眉目清秀的像是个女孩子,但太过于苍白又瘦弱,就像是久病未愈,薄唇总是抿着,眼底放佛绕着一丝缭绕的雾气。
“你叫默言?”她问。即是琴师,不会说但总能听吧。
他点了点头,然后还是直直的望着她,眼底的雾开始翻腾。然后他抬手,往她脸上伸去,擦去了还未干的泪痕。他手指纤细,就像是细柳拂过水面。
“放肆。”她被吓到了,眼睛睁大,直直的后退。
他不做解释,只是就地坐在了桃树下,抬手抚琴。
琴声清冷,阴鸷,寒气逼人。想来果然是音如其人。她听这琴声清凉,觉得消了些怒气与失措,只是驻足听着。
琴声转而又变得悠长而哀切,如杜鹃啼血,子归哀鸣。她又落泪了。对她来说,落泪已是寻常,眸子哀哀欲诉,对着纷纷落下的桃花瓣出神。眼泪一滴滴洒落,风一吹,飘洒到了抚琴人的手背上。
她哭了,他却笑了,仿佛在嘲笑她懦弱敏感又多情。他拭了掉在手上的泪,站起身来。
小怜觉得自己突然被束缚进一个寒冷如冰窖的怀抱里,微冷的舌滑入口中,唇被粗暴的咬破,她又一次尝到了鲜血的味道,那是她自己的。
“你……”,她用力睁开了那个令人生厌的怀抱,伸手打了那个放肆的人一巴掌。
苍白的脸终于增添了些血色。他歪头看着她,笑着。舌头微微伸出来,似乎在品尝余下的鲜血。
又是一巴掌,接二连三的巴掌落在他脸上。
怕是疯魔了吧,积攒的怒火与怨气如今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口。她终于打累了,停下喘着粗气。
他苍白的脸上如今满是红痕,倒显得如桃花迎面,十分妖娆。他捡起一枝桃树杈,在泥土上写了一行字。
“夫人,如此之法,可否解忧啊?”
此时此刻,那少年正似笑非笑的盯着她。
如果她喊人,立刻会有人来将他打死抬走。
但她突然感到不舍了,不知为何,只觉得这疯狂的发泄确是让她舒坦很多。
于是便勾勾手指,叫他继续为她弹一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