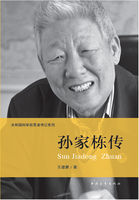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奥本海默没有退缩,没有抱怨,而是重新学习。他像12年前刚刚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授课讲得一塌糊涂,旋即迅速改正一样,很快扭转了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被动局面。他编出了一份详细的实验室人员表,职责分明,按计划要求完成进度,使组织领导重新纳入正轨,完成了从一个纯理论物理学家到巨型科技组织领导者的转变。他以身作则,从早到晚投入工作,戒掉了自由散漫的毛病,以满腔的热情、精确的计划、在行的评估去进行领导,学会了说服、鼓励、规劝、协调。他不仅熟悉所有的科学家,而且叫得出工地上大多数工人的姓名和昵称,了解他们的工作和需要,与他们同甘共苦,很快赢得了广泛的信任和爱戴。有人说:“在工地上,只要有需要,几乎所有的人都愿为奥本海默赴汤蹈火。”在科学讨论会上更是充满了热情洋溢的气氛。奥本海默长于启发大家各抒己见,又善于抓住关键引导人们深入思考。只要有他在场的讨论会,科学家都心情舒畅,满载而归。虽然他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却赢得了绝大多数科学家的爱戴和赞誉。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自愿接受他的领导,年青的科学家甚至把他当作学习的楷模。
然而仍有两件事使这位洛斯阿拉莫斯的总指挥忧心忡忡,情绪压抑。一是特勒给他带来的烦恼。特勒与奥本海默曾同是美国理论物理学界两颗耀眼的新星,一颗在西,一颗在东,遥相辉映。特勒来洛斯阿拉莫斯稍晚,他本以为会让他从事氢弹的研究,没想到来了以后不仅没让他搞氢弹,反让他在贝特领导下的理论部里搞计算工作。他自认为是一流科学家,却扮演着三流角色,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因此心怀不满,处处把气撒在奥本海默身上,在各种会议上与奥本海默作对。两人之间原存的友谊经过几次碰撞,荡然无存,成了势不两立的对立面。二是奥本海默一直受到保安机关的纠缠。虽然他是国家最高军事机密研究计划的技术负责人,但长期以来一直是联邦调查局的侦察对象。从1942年至1944年他的一系列言行,使曼哈顿工程的保安官员对他愈来愈不放心,要把他作为“苏联间谍”对待,进而打报告要“解聘他”。
奥本海默招揽了一大批他的学生赴洛斯阿拉莫斯,这些青年科学家年轻有为,思想活跃,富有创造力,是从事原子弹研制开发的中坚骨干。但是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也同奥本海默早年一样,曾与左翼有过接触或联系。他们有的在30年代甚至不满美国现实,为了探索美国社会的前途而同情共产党或参加共产党。这就触犯了保安人员的神经中枢。他们打报告给华盛顿称:“在苏联窃取对美国生死攸关的最高国防机密的间谍活动中,奥本海默占有重要地位”,“他是极其狡猾的敌人与不忠诚的分子”。奥本海默为了完成科研工作,招聘人才却招致了窃取国家机密情报的罪名,这是奥本海默做梦也未曾想到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奥本海默在加州大学时的密友薛瓦利埃教授在厨房中和他谈起,旧金山壳牌石油发展公司的英国工程师爱尔坦顿能把保密资料送往苏联领事馆。两人纯属闲聊,并无更深层的意思,事后双方已忘得一干二净。1943年8月底,奥本海默也可能出自爱国心,也可能为了摆脱保安机关的纠缠,主动向伯克利分校的保安官员谈起了爱尔坦顿的事。保安官员追问来龙去脉时,奥本海默极力回避谈事情的来源。保安机关紧追不舍,或采取严肃提审,或采取轻松的谈话方式,千方百计要从奥本海默口中追出那个提供线索的中介人,都被奥本海默机智地挡了回去。12月12日,保安机关通过他的上司格罗夫斯将军下令让他交待,不得已他只好供出了薛瓦利埃。从此保安机关加紧了对他的全面监视和跟踪:他的司机是情报人员,他的信件和电话受到全面的监听和检查……一般人很难想象奥本海默为了研制原子弹所背的精神十字架有多么沉重!由于铀235提纯的速度缓慢,总也积聚不到能制造原子弹的份量,因此有人想用钚239作为裂变材料,但又碰到技术上的“拦路虎”。钚239产生的本底中子较多,使用“枪法”速度嫌慢,形不成有效的爆炸,只有借助“内爆法”才能奏效,然而“内爆法”从理论到实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内爆法”不能投入操作,那么到1945年7月只能制成唯一的一颗铀235原子弹,无论从实战或威慑的角度,都不可能实现迫使日本尽快投降的战略目标。整个洛斯阿拉莫斯都为解决“内爆法”,制造第二颗原子弹而揪心。
这时,各路优秀科学家云集洛斯阿拉莫斯,为解决“内爆法”生产钚239原子弹献计献策。费米第一次推算出钚弹的临界质量只需5公斤,大大低于人们原来的预计值,使钚弹的生产露出了第一道曙光。炸药专家基斯泰科夫斯基负责内爆法的全面技术工作,这个组迅速扩展到了600人,几种方法同时全速并进。青年科学家阿尔瓦雷斯完成了新颖的起爆装置,达到百万分之一秒内同时点火的指标。英国爆破专家塔克过去曾在穿甲弹的设计中采用透镜式炸药,使爆炸时不同速度产生的冲击波按照光学原理,像透镜聚光的现象而积聚在一起,形成强有力的爆炸效应。他将这个崭新的技术引入原子弹的起爆,,解决了由于多点点火引起爆破波不均衡产生干扰,以致根本形不成球面波,出现非对称性,严重影响起爆的问题,终于使钚239的芯块能按计划压实到临界质量,产生出最佳爆破效应。数学家冯·诺伊曼还利用刚出世的电子计算机,进行了浩繁的计算分析,把不对称度爆破控制在5%以内,终于解决了制造原子弹的关键难题。
在这期间,奥本海默还要领导下属解决检验、仪表制造、安全防护等技术以及7000余人的生活后勤问题;而每项技术问题的解决都是绝无仅有的开创性工作;仪器需要测量微秒级的时间间隔,检测方法需要全新的构思和技巧,原子弹制造过程中钚的提纯、裂变体的截面加工,保险的引信,放射物的防护……等等,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出了纰漏,都将人命关天。科研工作的节奏,科研人员的协作,生产工序的调整,计划的安排,千头万绪都要他缜密筹措,苦心规划。
1945年3月,鉴于关于原子弹的主要物理研究都已接近完成,奥本海默宣布实施“三一计划”(即原子弹试验。以原子弹实验场命名,取自约翰·唐恩十行诗,以纪念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圣体),7月4日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8月1日完成装配第一颗原子弹。
在这最后关头、许多事情却仍未尽如人意:“内爆法”全尺寸透镜体棋子交货因故延期,炸药雷管性能达不到可靠性的指标,裂变材料供应跟不上进度,而7月中旬风雨交加的恶劣气候,也不适合进行试验。然而,杜鲁门为了在7月15日美、英、苏最高首脑会议上,以手中的原子弹作为砝码,就战后格局压苏联就范,要求原子弹无论如何在7月14日前试验成功。奥本海默夹在大自然和政治风暴中受尽煎熬。为了赶进度,他不时冒风险,在极度焦虑和兴奋中度过了整个春季,体重整整掉了28磅。原来就很瘦弱的奥本海默,几乎完全垮了。
7月16日早上5点半,一颗安装在铁塔上的试验原子弹终于抢在暴风雨的间隙爆炸了。一团巨大的火球陡然升起,然后是蘑菇云,震耳的轰鸣,耀眼的光芒,浓烟迷雾,风暴怒吼,大地颤抖,真是天崩地裂,有如世界末日之来临。所有在场的科学家的心灵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震撼!试验成功了。
奥本海默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有几个人笑了,有几人个却哭了,大多数人惊呆了,一声不响。我心中浮上了古印度圣诗《勃哈加瓦基达》里,克里希那试图说服王子执行他使命的一句诗:‘我是死神,世界的毁灭者!’”奥本海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功地领导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他不仅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工作,更重要的是作为一项空前的科技工程领导者,他能排除一切干扰,艰难而顽强地向着既定目标挺进,充分展示出他的坚韧不拔的品质和高超的决策水平与组织才能。他利用世界一流科学家云集洛斯阿拉莫斯的有利条件,对他们提出的各种技术方案,进行正确评价和选择。最具意义的是,他十分重视具有创造性的思想火花,并能迅速抓住它,及时推动它付诸实施。这就使奥本海默完成了从纯物理学家到科技领导者的转变。他尊重科学家,与工人们同甘共苦,以出色的工作和高尚的人格去赢得人们的信任和爱戴,推动了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关键时刻,大家甚至愿意为他“赴汤蹈火”。
由于奥本海默对原子弹研制工作的杰出贡献,他在1945年后成为世界头号新闻英雄人物,被誉为“原子弹之父”。1946年杜鲁门总统授予他美国功勋奖章,表彰他“伟大的科学经验和能力,他无穷无尽的精力,作为一个组织者和实行者的稀有才能,他的首创性和机智,以及他对责任的坚定不移的献身……”战后,他担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主席,为美国核武器的战略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少数科学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