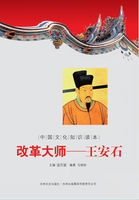由于明王朝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晚期,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皇权被提到前所未有的“至尊”地位,明朝的皇帝们行的完全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独裁路线。他们对待臣民,只要是有异己或稍不顺心,便大肆屠戮,甚至还制定了“廷杖”的刑罚:即对忤旨的大臣当庭杖责,有的人被当场打死。这对于把脸面视如生命的知识分子来说是极大的羞辱,且有生命之虞。在这种政治环境里,文武百僚大都变得唯唯诺诺、顺旨逢迎。不过,明初的几代皇帝还不是那种昏庸式的暴君。他们还是有政治进取心的。为了使自己的大明江山千秋百代地传下去,他们必须要在政治、经济方面施行一些改良措施,对大地主阶级的贪欲进行一些限制。这样,他们又希望能经常有人提一些建议,甚至也允许批评一下时政。为此,都下过一些诏令,提倡让大臣们直谏阙失,还规定了什么“不言者罪。”在这种进亦获罪退亦获罪的情势下,大臣们,特别是一些比较清明的臣僚说话办事只能是吞吞吐吐如履薄冰。事实上,真正因不言而获罪的并不多,以言获罪的倒是大有人在。因此敢于犯颜直谏者就更少了。但是我们敢说,杨士奇可算这为数不多者中的突出一人。关于这一点,宣宗曾对杨士奇讲:“卿能持正言不避忤意。议事之际,先帝数不乐卿,然卿言以不败事。尝有小失,甚悔不用卿言。”(《东里集》王直作《杨士奇传》)
如何提意见既切中时弊又不至于拂耳难入呢?这不仅需要敏锐的政治眼光和极大的勇气,而且还要有巧妙的进谏艺术。士奇当政四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逐渐形成了他独特的进谏风格,从而使自己的意见多被采纳,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鉴于诸臣不敢讲话,成祖在位期间倒是很认真地下过几道命令以鼓励人们直言:
上谕给事中朱原贞曰:“郡县之间岂无一事可言?今在朕左右,尚犹默默,况远在千万里外乎?卿等可以朕意谕之,何利当兴,何弊当革,皆勿隐。若公不言,有他人言之,则无所逃罪矣。”(《明通监》卷十四)“一日,上御奉天门,谕科臣直言,因顾(解)缙等曰:王、魏之风,世不多见,若使进言者无所惧,听言者无所忤,天下何患不治,原与尔等共勉之。”(同上)
“上谕郑场曰:不罪直言则忠告言进,谀言退。”(《明通监》卷十五)
但是,进“谀言”还是大有人在。
永乐十二年元旦那一天日食。这之前皇帝问礼部和翰林诸大臣:“正是元旦这一天日食,百官还行不行贺礼呢?”礼部尚书吕震是个惯于溜须拍马的家伙,他从不放过一个讨好的机会,于是赶紧说:“日食与朝贺不在同一时辰,应该如期举行大庆贺。”而礼部侍郎仪智却不同意说:“但毕竟是同一天呐,还是免了吧。”士奇非常鄙夷吕震的为人,他站出来坚决主张免贺,接着他又举出宋仁宗时元旦日食免贺的例子来驳斥吕震,劝说皇帝,最后成祖同意了士奇的意见。“上曰:‘君子爱人以德,士奇与智言是也。’”(《东里集》王直作《杨士奇传》)免去了繁盛的贺礼贺宴。
以日食而主张免朝贺,应当称是一个迷信论点,但也从侧面反映了杨士奇不无端逢迎,反对铺张,能秉公论事的正直性格。
永乐二十二年(一四二四年)七月,成祖去世,八月,朱高炽以太子身份继承皇帝位,这就是历史上的明仁宗,年号洪熙。仁宗性格不那么刚烈,也较乐于纳谏,加之他在二十年监国中,遭受过种种打击,全仗士奇等人为他排解纷扰,因此,对于这位患难与共的忠臣的建议,自然是言听计从。他一即位,便提拔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这是明史上内阁大臣第一次担任六部职务。“上践作以来,士奇、荣等皆东宫旧臣,俱掌内制,不次超迁,然居内阁者,必以尚书为尊,自荣后,诸入文渊阁者,皆相继晋尚书,于是阁职渐崇。”(《明通监》卷十八)仁宗朝,是内阁权力增大的重要过渡阶段。
这次提升之前,仁宗曾对士奇说:“自今朝廷之事,全仗蹇义和你了。”要先封他二人的官。士奇的态度非常明朗,说:“汉文帝即位时,先提拔他的亲信宋、昌,历史上皆批评之,还是先提拔扈成祖北征的有功之臣吧。”杨荣与金幼孜在成祖时多亲随北征,因此他们都得到了提升。杨士奇这个意见,既规劝了仁宗要任人为贤,又体现出他不以宠臣自居傲视别人的谦虚美德和宽阔胸怀。仁宗很钦佩他这种品格,对他更加信赖了。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为了发展生产,稳定封建秩序,一面招抚农民开荒,一面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使明初的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朱元璋的继承者也基本上遵循了这种路线。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随着经济发展,明统治者们出于他们的阶级本性,贪欲日益增大,因而出现了对人民徭役赋税越来越重的趋势。明成祖为了营建北京,永乐十五年——十八年(一四一七——一四二0年),动员了三十万优秀工匠和上百万农民参加修建工程,这对人民无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一四二0年的唐富儿起义,正是剥削惨重、徭役繁多的结果。尔后的皇帝们,随着他们追求享受的欲望增大,宫廷开支剧增,因此对百姓征收的赋税越来越没有名堂了。此时的杨士奇虽然长期生活在上层,但是由于他三十多年的平民生活,使他能够理解人民的疾苦要求,能够清醒地分析现状。他出于对明朝根本利益的考虑,不断地向皇帝进谏,批评和制止了种种增派赋税徭役的做法,减轻了百姓们的一些负担。
仁宗继位后,下了一道命令:同意宫廷岁用征收减半。这命令下了两天后,杨士奇便听到惜薪司准备按旧例向北京、山东年征大枣八十万斤为宫中烧香炭所用的消息,并听说已得到了皇帝的批准,他很不满意,准备提意见。一天,仁宗在便殿听蹇义、夏原吉奏事,看到杨士奇来了,便对二人说:“新任华盖殿大学士来了,一定是有直言相告,我们不妨一同听听吧!”这时士奇上前进言道:“朝廷关于减轻岁供的诏书下了才两天,可是惜薪司还在传旨征集大枣八十万斤,实在太多,这不是和朝廷下的诏书相违背了吗?”仁宗接受了士奇的意见,高兴地说:“我就知道大学士说出来的话必定有道理。这些日子我的事情太忙,那件事(指征枣)是我一时仓促回答的。”于是马上重申,大枣征收减半。仁宗诚恳地说:“你们三人是我的得力助手,有什么话都应该说出来,以纠正我的过失。”他认为士奇这人忠诚可嘉,便又升他为少保,然后赐给他与杨荣等人每人一枚刻有“绳愆纠缪”的银章,以示自己纳谏的决心,他还准许这几个人可以密奏重大国事,不久士奇又被晋升为少傅,权力就更大了。
仁宗由于监国二十年,所以他有着较丰富的经验,懂得“国以民为本,民安则国安”的道理。他很痛恨一些地方官吏侵扰百姓的行为。为了使自己不被蒙蔽,他一再鼓励大臣直言。一次他对士奇、杨荣、金幼孜说:“你们三人和蹇义、夏原吉都是先帝旧臣,我正要依靠你们的辅助。不少皇帝恶闻直言,他们的亲信都是畏威顺旨,而忠臣们由于提了意见不被接受,亦表示不言。我和你们都应该深刻地记取这种教训呀!”正由于仁宗有这种勇于纳谏的作风,士奇提的建议、批评,才不断被接受实施。
洪熙元年(一四二五年)正月,全国各地的地方官来京朝贺。趁着仁宗高兴,兵部尚书李庆对皇帝说:“现在民间牧养的马繁衍很快,有不少已散到军伍之中,目前还剩下几千匹,请您下令,让在京的朝觐官们领去饲养以减轻民间负担,让正官领一匹公马,佐贰官领一匹母马,然后每年收他们的马驹子,如有了亏损,也与百姓一样,令其赔偿。”这个建议貌似同情百姓,官民平等,实际上是一个媚上压下,非常可笑的主意。它不仅于国家收入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影响又很坏。杨士奇一听就反对这个意见。李庆非常生气,不顾杨士奇的劝阻,一意孤行。于是士奇便单独晋见皇帝,指出:“当今朝廷征求天下贤能者任官,却又让他们去养马,还要象百姓一样收他们的税。难道这是重人才贱牲畜吗?”第二天他又上奏:“如果一定要颁行此令,天下的贤能之士谁愿意来做官呢?亏损一匹马一定要赔偿,耗费了全家资产还累及子孙,朝廷如何以此名声而负天下和后世呢?”皇帝听后答应马上制止此事,但是过了几天仍不见皇帝的指示下来。士奇不罢休,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他又亲自上街视察。他向仁宗汇报道:“兵部现在已经督使朝觐官领马去了,而他们散出去的多是些没驯过的生马,那些南方人都很脆弱,根本驾驭不了,眼看着野马在街头逃逸,无法追回,只好号泣于街头。看来这个命令的错误真是太大了”。仁宗漫不经心地说:“我偶然忘了。”中午,仁宗来到思善门,把士奇召来说:“我哪里是忘了这事呢?我是听说吕震、李庆都很嫉恨你,我怕你遭到别人攻击,处于孤立的地位,因此不愿意由你制止此事。现在咱们可有话说。”说着他拿出陕西省按察使陈智的《言养马不便疏》,让士奇以此写一道诏令制止分马。士奇一听非常感动地说:“陛下这样信任我,我并不孤立啊!”仁宗说:“今后行此令若有不便,你只管和我私下说。李庆、吕震这些人不识大体,不足以和他们商量。”没多久,仁宗就罢掉了李庆的职务,让士奇兼兵部尚书,领三份的俸禄。这样一来他就身兼三职:少傅、兵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由此可见,仁宗倒是一位善辨忠奸的明君,他对士奇的信任到了宠爱的地步。但是杨士奇并没有借宠逢迎,而是更加谦恭和忠心耿耿地向皇帝进谏,批评时政。士奇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有着他明确的政治抱负的。我们从下面的这段对话可以窥其一二:
一次仁宗对士奇说:“我办事情如有过失,退朝后就很后悔。如果此时大臣正好说到了这一点,那我会感到很痛快。”士奇说:“宋朝宰相富弼说过:‘愿不以同异为喜怒,不以喜怒为用舍’。”仁宗说:“是的,书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群臣所言,即使有人讲的很不中听,我退而自思,若确实是我错了,那我也不会怪罪他。”士奇说:“成汤能够善于改过,所以才成为圣人。”仁宗说:“我有不对的地方,主要是怕自己不知道,如果知道了并不难改。”
从这番对话,我们可以看出杨士奇作为一个开明的政治家,热情地希望自己能成为成汤文武那样的圣人,因此他非常佩服“耻君不尧舜,以谏争为己任”的唐初魏征。实际上,他在某些方面也起到了一个唐朝魏征应起的作用。这样,明朝前期也出现了一个为史家所称道的“君明臣直”的政治局面。
洪熙元年四月,有人为了逢迎新皇帝,上书歌颂太平盛世,仁宗看过后拿给杨士奇、蹇义、夏原吉、杨荣等人看。不少人看过后,都点头称是。蹇义说道:“陛下即位以来,所行的都是仁政,百姓们再没有科敛徭役之苦,现在真是治世呀!”很明显,这是一种不合实际的吹捧。这时唯独杨士奇没有高唱赞歌,没有粉饰太平,而是实事求是地对现实进行了正确的估价。他说:“陛下虽然恩泽天下,但是现在仍有流民无家可归,战争的创伤还未医治好,国内还有吃不上饭的人。看来,必须再休养上几年,太平日子才会到来。”这一席话,压住了阿谀奉承的不正之风,给产生了骄傲心理的仁宗敲响了警钟。仁宗逐渐冷静下来,连连称是,他转向蹇义等人说:“我对待你们非常至诚,是希望你们能够经常匡正我。但是现在唯有士奇曾经上书五章,而你们却无一言可进,难道朝政果然没有缺点,天下果然就太平无事了吗?”这番话把另外几个羞得满面惭色。
事实上,在当时辅佐皇帝的大臣中,杨士奇不仅具有冷静的头脑,而且更具有敢于针砭时弊的正直品格。他除了自己直谏外,还支持其他官员大胆上书,当这些人遭受打击时,他也能站出来,为他们申辨。
仁宗皇帝继位之初,提拔弋谦任大理少卿。弋谦为人十分耿直,敢于议论朝政。他特别痛恨那些贪官污吏的残暴行为,多次上书请求制裁,仁宗都接受了。但后来他又提了五条意见,因为言辞过激,引起了皇帝的反感。礼部尚书吕震和都御史刘观都是些专事逢迎的谀臣,他们善观风向,喜欢揣摸皇帝的心理。现在看到皇帝不高兴,他们立刻纠合了一帮人攻击弋谦,说他是借批评时政来诬蔑朝廷,应当论罪。皇帝于是问杨士奇该如何处理,士奇直率地说:“弋谦这人讲话虽然过激了些,但他乃是一片忠心,想报效朝廷。古来主圣则臣直,因此请陛下一定要宽怀容人。”皇帝虽然没有治弋谦的罪,但因多位官员的弹劾声常在耳边回响,他心中依然很愠怒,一方面要弋谦任事如故,另一方面又不让他上朝。士奇觉得这样下去不利于君臣共事,便又从容地对仁宗说:“陛下,是您下命令让大家提意见,说讲错了也不怪罪。可您现在却因为弋谦提意见而如此生气,那以后朝臣们就害怕了,谁还敢提意见呢?若传出去,人们都会说朝廷不能容纳直言了。”这番话虽然引起了仁宗的警觉,但他仍然很不痛快,说:“可现在大家都在说弋谦的不是呀,以后不要让他见我算了!”果然,从这以后提意见的人越来越少了。仁宗开始有些不安了,他忙把士奇找来解释:“我不是讨厌弋谦提意见,而是嫌他言过其实。你看群臣让我治他的罪我都没有治,只不过免去了他的朝参。但从那以后言事者果然越来越少。现在请你把我的心意向大家转告一下。”士奇不错过这个机会,说:“这不是我讲了人家就会相信,一定要您下诏书才行。”仁宗为了挽回影响,便请士奇代笔检讨了自己的过失,表示今后一定会待谦如初,并希望大家不要以弋谦的境遇为戒。不久,仁宗又提拔弋谦当了副都御史。在那种君主权威至高无上的封建社会里,一个皇帝能够这样主动地引咎自省,一个臣子能够为一件事这样三番五次地犯颜直谏,确实都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