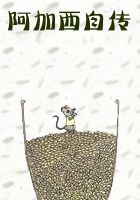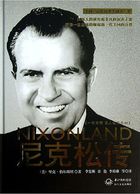——刘文典与胡适
刘文典(1889—1958),原名文骢,字叔雅,安徽合肥人。著名学者、教授。
刘文典少时进教会学校读书。1906年考入芜湖安徽公学学习,敏而好学,深得该校教师陈独秀和刘师培器重。受陈独秀影响,萌生反清反帝、追求民主自由思想。1907年加入同盟会。两年后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求学,追随国学大师章太炎,听其讲《说文》课,国学功底大进。参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工作,宣传爱国反清思想。辛亥革命爆发之后,1912年回到上海,与于右任、邵力子等办《民主报》,以天明、刘天明等笔名撰文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他再东渡日本,加入革命党,任孙中山秘书处秘书一职。1916年归国后,对革命颇为失望,决定远离政治,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1917年,他的老师陈独秀携《新青年》至京,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推行教育改革,广揽人才。应陈独秀之邀,到北京大学任教,先后开十多门课,颇受学生欢迎。教学之余,潜心从事古籍校勘。在北京大学十年间,是他学术上最有成就的时期,先后出版《淮南鸿烈集解》《三余札记》《说苑校补》《庄子补正》等多种著作。自1916年始,他便在《青年杂志》上发表作品,改成《新青年》后,他任该刊英文编辑,利用自己精通英、日、德等外文的特长,翻译介绍大量外国著作,如叔本华的哲学著作。1927年,他接受安徽省政府之邀,回皖积极筹备安徽大学的建校工作,大学建成后,刘文典担任法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代行校长之职。1928年,因当面顶撞蒋介石,险遭枪毙之灾,后经多方营救,释放。1929年,他再回到北京大学任教授。不久,应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之请,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一度曾代理过该系系主任。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被日军占领。刘文典闭门在家,不参加任何活动,也不讲一句日语。第二年他几经辗转,到云南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任教。1943年转云南大学文史系教书。清华大学在北京复办,刘文典未归而滞留云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继续在云南大学任教。开设温李诗、杜诗研究、文选学、校勘学等课程,主持过杜甫研究室。主编《杜甫年谱》《群书校补》《王子安集校注》(未完成)等书。因其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卓著,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
1958年7月15日,刘文典因罹患肺癌,在昆明逝世。
“看风格,要看这些地方”,是余英时先生的话,在这里,讲的是胡适、刘文典“这些地方”。
据说,自古学人是分“通儒”和“俗儒”的。“居则玩圣贤之词,动则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当时之事,此通儒也”,即大儒;而“能纳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讲诵而已,无能往来,此俗儒也”(汉《风俗通义》)。
如清代的汪中,自称通儒,论思想,论学问,的确了得,但他狂傲,既目中无人又喜欢骂人。“不恕古人,指瑕蹈隙,何况今人,焉免勒帛?众畏其口,誓欲杀之,终老田间,得与祸辞!”(《公祭汪容甫文》)骂人太甚,引起众怒,逃到乡间,免得一死。
刘文典,系民国初年的一介狂儒,不亚于汪中。曾因在1909年拜访国学泰斗章太炎,谈笑甚欢,遂成为其弟子。自此学问益进,狂傲也有增。
(一)
在西南联大教书时,从不把闻一多、朱自清等才子作家放在眼里,讲课时,对他们多有轻蔑之语,对已有名气的青年作家沈从文更是蔑视得很。得知西南联大欲提拔沈从文为中文系教授时,刘文典颇为不屑地说,陈寅恪才是真正教授,他拿四百大洋理所当然,我拿四十块足矣,朱自清也只能拿四块,至于沈从文,怕四毛钱也不值。“他若是教授,我是什么?”当教务会上,众教授都举手同意沈从文升为教授时,他勃然大怒道:“沈从文在北大时是我的学生,他若当了教授,我岂不是要作太上教授了吗?”
刘文典之狂,并不畏强凌弱,不仅对学人如此,即便是对蒋介石这样的党国魁首,他也毫不畏惧,敢于犯上。他在安徽大学初创之时,学校发生学生风潮,蒋介石以政府首脑的身份到安徽弹压。召见代校长刘文典,刘文典不称“主席”,只叫“蒋先生”,蒋大为不悦,蒋命刘文典交出学潮中的共产党人,刘文典答道:“我只知道教书,不知谁是共产党。”并以“情况复杂”为由,拒绝严惩闹学潮的学生。蒋介石自然恼火:“你这个校长是怎当的?不撤掉你这个学阀,就无法告慰总理的在天之灵。”刘文典也被激怒了:“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发动革命之时,还不晓得你的大名哩!你讲我是学阀,我就说你是新军阀。”蒋介石龙颜大怒,抬手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把他抓起来,关进监狱,听候发落。
蒋关刘的事,一经披露,舆论大哗,学生游行示威,要求放人,后由蔡元培、陈立夫出面斡旋,才以刘文典“即日离皖”为条件,开释刘文典。老师章太炎病中闻之,即赋对联相赠,曰: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对弟子刘文典的文人气节大为赞誉。上联用晋代狂士嵇康蔑视司马氏的典故,下联用三国名士祢衡击鼓骂曹的史实,比拟其弟子刘文典的刚正之举。
说起来,刘文典狂傲和狷介,还真有点儿像自己的老师章太炎。当年,章太炎就曾有将袁世凯颁发的勋章,倒将起来做扇坠,赤足在大堂跳骂袁世凯倒行逆施的逸事。今见弟子继承自己的衣钵,敢于仗义执言,岂有不赞之理!
刘文典狂傲,但对有真学问的人,充满敬畏。对老师章太炎、陈独秀尊重有加,从不放狂。对像人称“教授之教授”、“大师之大师”的陈寅恪这样的学者,刘文典当然十分敬重。他研究庄子有成,写出《庄子补正》,陈寅恪特为之作序:“先生此书之刊布,盖为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有陈寅恪之序,刘文典顿时身价倍增,让他获得“庄子专家”的荣耀。一贯恃才傲物的刘文典,从此更为狂妄,他说:“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某人。”
刘文典除狂傲还争强好胜,一般从不服人。他的朋友学者吴宓,一大学问家,深得陈寅恪器重。在西南联大时,开过“红楼梦讲座”,听者甚众。刘文典听了几次,自诩比吴宓更懂《红楼梦》,就也开课大讲红学。刘文典讲课,有几分“索隐派”的味道,旁征博引,也吸引不少学生前去聆听。对台戏唱得热闹,成为西南联大一景。
刘文典在日本师从章太炎学《说文》时,与鲁迅相识。他被蒋介石抓入牢中,学界抗议,鲁迅并未念旧而声援过他。在西南联大讲课时,偶尔提到鲁迅,他举手伸出小拇指,未作口头褒贬。20世纪50年代初,有人揭发此事,经过多次政治运动,学乖了的刘文典坦然一笑,承认确有伸小拇指一事,但他解释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小拇指喻指我们同学中最年少的鲁迅有什么错吗?实际上鲁迅比刘文典大十岁。那时伸小拇指,褒贬自明。
(二)
“活庄子”刘文典,恃才傲物,对胡适却心悦诚服。
1921年,北京大学成立研究国学机构,胡适拟出一个计划,想把有价值的古代文化典籍整理出来,既继承传统又古为今用。每一种书成为可读的单行本。胡适让刘文典负责整理《诸子文粹》和《论衡》两部书。后经胡适筹措,创办《国学季刊》,成立了编委会,胡适特邀刘文典担任该刊编辑。
原本国学功底深厚,又得章太炎真传的刘文典,经过潜心研究,终于完成《淮南鸿烈集解》学术专著。这是刘文典第一部研究古籍的书。他很看重,在出版前,他找到胡适,请他为此书作一篇序。他还向胡适提出一个具体要求,要用文言文写而不要白话文写。这让胡适为难了,正是胡适率先倡导白话文,从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使“无声的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胡适不仅用白话文写作,还出版了白话诗集《尝试集》;鲁迅用白话文创作,成了白话文运动创造出来的乘时势的英雄。但是胡适还是答应了刘文典的请求,用文言文写了一篇漂亮的序。序文一出,立刻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支持白话文和反对文言文的人纷纷猜测,莫非提倡白话文的急先锋胡博士又要复古了?
正是胡适用文言文作序的《淮南鸿烈集解》的出版,刘文典得到学术界的公认而确立了自己在国学方面的地位。
说到作序,为刘文典所作之序,让刘文典名声大振,但有时,又会遭谤议。如张东荪的哥哥,即《玉溪生年谱会笺》的作者张尔田,也是一个有个性的文人,他最恨胡适。他的好朋友陈援庵写了部《元典章校补》,请胡适作了序。张尔田闹到陈援庵的家里,说非要把胡适作的序从书中撕掉。胡适闻之,一笑而已。
比起刘文典的狂傲,胡适则是谦和和仁爱的,更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学者。两人性格截然不同,这不妨碍他们成为挚友,况他们又有同乡之谊。但胡适之所以帮助刘文典,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有共同之处。
刘文典敢于顶撞政坛新贵蒋介石,斥责他专横跋扈,被蒋投入监狱,胡适为营救他全力以赴。胡适看中的,正是刘文典身上那股精神自由刚正不阿的个性。胡适独特的人生经验和思想旅程,使他渴望入世,渴望对话,渴望开诚布公,渴望肝胆相照,渴望人人选择个人的人生方向,渴望文人学者有自由精神的个性。刘文典是他的知音之一,所以他们成为朋友。
1927年,“刘文典事件”之后两年,胡适与罗隆基等新月派作家发起了一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人权运动”。胡适在当年四月的《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该文以“刘文典事件”为例,抨击蒋介石:“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与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鲁迅也曾就“刘文典事件”发表过意见,有趣的是那是发表在1931年12月1日《十字街头》杂志的《知难行难》,署名佩韦。文中并无对蒋介石的声讨,只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鲁迅此文并非针对蒋介石,而是针对胡适1929年6月发表在《新月》上的《知难,行也不易》一文的。而且,鲁迅的《知难行难》的发表,已距“刘文典事件”之后四年多,与胡适发表《知难,行也不易》也有两年,特别是胡适发表《人权与约法》之后,又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犀利的文章。为此,1929年10月4日南京政府教育部发出公文,对胡适给予警告处分。胡适毅然以辞职抗议。鲁迅对此无动于衷,矛头不对蒋介石,而却攻击遭到国民党处分的胡适,其动机明白人自然了然。
我们再回过来说“刘文典事件”。刘文典被迫辞去安徽大学校长一职后,走投无路,他想到了同乡胡适。于是写了一封信给北平的胡适,请他施以援手。胡适一直密切关注“刘文典事件”的发展,对他的处境十分同情。见刘文典信后,他找到蔡元培。北大校长蔡元培早对刘文典为保护学生顶撞蒋介石的正义之举深表敬佩,遂力邀刘文典回北京大学任教。
(三)
与刘文典自诩是庄周之外第一个懂庄子的狂傲不同,胡适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谦谦学人。用学者余英时的话说,胡适“把自由主义的香火在中国保存下来,他的功绩最大”,“胡适在学术思想上有‘开风气’的大功”,在“提倡现代价值方面,如自由、民主、容忍等,他的贡献到今天还未完全失效”(《余英时访谈录》)。
有许多人都未真正了解胡适。如1980年,胡绳等学者访问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教的余英时,余英时请他们一行吃饭。席间在谈到胡适时,胡绳说:“我们对胡适,政治上是反对他的,但学术上是尊敬他的。”这番话比起“文革”前把胡适妖魔化,视其为无产阶级的敌人的官方立场,无疑有了进步,那时胡适的学术成就也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糟粕。余英时以跟他们开玩笑的口吻说:“我的看法跟你正好相反,我认为胡适在学问上早被人超过了,但政治上还没有被人超过。”胡绳自然知道余英时在说什么,他很有风度地不再争论。
刘文典是有成就的学者,有时会忘乎所以,有点老子天下第一的味道。胡适早就因开启新文化运动而让天下无人不识君,他的学术研究成果也让他享誉海内外,但他对“暴得大名”有极清醒的认识。在政治上,他主张每个人都要有声音,每个人都能得到尊重的这样一种民主制度。为此,他不赞同蒋介石的独裁。他不断写文批评国民党政治的反民主、反自由的丑行。他在就任中研院院长时,当众说:“总统错了!”对此,余英时在《余英时访谈录》中说,“看风格,要看这些地方”。
刘文典以文人的良知和血性顶撞蒋介石,而胡适则是继承中国文人的风骨道义,“以道抗势”的传统,批评蒋介石。
胡适与刘文典皆为“五四”学人,为人处世也各有不同,各有风采。
胡适在与人讨论学术问题时,坚持真理,却心平气和。比如胡适早年提倡白话文,他的好朋友任鸿隽、梅光迪、唐钺等人极力反对。双方在激烈笔战中,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后来相持不下,各自坚持,但都心平气和。
梅光迪尤为反对胡适提倡以白话文写诗,胡适就偏偏写了一首千行白话诗戏逗他。其中有: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
古人悬梁,今人上吊。
古名虽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尝不妙?
……
一场严肃的论争,因有这样诙谐的诗出现,双方顿时开怀大笑。
而刘文典生性爱争强好胜,总想胜人一筹。
他专心研究古典文学,看不起作家,巴金当时的《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刘文典不屑一读,连巴金是谁都不知道。对年轻的作家沈从文升为教授,更是说三道四,口出狂言。即便是对研究古典文学的朋友吴宓,也同样不失时机地打压一下。刘文典讲课,常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内容,新鲜而有深度。学生很爱听,许多校内外的著名教授也都去旁听,他的朋友吴宓更是常客。吴宓总坐在最后一排,认真听讲并记笔记。刘文典讲到得意处,常常紧闭双眼,口若悬河。这时,会突然睁开眼睛,向坐在后面的吴宓发问:“雨僧(吴宓字)兄以为如何?”吴宓照例站起身,恭恭敬敬点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然后悄然坐下,每到此刻,刘文典的脸上便泛起狡黠的笑,学生也就吃吃暗笑。
他看不起沈从文,就设法捉弄他。在西南联大时,日机空袭,警报即响。师生照例疏散躲避。一次警报又响,师生又四处躲避,刘文典刚巧与沈从文不期而遇。他面有不悦之色地对学生说:“我刘某人是为庄子跑警报,他沈从文替谁跑啊!”沈从文尊他是前辈,并不计较地跑开。
刘文典与胡适的友谊,经受了风风雨雨的考验,伴着他们都去了天国,一直弥漫着一片无比温暖的文化情怀。
“五四”学人,如胡适和刘文典,他们鲜活的复杂个性,他们之间的相轻与相重,是躁动的、痛苦的时代生活在文人心理上反弹出的内容,是文化心理的一种反映。在那世局交相嬗替之际,远远超过一介文人道德情操的意义。研究、审视他们,如同研究、审视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