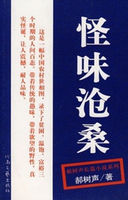那辆桑塔纳到达郑家湾时,郑青禾老师正在河堤上散步。这年头,像她这种年届不惑又身智健全的人,不是忙着赚钱就是忙着当官,能悠哉悠哉地在河堤上漫步的实在是凤毛麟角了,怪不得她的同年堂姐郑鹂歌就说她“胸无大志”。
奠耳河十分开阔,村头一棵千年老榕,亭亭华盖荫庇了半个村庄,从树下跨出去的箭啸桥,直直地射向对岸。间或有轻舟从桥洞里穿过,河面就泛起细细的涟漪。几只白鹅漂在水面上,神定气闲得好像打坐的智者。
对于这条稔熟的母亲河,郑老师只有欣赏的份儿。7岁那年她和鹂歌一帮小伙伴一起下河学游泳,别人都抱着家里的大门闩下去,尽兴之后再抱着大门闩回家;只有她的门闩在水里打了个滚跑了,她连喝了几口水就沉下水去,直到明晃晃的河底。当大人们七手八脚地把她打捞上来时,她已经双目紧闭没气儿了。闻声赶来的父亲把她横撂在牯牛背上,用鞭子抽得牛满村子疯跑,就有一股股的清水从小青禾的鼻孔里冒出来,这样跑了半个时辰,肚子里的水颠光了,她才悠悠地醒了过来。几天之后,一个瞎眼的算命先生摸到了她家,他掐着肮脏的手指念念有词了半天,对她妈说:你这囡儿是火命,水火不相容,从今往后再也别让她下河了。
可是河水非常温柔,一点也没有吞噬人的意思。夕阳的余晖染得水面金光闪闪。一只青蛙从田里蹦了出来,不要任何过渡就直接跃入河中,然后以漂亮的泳姿向河心游去。除了郑青禾,郑家湾个个都是游泳高手,他们向青蛙学得一身本领。上初中时,鹂歌还得过地区少年蛙泳冠军呢。
河边是块蚕豆田,蜜蜂忙碌着,嗡嗡嘤嘤地唱着劳动歌谣。隔了这块豆田,就是郑青禾所在的郑家湾小学了。每天傍晚,郑老师送走最后一个学生之后,就到这里来看看庄稼看看河水,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豆秆高高的很是挺拔,顶端正开着蓝紫色的蝶形花朵,下边的嫩豆荚却可以摘吃了。女儿逗逗躲在豆垅中间,她爱吃生嫩豆子,说那是最香甜的美食。逗逗也爱吹豆秆笛儿,折一截尺把长的豆秆,拿剪刀剪出6个等距离的小洞洞,就可以吹出最原始的音乐来。对于这块豆田,逗逗有一种特殊的感觉,钻进里面就不想出来了。
太阳落山了。郑青禾喊:逗逗啊,该回家吃晚饭了!她的喊声像奠耳流水一样不徐不急,柔软绵长。
逗逗蹑手蹑脚地出来,从背后一把抱住了母亲。12岁的女儿已经高达母亲的耳垂了,她的脸型很好,嘴角翘翘的,显得喜庆,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总是弥漫着一层水雾。谁能看得出,10岁之前的逗逗一直病得不轻,好几次都差点要了小命!
逗逗转过身子,将脸贴在妈妈的肩上,娇呓着说,妈,我想哥哥了。青禾摘下她头发上的蚕豆花瓣,说,这么大了,还想啊想的。逗逗耍赖般说,就想就想,后天就大礼拜了,哥哥说带我捉蟹去!
16岁的安遥在乐川市实验中学读书,两个星期才回家一次。郑青禾揪了下逗逗肉肉的耳垂说,就知道捉蟹,别让蟹把你给捉了去!
就在这时候,那辆鬼鬼祟祟的桑塔纳停在郑青禾的身边,从车上下来一男一女,男人白脸,女人黑脸,他们架起郑青禾,不由分说塞进了车里,车门碰上了,小车绝尘而去。
乐川市柳镇镇长郑鹂歌驾着自己的小别克,和那辆桑塔纳擦肩而过,但是她并没看见车里的堂妹。
鹂歌比青禾大两个月,小时候她们一块儿玩耍,一块儿上学,一块儿参加学校的文体活动。两人模样儿都好看,可性格差异就大了去了,鹂歌从小就要强,跳舞是领舞,唱歌是领唱,就连玩个抓子儿踢毽子什么的,也样样要抢在前头。从小学到中学,鹂歌一直当着班里的“主要领导”。
她们一块儿高中毕业,又一块儿在郑家湾小学当民办老师。再后来郑鹂歌转了正,调到柳镇中心小学去了。她们同年结的婚,第二年,郑鹂歌生了女儿萌萌,郑青禾生了儿子安遥。接着鹂歌当校长,当镇教办主任,当副镇长直到镇长。随着她职务的不断升迁,同学和玩伴一个个都生分了,姐妹俩却没有疏远。郑鹂歌虽然有萌萌,却也喜欢逗逗,得空给逗逗送点好吃的,或者带着她去买个书包、裙子什么的。
鹂歌把车子泊在箭啸桥头,自己顺着河岸下来。她左右看看,没有青禾和逗逗,就以为这娘俩躲在豆垅里。青禾和别人不一样,她就有闲情逸致坐在田塍上编花圈,田塍上的矢车菊和野绣球花型可爱颜色娇艳。鹂歌高一声低一声地呼唤着,却不见回音。在鹂歌的眼里,堂妹有点不思上进。单位里评先进评职称什么的,她总退总让。鹂歌就替她愤愤不平,有一回她不客气地指着她的鼻子骂:你是死人吗?张显然比你迟两届,又是这么个烂水平,竟让他把你的小教高级给抢了去!你退你让,你退让到阎王那儿去吧!说这话的时候,郑鹂歌已经是柳镇副镇长了,而郑青禾至今仍是个普通小学教师一个。
可是堂妹的语文课讲得真叫精彩,别说学生,连鹂歌都被迷住了。青禾宠爱学生到不可理喻的地步,比如她给逗逗买的花生糖豆,孩子们可以一抢而光。孩子们玩击鼓传花时就去她家拿脸盆,她家那两个搪瓷脸盆上的块块黑斑就是孩子们奋力敲击的结果。
鹂歌心急火燎地跑到青禾的家里。家是她们的祖上老宅,一个小小的四合院,她爸和青禾爸各占一半。鹂歌父亲跟金寡妇跑了以后,母亲就气死了;叔叔和婶婶又被在外地工作的堂哥接了去,现在偌大一个四合院,只住着郑青禾和逗逗娘儿俩。
她一进门,就发现逗逗哭得惊天动地的,学校的炊事员何久久正给她服抗癫灵。逗逗一见她,绝望地哭喊着:鹂歌姨,我妈被人给抓走了!
鹂歌的心一下子全乱了。
青禾被带到一间办公室里。白脸男人翻开个夹子,拿出张纸片晃了晃说:这是乐川县人民医院的孕检报告单,时间是1995年10月19日,结论是怀孕3个月。郑青禾问,跟我说这个干什么?白脸男子说,你没见上面是你的名字吗?郑老师说,天底下叫郑青禾的人不止我一个吧?白脸男子说,可我们乐川叫这个名字的却只有5位,其中两名是男的,三名女的中间,一名是80岁的耄耋老妇,另一名今年刚满16岁;你怎么解释?郑青禾说,我根本就不用解释。男子说,有人举报你计划外超生。青禾说,除安遥之外,我没有怀过第二次孕。男人说,你不是还有个女儿吗?青禾说,逗逗是弃婴,人家把她丢在蚕豆地里,我捡回来养着,就这么回事。
黑脸女人的眉毛动了一下,说,就按你说是捡来的,可当时为什么不送派出所?郑青禾说,送过啊,逗逗还上过电视呢,可就是没人认领。黑脸女人说,为什么不送福利院?郑老师说,那时候我们乐川还没有正经的福利院,只有一位文盲老太太和一个小姑娘照看着几个残疾孩子,可我还是送去了。办手续时,逗逗一直紧紧抱住我的脖子不松手。后来我狠了狠心,掰开她的小手,她一声惨叫,牙关紧咬,浑身抽搐,就昏死过去了。老太太大呼小叫着说:羊角疯,这孩子犯羊角疯!你行行好抱走吧,千万别让她死在我这里!
羊角疯?恐怕是佯装疯吧?白脸男子说。
“你倒是找一个两岁的孩子装疯给我看看!”郑青禾尽管脾气好,这时也有些恼怒了,“我抱着她从福利院出来,就直奔医院。医生说,那病叫癫痫,不容易好,且要时刻留意着,昏厥时身边没人就危险了。从那以后,我们一家寸步不离地照看着她,隔三差五地带她上医院,心想待她身体好了再把她送走。可每送一次,她就犯病一次,嘴唇紫绀,口吐白沫,浑身抽搐。弄到后来,我实在不忍心再送了。
男子说,她就是你亲生女儿,你偷偷地把她生在外地,然后让人扔回郑家湾来。
“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郑青禾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白脸男人说,你嘴犟没用,我们可是要做亲子鉴定的!郑青禾说,做吧。男人忽然转了话题,问,安逗逗的户口是怎么落实的?
郑青禾说,逗逗的户口倒是让我们伤了好大的脑筋。后来,是郑家湾村委会看我们艰难,给逗逗上了个农村户口。
郑青禾站起身来,抻了抻衣襟,说,10年时间说长是长,说短也短,能证明她身世的大有人在,你们调查去吧。
郑鹂歌在美容床上放松着身子。每当她心绪烦乱时,她就要到这里来放松一下。今天她在镇北的苍山深处忙了一天,处理一起因水源引发的恶性械斗事件。苍山械斗历史悠久,已成顽症了。分管副镇长李勇是个好人,却缺乏杀伐能力,所以她就亲自出马了。今天她不断地爬坡下坡,察看现场,制定分水方法,拍桌打凳地狠训了几名为首的肇事者,累得骨头架子都散了。一回家,就听说有人查郑青禾的超生问题。她忐忑着,急急地赶往郑家湾,想对傻乎乎的堂妹提示几句。哪晓得还是晚来了一步!
美容小姐招弟软滑的双手,在她的脸上舞蹈着。这双手很体贴,很善解人意。
再过几个月鹂歌就满40了,“男人四十一枝花,女人四十豆腐渣”。她不由自主地皱了皱眉头,老天爷就那么不公平,重男轻女到这个田地?
腰很酸。少年时代的她常挨父亲的扁担,有一扁担落在腰眼上,当时她疼得瘫倒在地上,父亲却不管不顾地扬长而去。落下病根了,这腰如今就是晴雨表,天气一变化,腰就先疼上了。
郑鹂歌说,你们的床也太软了,腰不得劲。聪慧的招弟说,郑镇长你覆过身去,我给你推推腰背。
她想起家里的床,那是顶级的世界名牌,漂亮舒适得让所有到过她家的人艳羡。可是她厌恶那张床,在那张床上,她有着太多的屈辱和痛楚,那屈辱和痛楚还得烂在肚子里,不得与外人道也。谁能想到,美丽、健康,看起来风风光光的她,这辈子竟没有享受过床笫之欢!
她上小学六年级时,母亲就去世了,孤苦伶仃的她常对陌生人说,我是孤儿。其实她的父亲现在还活得好好的,而且一如既往地风流潇洒着。自她记事起,在供销社工作的父亲就骂她“小牝子”,非要母亲生个“站着撒尿”的不可。可是母亲的心脏不行,医生说再妊娠就会要她的命。父亲就对母亲说:既然你的心脏这么脆弱,那就得让贤。当时父亲正心有旁骛,那个心脏坚强的女人就是邻村的寡妇金桂枝,金桂枝的男人靠走私香烟捞到了第一桶金,可那个男人也在最后一次接货时失足海水淹死了。
母亲抵死不离婚。可是父亲却跟金寡妇生出了男孩。在母亲垂危的日子里,病床旁只有小鹂歌一人。鹂歌对着奄奄一息的母亲发誓,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活得比那个野种弟弟好,让天下所有的男人都不敢小觑她……
手机响了。招弟把她的坤包递到她手中。鹂歌掏出手机,“呼延刚”三字跳将出来。呼延刚是乐川市主管干部的头儿,铁腕人物。而乐川市的干部最近要大洗牌,现在正是非常敏感时期。“小郑你在干嘛呢?到我家坐坐吧,有要事告诉你。”呼延的语调相当暧昧,这跟他在台上做报告时判若两人。鹂歌想,他指的肯定是干部换班的事。呼延继续说,她旅游去了,我挺孤单的,你来吧!
可是鹂歌讨厌这样的邀请。有一回她去过呼延家,刚一进门,呼延就把她搂住了。她当时真为难死了,动怒吧,得罪不起;忍了吧,人家会得寸进尺。她只能是挣扎着,轻轻地说这样不好不好……幸好呼延的手机响了,鹂歌趁他接电话的刹那,抽身跑了。
可在这关键此刻,鹂歌不能太冷落人。于是强打起精神,换了副脆生生的声调问,什么要事,领导大人?呼延说,你来了说。鹂歌说,电话里不能说吗?呼延说,不能,只能面对你漂亮的脸蛋,我才……鹂歌忽然想起一句老话: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于是说,对不起,我下乡呢。呼延说,下什么乡,别骗我。鹂歌说,骗谁也不敢骗你啊,苍山两个村为水源又干仗了,弄刀弄杖的,很吓人。鹂歌想,呼延是应该知道苍山械斗的,但他不知道她此刻在没在苍山回没回家;当然他也不便打电话去落实一位女镇长的行踪。但呼延显然不高兴了,说,约见你比约见省长还难啊!鹂歌赶忙撒娇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械斗如果出了人命,你又该打我的屁股了!呼延说,你那个屁股,可是我打得的?鹂歌笑了,忙说,您老可别生气哟,待明儿我到你办公室,你爱骂就骂爱打就打……对方没等她说完,啪的一声把手机关了。
鹂歌想,不好,我又把呼延给得罪了。呼延工作挺有魄力,也没听说他有贪的行为,就是有点色。鹂歌想,十个男人九个花。和呼延这样的上司,调调情可以,但决不上床,这是她给自己定的做人底线。女人不能糟践自己,再说自己够聪明够优秀的了,只有蠢女人才靠和上司睡觉往上爬的!
放下了电话,招弟已经在给她做眼部护理了,招弟的两个拇指压住她的眉头,然后分别向两边的眉梢行走。鹂歌轻轻地叹了口气。快乐的人易长鱼尾纹,而她的眉心却长出了一根细细的“悬针”。工作忙,压力重,晚上她不易入睡,睡着了又容易惊醒。
电话又响了,是女儿萌萌。女儿说学校后天有一场演讲比赛,她想争那个第一,问妈妈几点能到家,她要先讲给妈妈听,还请妈妈给予“振聋发聩”的指导。萌萌这方面很像她,伶牙俐齿,敢说敢做。萌萌还要妈陪她买套漂亮的裙装做演讲服。
现在的孩子真幸福啊,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