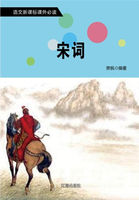“南郡秭归王嫱——”太监呼喊。王嫱应声到前,太监向她伸出手,王嫱愣了一会儿神,想起父亲的交代,再看这太监理所当然的样子,想必他也向别人伸手了,都一视同仁了。
“姑娘,你天生丽质,我自先唤你进去给画师画像,别等后面画得烦了随便一勾那可就耽误姑娘了。”
“谢谢公公。”王嫱从袖子里掏出银子放于他手中,他垫垫分量还不赖,满意地又道:“王嫱姑娘,我是王桂,姑娘日后得了皇上的宠爱可别忘了小奴。”
王桂也是见多了宫里事情的,想这王嫱生得如此貌美,必然能得皇恩的,先招呼好了,日后好沾点光。
王嫱微微屈身施礼,谢过王桂。王桂一路引领着她走到画师房间,才退了下去。
王嫱抬头一看,画架前站着的男子就是刚刚还在想的人。他见了王嫱也似熟人一般,微微颔首,眼角有笑。
“南郡秭归王嫱见过画师。”
“在下毛延寿,宫廷画师,专在此为你们描摹玉容,呈献给皇上,皇上看了喜欢的才召去见见。”毛延寿围着王嫱打转,颇有不敬之色。王嫱心中不悦,但想他手握一支笔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大权,也只得赔笑道:“有劳画师了。”
“王嫱姑娘可惜了。”毛延寿握笔不画,看着王嫱若有所思。
王嫱闻言一怔,不知他是何意思。
引路太监都要收受贿赂,难道他也要打点?王嫱心中疑虑,但看他一介风流,也不似那般贪财之人,只是这宫廷之中谁又敢保证呢?
王嫱微微露出自己携带的银两,毛延寿却只瞄了瞄,眼里似有不满之意,却道:“王嫱姑娘如此急切想入宫承受恩泽?”
王嫱微微屈身施礼道:“有劳了。”
“钱少了。”
王嫱又是一怔,再看那毛延寿,似有怨意。
“我家并不宽裕,这都还是变卖家产才凑的……”王嫱内心悲愤,但也无可奈何。
“既是如此,为何不安分等待自己的姻缘?何必和三千后宫争一个男人的恩宠?”
“你不过一介画师,尽忠职守就是,为何僭越本分说三道四,你不怕我在皇上面前……”
“你没有机会。”毛延寿冷冷打断王嫱的话。
“你……”王嫱想不到小小一个画师居然嫌贿赂太少而公然冒犯,想这宫廷之中也是想象不到的黑暗。
“我人在这,你爱怎么画就怎么画。”王嫱悲愤无奈,端坐一旁,怒道。
毛延寿似乎也生气了,冷着一张脸,根本不看她,却画得似胸有成竹。王嫱见了他这样的作为,想自己必然被画得随意了,此番也再不能见到圣上,自己辜负父亲的一番苦心了。王嫱心有戚戚然,却不愿意在这等小人面前显露出来,只是坚毅着一张脸,看着毛延寿把画笔一丢,道:“好了。请回吧。”
王嫱坐着不动,父亲的期望和自己的愿望跟尊严比起来,哪个重要?求他吧!求他把她画得美一点——不,只要画得是本人的模样就够了!虽然自尊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可是要丢弃它却显得异常艰难。
求他吗?
毛延寿对自己的画作似乎很满意,没有理会王嫱此刻的复杂心情。
“姑娘请回吧!还有很多人等候,我没有时间耗费。”
王嫱最终还是拉不下脸来,这个男人,生得了一副好皮囊,却包裹了一颗肮脏的心,在宫廷里如何生存,他已经给她上了第一课。
王嫱果然没有等来皇上的召见,她被安排进了掖庭做了浆洗宫女。王襄也在失望中黯然离开京城回去自己的家乡。王嫱怀着愤懑低头洗衣,沉默不语。在这掖庭宫,也有不少容貌姣好的女子,不务正业,整日对着镜子梳妆打扮,似乎还不死心。王嫱虽然不甘心在这里做个洗衣服的宫女,可除此又有什么可以打发这百无聊赖的生活呢?
一日王桂来掖庭巡视一番,大谈那个新晋的妃子得了皇上得赏赐,那个娘娘怀了龙胎得了封号,众宫女围着他,似乎从他的话语里能分得一滴润泽,好浇灌自己枯萎的人生。王嫱瞅得机会,问王桂:“王公公,王嫱的容貌在宫里是几等?”
王桂哈哈一笑道:“王姑娘,你容貌是一等,可惜朝里宫里都无靠山,又得罪画师,所以无缘面圣,我也就实话实说啊哈!”
“如此说来,我王嫱此生是被一个小小的画师耽误了!”
“这都是命,姑娘,你认命吧!”王桂也不和她多说,大摇大摆离去了。
“哈哈,真傻!你一个刚入宫的,也太没有自知之明了吧!这宫里小小宫女太监都是得罪不得的,不要说是画师了。皇上喜欢画,特别喜欢欣赏画像里的女子姿态,宫里的画师都是那些嫔妃们巴结的对象,好让画师把自己画出风情来,得到皇上的恩宠。却没见有人敢得罪画师的,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宫女嘲笑王嫱,王嫱听了也只有咬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