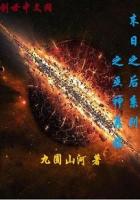烈日当头,空气里一丝风也没有,人走路上就像油锅煎蛋一般苦闷。
“张春花,我操你大爷。”
一声怒吼震破九重天,青冈村老井前的几颗摧枯拉朽的柳树簌簌的掉了许多叶子下来。
从青冈村的那不算太蓝的半空望下去,村外地里束着一堆一堆暗黄色的草垛,这些去年收割的稻草垛子用处很多,除了给骡马当下脚料,各家各户的木床里也都垫着厚厚的一层,就连张春花住的草庐也是用这东西盖成的。
一个满头杂草,衣衫破旧的小村姑坐在其中一个草垛上扬着脖子不知道在想什么。
“**雨,春暖什么的也比春花强呀,怎么偏偏叫这么土鳖的名字。”小村姑嘴里胡乱嘟囔着。
只见那村姑从草垛上跳下来,分明是个十六七岁的豆蔻少女,蓬头垢面的,身材瘦小,唯独一双灵动的凤眼比较醒目。
小村姑拍拍屁股上的灰,伸手扯掉满身的稻草杆子,慎重的穿好一双已经破了几个洞的旧布鞋。
想她张滴滴,行医治病救人无数,规规矩矩做人,从小到大犯过最大的错就是偷了隔壁二婶家的鸡蛋,生吃了下去。
当她好不容易熬出头了,刚得到了外科圣手的医学称号,结果竟然被一道响雷劈中,莫名其妙的穿越在了一个倒霉催的村姑身上。
这不,她刚从草垛里爬出来,仔细检查了原主的身体,就发现手臂上有一些绳子的勒痕和一些棍棒敲打的痕迹,很显然原主是为了躲一些人才钻进草垛里的,结果却不知道是饿死的还是病死了。
山坳里传来一阵鞭炮声,接着是欢天喜地的锣鼓声。
田埂上飞快的跑过来几个七八岁的孩子,看见了站在草垛前站着的张春花,就停下来围在一起嘀嘀咕咕的说什么。
为首稍大一点的胖小子从田埂上跳到地里,捡起一方土块儿在胖手里颠了颠,撑着腰歪着脖子睨着眼前直愣愣看着他的傻村姑。
“喂,张春花,你爷要给你娶一个后奶奶,你不去吃酒席么?”胖小子明显带着嘲笑。
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张员外家里殷实富裕,又是几代单传,到了张春花这一辈,结果是个从小脑子里多根筋的。
所以张春花不到八岁的时候,张员外就让儿子在后山的竹林搭建了一个草庐,把‘疯癫’孙女丢进去,任其自生自灭。
“我去不去关你屁事啊。”
张滴滴本来心情很不好,既然有人送上门来让她出气,那她也就不客气了。
胖小子咧嘴一笑,飞速的将手里的土块朝张春花扔过去,然后拔腿就跑,其他看戏的一群孩子也跟着跑。
张滴滴闪身躲开了直击面门的土块,阴沉着脸,咬咬牙,既然有酒席那就去看看呗,反正也饿了。
张滴滴慢条斯理的朝着热闹的村子走去,路过村口的古井时停下来洗了把脸,稍微整理了一下,俏生生的小女,明眸善睐,清秀可人。
张滴滴刚一转身,一满脸褶子,面色蜡黄的老妇人把脸贴了过来,吓得谢滴滴差点失足掉到井里。
“春花啊,真的是你,我的乖孙女儿,你可回来了。”老妇人一把搂过张春花哭哭啼啼的抹着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