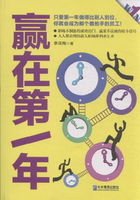这不是他头一次来凶案现场,9年前从警校毕业后,顺理成章的进入刑侦队做了刑警,九年下来,大大小小的凶案现场见了不少,九年下来,也破过不少大案要案,九年下来,他依旧觉得这个工作是不适合他的。
走进凶案发生的房间起皱着的眉头就不曾舒展,不是因为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和淡淡的尸臭,也不是因为看见了尸体脸上似哭似笑的奇怪表情,而是这里太乱了。桌面随意堆放的杂志,满是烟蒂的烟灰缸,散落在沙发上的衣服和丝袜以及不知道躺在洗碗池里多少天的满是油渍的碗碟,有轻微洁癖的他,是不能忍受这一切的。不过让人奇怪的是他很喜欢尸体,喜欢嗅着血的味道和死去的肉的味道。这个秘密从第一次打架时闻到自己鼻腔里涌出的血液时他就知道,也从记事起第一次摸到母亲搁在砧板上的牛犊死去的残躯时他就知道,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因为理智告诉过他这很奇怪。有时候真的很羡慕那些法医们,也许那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吧,正在带手套的他如是的想。
他四处逛了一圈,除了脏乱,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地方,最后来到尸体面前。这是一具奇怪的尸体,跪在地上,全身唯一的伤口是胸前那颗透体而过的长钉,双手也被交叉着定在胸前,光看姿势只觉得是一位虔诚的信徒,在对他的神,述说着自己的罪过,祈祷他的原谅。脸上的表情十分诡异,像哭又像笑,嘴角咧着夸张的弧度,低垂的眉眼和浑浊的眼球又如同在放声大哭。这是第五具这样奇怪的尸体,其他的四个散布全市区,各个年龄和阶层,妇女、青年、老人。只是第五个出现在了这里,在他生活的城市,这个青年女子应该和其他四个人一样,致命的不是胸前刻着奇怪花纹的长钉,而是骤停的心脏。
他蹲着尸体面前轻声的问:“你们啊,到底是在对谁祈祷呢?那时又是谁站在你们面前?”他站起来在尸体周围踱步,走到这个跪伏的男子身后,也不介意破坏整个现场最有价值也是最没价值的物证,贴着这具不再温暖的躯体,感受着冰冷的温度,望着她眼前的虚无,如在情人耳边呢喃着:“你说啊,到底是谁呢?”
看完现场的他回到队里,走向那张干净整洁的办公桌。把之前四人的资料从厚重的文件中抽出。“林队,这是这次受害者的基本资料。”一个年轻的女干警羞涩的把刚刚打印的资料放在桌上,他笑着回了一句谢谢,这个男人一直这么干净和自信,让女孩看到他第一眼就觉得很亲近,这是她第一次对男人有这种奇怪的感觉,放下资料后也不离开只是静静地在他身后站着,偷偷嗅着他身上温暖的味道。
林队拿起资料仔细的对比着,“除了杀人手法以外,还是没有什么共同点啊。”他疲惫的揉着太阳穴,这个几个诡异的案件媒体们可都是很感兴趣的,虽然被局里用强硬的手段暂时压了下来,毕竟不是长久之计,那堆嚷嚷着知情权的记者可不是这么好对付的,最近的压力可是不小,睡眠质量倒是越来越好了,似乎是感觉到身后那不同寻常的注视,他回过头问,“你还有什么事么?”脸上依旧带着温暖的微笑,这是他的习惯。“没事,我没什么事。”女孩估计也发现自己的失态,带着羞红的脸快步回到自己的桌前坐下,坐下前还不忘偷偷的看两眼他的转回去的背影。
时钟在不知不觉间快转到了晚上八点的位置,桌前的男子抬起埋在卷宗里的头,吃力的转动两下有些僵硬的脖子,听着骨节间发出的咯哒声。剩下的东西拿回去吧,最近可是越来越容易犯困了,是自己老了么?林队想到这也失笑着摇了摇头。把几分资料和笔记放入提包,又把桌子收拾得如同往常一样井然有序后站起身,摆好椅子,拎着棕色的皮包来到车里。熟练的打着火,伴着霓虹和路灯往家里开去。
城市的夜晚从不缺少霓虹闪烁的灯光和肮脏昏暗的小巷,带来静谧月光和更疯的疯狂,这些都属于黑夜。林队自小都不喜欢太嘈杂的地方,他一向更喜欢安静,也许和自小就一个人生活有关,从来不知道父母是谁,家人有哪些,曾经很好奇,可是又有什么是时间磨不碎的呢,他把这些都埋在心底,现在只想破掉这个案子,再请一个长假,去各地走一走。
打开房间的灯,随意的煮好一碗牛奶燕麦,端着还在冒着热气的碗坐到桌前,他不讨厌这种简单的食物,反而很喜欢,有时还会加一些果仁或者巧克力碎,有时又加一些玉米片或者就上一些饼干,总能有些意外的惊喜。待燕麦冷了些随手挤入一点蜂蜜搅和了一下,就着卷宗就吃起来。
他被闹钟吵醒,幽幽的按掉闹钟,又看了眼时间,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六点,桌上放着翻开的资料,还有半碗冷掉的拌好蜂蜜的牛奶燕麦,他皱着眉,很不喜欢这样,浪费了粮食,凝固在碗沿的牛奶燕麦很难洗干净,而且昨晚也没洗澡。也不知是几点睡着的,他坐着伸了个懒腰。把隔夜的吃食端到厨房,倒入下水道,又仔细的洗干净碗,擦干放到碗架上。从橱柜拿出砂锅放上米和水,又放上一点鲜肉末,准备熬一锅粥。作完这些他才打着哈欠拎上干净的衣服走入浴室,始终回想不起是什么时候睡着的,端着的碗还好没有打翻到卷宗上,要是那样的话可就太邋遢了。洗完出来,昨天的衣服还在洗衣机里轰隆隆的旋转着,走到厨房看了看砂锅里翻滚的白色粘稠粥汤,从冰箱拿出一个皮蛋用线小心的切碎丢到锅里。
警局里还是一样的忙碌,还是一样的难题。验尸报告如出一辙,致命的不是胸前的贯穿伤,而是骤停的心脏。尸体和铁钉上没有任何指纹,铁钉趁人活着的时候穿过的胸膛,可是为什么伤口上没有明显的撕裂痕迹?受害者为什么不挣扎?
谜题越积越多,迷雾越拨越浓。
中午吃过午饭趁着休息,林队走到街上想透透气,离开办公室晃眼的灯光,正午的阳光还是挺毒辣的,他并不在乎,信步在街上走着。不知道走了多久,直到觉得天空阴暗下来,哗哗的下起雨,他闪身躲到附近的雨棚下,身上依旧没有雨点,路上稀拉的行人也都对这场雨熟视无睹,林队皱着眉头思索着,为什么只有我看见了这场雨?
正在大脑中飞速的运算着一切不可能的可能,一名陌生男子提着外带披萨盒,从大家都看不见的雨中,冲到同一个雨棚下。习惯性的想要拂掉水珠却愣在半空中的手,不可置信的望向大街的双眼,虽然看起来很呆,不过他应该是看得见这场雨的。林队难得的先开口搭讪道:“你也是在躲雨么?是啊,他们好像都看不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