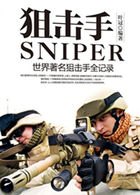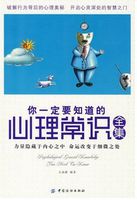1938年8月,胡老板突然给我发来一封电报,随后还有一封航空信,一方面对头一年在上海遣散同仁(包括我在内)的事,深表歉疚,说那是动乱中的失计。表示今后无论遇到任何困难,绝不再轻易散摊子了。不管这是一种姿态还是一番诚意,这样自我谴责的态度总是感人的。接着他又谈到在香港办《大公报》的用意和决心。强调那是抗战宣传的前哨,要我务必火速来港,共图大计。紧接着,自然就电汇来旅费。
困居昆明的那几个月,是我入世以来最苦闷的一段日子。我太好动了,不适宜编教科书。从1935年当上报人马不停蹄热闹了几年,突然,生活变得那么冷清闲散。“小树叶”至少还在上着学,我则像只断了线的风筝。尤其想到昔日许多朋友都各有作为,我这个奥勃洛莫夫却恰似一条惯走江湖的小货轮搁了浅。送走好友曹维廉去新四军之后,“小树叶”同我一道认真商量过去延安的问题。有人吓唬我们说,一路关卡多着哪。一旦被扣下,就得蹲集中营,上老虎凳,灌肥皂水。毋庸讳言,现在回想那时,自己不折不扣是个懦夫。喊了几年“大时代”,及至大时代真地到来时,我却无所作为了。
那几个月,失眠、忧郁、苦闷,百无聊赖地在翠湖边上转悠。有一天走过威远街一家西药店,看到一瓶专治闷郁症的药,我赶忙买了回来。吃了几粒之后才从处方上发现:那原是专治妇女月经症的!
胡老板的电报就是在我处于那样黑色心情之际到达的。我的亢奋曾使得“小树叶”很有些不悦。然而我掩饰不了当时的亢奋。
几天后,我就找到一位同伴——施蛰存。我们一道经安南去香港(那时往来昆明的捷径是走安南和香港,如去西藏得走印度!)。
仅仅从昆明到安南的海防就要走三天。火车是昼行夜停,旅客要下车住客栈。头两天是在昆明境内走。晚上歇在开远,第二天到滇(河口)越(老街)边境。谁料到还没过境,就来了场虚惊。
我有个职业习惯:喜在旅途中记些笔记。快到边界我正一边望着窗外景物一边往摊在台子上的小本本写着什么的时候,突然被人从后面拦腰一抱。本子登时给夺去,我被看管了。这时同行的施兄也吓傻了。火车开到河口,我立即被押到边界哨站去。幸而施兄也跟了来,经过反复盘询和检查,又摇了一通电话,才弄清我的良民身份。
然后到了老街——法殖民者的天下。海关检查员像刚喝了一肚子烈性酒:脾气暴戾,把箱子里的东西翻腾得乱七八糟。幸而老友周承周刚巧在那里的交通银行支行工作,承他照拂,总算平安抵达海防。
接着还有三天海路!
一走进皇后大道中的报馆编辑部,就又看到老同事了,真是恍如隔世啊。
走在香港马路上,感觉也十分异样。一年前,我同“小树叶”路过香港时,境遇和心情有点像丧家之犬。如今,有了职业,就会恢复了自信,精神面貌大为改观。马路上遇到熟人,又可以报一下自己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了。失业者与有职业的,在自尊上悬殊多大啊。更重要的是:尽管我没去敌后或延安,毕竟又站到抗日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岗位上了。我决心把《大公报·文艺》办好,让它依旧在文化阵线上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干的还是老行当:编《文艺》并负责一个娱乐性副刊,如有余力,就往内地跑跑。
重整旗鼓第一步是同敌后游击区的、延安的、上海孤岛的朋友们联系上。需要写上不是几十封、而是几百封信。同时,根据1938年的客观环境,重新设计副刊。
写至此,正愁手头没有香港《大公报》可供参考时,有朋友为我寄来两篇文章。一篇是1987年6月出版的《当代农民》杂志上刊登的《延安文学在香港〈大公报〉》,作者是穆紫。另一篇是《香港文学》于1986年所刊《萧乾·〈大公报·文艺〉与〈清算日本〉》一文,作者是杨玉峰。此二文概述了1938年我抵港后在副刊方面所做的主要工作。
根据穆紫所列的篇名,包括杨刚接编的时期在内,《大公报》这个刊物在三个年头内,竟然发表了一百一十八篇来自延安的文章,其中陈毅的《最近的山西》连载了三期,刘白羽的《蓝河上》连载了十六期,何其芳的《夜歌》连载了四期,沙汀的《抗战期中的“日后”文艺》连载了五期。如果加上来自各战区的文章,说《大公报·文艺》曾为抗战作品提供过重要园地,该不是溢美之辞。
杨玉峰在《萧乾·〈大公报·文艺〉与〈清算日本〉》一文中写道:“《大公报》的宗旨是希望替民族解放事业作一点贡献;说得直接些,就是作为宣传抗战的媒介。由萧乾主编的《小公园》和《文艺》两个副刊,目的自然与报章宗旨步调一致的。”
此文介绍的是1939年3月出版的一本《清算日本》(《大公报》出版部发行),内收原登在《文艺》上的四十三篇从各方面揭露日本的文章。作者慨叹这本书未能引起大家的重视,并说:“就连编者本人恐怕也毫无印象了。”他的推断准确得很,我早已把这本书忘得干干净净。从文中所附那本书封面的照片看,那是“综合文艺丛刊”第一种。也不知道杨刚后来有没有再编下去。
《文艺》是在1938年8月13日出刊的。第一期,少不得要向读者交代一下大政方针。我申明:“《文艺》过去从不登萎糜文章。现在仅仅那样就不够了,我们要把文章变成信念和力量。”在同一文中,我表示希望保持刊物固有的全面推动文艺的做法,提出不必局限于战争题材,因为对整个抗战来说,后方也是同样重要的。为此,《文艺》曾出过《我们的大后方》及《不打仗的作家们干什么》等特辑。
这段时期,《文艺》还是登了不少有分量的作品,如陆蠡的《囚绿记》、李辉英的《小山岗上》、芦焚的《夜哨》、杨刚的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艾芜的《退到后方的人》、老舍的长诗《成渝路上》、巴金的《在轰炸中过日子》、落华生的独幕剧《女国士》、沈从文的中篇连载《湘西》、杨朔从西南寄来的《跳动在历史过程中》以及茅盾的《追记一页》。
在上海时《文艺》曾特别提倡过写书评,到了香港,这一方针也并未放弃。刊物评介了茅盾主编的《文艺天地》、史沫特莱的《打回老家去》,以及木刻家陈烟桥主编的《自由》,并举行了《文章下乡》的讨论,还刊载了中央大学对《阿Q正传》的讨论。
刊物原有《文艺新闻》一栏。在新形势下,此栏更能在作家间起沟通声息的作用了。除特辟《战地书简》及《作家行踪》二栏外,也报道了大后方的文艺动态,如《桂林剧坛》。《文艺》最早通过严文井一长信报道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情况,自然,关于上海孤岛,也经常有杨刚的报道。
在新形势下,《文艺》增添并突出了两个特点。一是编起了一个“综合版”,实际上就是为了尽最大努力加强自身对抗战的信念并揭露敌人,打破了纯文艺框框。在这一版上,凡能鼓舞我方士气的,不论是军事、政治还是经济问题,都可以谈。另一个特点就是大力加强了刊物的国际性。既然是同一场反法西斯战争,我们欢迎国际友人的声援,同时,我们也支持他们的斗争。
“综合版”的首要任务就是揭露日本本国的黑暗和虚弱。刊登了关于日本财政的专论,以及《狐狸精附了体——战时日本童工的剪影》(下村千秋作,高行译,1939年3月11日)、《死亡线上战栗着的日本大学生》(1939年4月1日)、《日本肥料缺乏》(1939年4月15日)等文,并报道了日本民众的反战运动。还转载过日本漫画家佐宗美邦的反战漫画。1939年初曾系统地发过几篇分析“日本这一年”的文章,同时综述了“一年来的汉奸活动”以及“日本在华北华中的经济侵略”,特别着重揭露了“日制大亚细亚主义”。自然,正面报道也有,如关于“中国工业合作化运动”的介绍。
国际方面,在平日版上发表了一些支援我国抗战的国际友人的作品,如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的《暗夜的事件》、美国朋友史沫特莱的长篇连载《八路军随征记》,以及日本反战作家村野四郎的《一九三八年的田园诗》。在“综合版”上,我们撰文祝贺过美国作家辛克莱的六十寿辰,介绍过黑人作家休斯的文学活动,刊登过丘吉尔的《论萧伯纳》,回顾过西班牙战争。另外,还刊登过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访问记。美国朋友F.Gibbon的《在中国空军队伍中》曾颇引起注意。在一篇巴黎通讯里,作者正面质问:“纪德能这样糊涂吗?”文中引用纪德一段话说:“中国与日本正如法国与德国,是种下了宿命的根。”他认为两国之间有着一道“超越理智的大鸿沟”。
到香港后,稿源很充足。娱乐性的刊物虽归我负责,但另有李驰在实际编。这样我又可以出去写旅行通讯了。
这时另外有个促使我千方百计抓机会离开香港的因素:我的婚姻触了礁,而责任全然在我。
我到一位原在北大任教的瑞士人家里去学法文,在那里,遇上了他的干女儿、钢琴家雪妮——一位从性格、容貌到艺术趣味都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姑娘。我立即意识到这里隐伏着的危机。为了我自己,也为了“小树叶”,我赶忙离开香港,逃往岭南。我陪老友黄浩由汕头出发,经潮安、普宁一直到梅县边上。一路他为华北游击队到处募捐,我则四出采访,写了五篇重庆登不出的通讯。我是想在踏访岭东农村的过程中,把雪妮忘掉。
回到香港后,我发现自己失败了。于是,我赶忙编出一批稿子,在老板的首肯下。又照原路回了昆明,想一面采访滇缅路,一面加固同我从没有过半次口角的“小树叶”之间的纽带。
从昆明到大理、龙陵、芒市,自畹町到缅甸的拉戍,我仆仆风尘地在工地上奔走着,采访着,工作着,衷心巴望能把雪妮抛到脑后。回到昆明,我发现并没成功。返回香港后,恰好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来函要我去教书。这下,我索性离开香港,永远地离开了雪妮,投身到另一场战火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