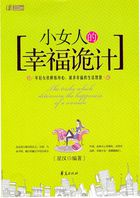蜀中奉节,秦驷两鬓微霜,白衫如雪,手把折扇慢摇道:“尊驾,还念着王瑞么?”“某,四代受平西郡王大恩,只恨文质之身,不能杀贼复仇。”“老人家,秦驷此来就是查这蜀中叛乱之事,我王明旨,于老先生,蜀中文人楷模,蜀中已归唐土日久,问你现在的蜀中和曾经的蜀中,有何区别?”“弄权老贼,愚民而已!昔我王公治蜀,兵强马壮,百姓威服,可惜中这老奸贼之计,哎!”“于老先生,上路吧!”“去往何处?”“九幽森罗。”“哦!是三尺绫,还是?”“磔刑。”“何为磔?”“上古人氏,无刀斧兵刃,祭祀上苍时,使大石断牲畜手足,头颅,以祭天地。后犯大罪者,具表天下不足以正视听,只有以磔刑处之,明告天地。”“秦大人,老夫我虽死不悔,只是有一事望大人帮我。”
于府之中,秦鞅一袭官服,满目淡然,开言道:“王老将军,想什么呢?”子义一旁束发持盔,叹道:“当年我尚在蜀时,于翁与我有些私交,眼见今日景象心中有些不忍。”“将军,向来恩怨分明,只是这事心软不得。”“仲阳啊!你我相识数十载,有些话我到不瞒你,明日行刑我就不去了,我晚间就回CD见先生复命。”“将军,仁厚不去也好。只是一点将军允我。”“何事?”“早上大哥送进将军大帐的孩子,还望将军给我留下。”子义,闻言怒道:“当年天策府拜将之时,先生许我不做违背道义之事,如今于氏满门即将死绝,就留下个十七岁的娃娃,仲阳也不放过?”“王子义,法治之道,不避亲贵,不避老幼,你这是人治。”“我王子义,只会治军不会治人,军令如山我必不可违,但是你那法令我王子义,不会认同。”“如无法治,何来这中兴之景,十贤立像。”“若是一本律例就能中兴,要我玄甲军,天策府何用?要先生何用?你还是再说先生也是人治么?”“府令依法治人,岂是人治?”“那我王子义,把人犯押回,送与先生处置,又有那点违法?”“奉节于氏反叛一案,由我与秦驷亲审,何劳将军辛苦?”“伯阳让我将犯人带回,又有何处不妥?”“罢了,罢了,王子义我服你了,回去别顶撞先生。”“先生和你不一样,你这法家恶徒,不讲情面,我回了,你小心办案。”“嗯!回去我在登门骂你。”“摆下酒宴,恭迎仲阳上门叫骂。”“嗯!一路平乱辛苦,回去好好休息休息,以后多让武孝替你分担分担。”“老将虽老,不用儿子上阵。”“你啊!我已经递了请辞文书,准备回家养老了。”“你是得罪的人太多,准备多活几年吧!”“是啊!是啊!”“回天策府了再说,走了。”言讫子义出府上马,直奔大营而去。
CD平西郡王府,奉先手把子义,来至一客房之前,开言道:“子义,你看先生当年,就是在此门前王严拿来,绿衣纁裳,鱼符冠带,出任军前参议的,再看先生如今两鬓霜降,不得感慨啊!”“谁说不是?先生,你看我这须发也是白了不少,这一转眼几十年都过来了。”“子义啊!早间君羡有书信送来,明年禀政之时他和颖儿一起回来。”子义闻言笑道:“先生,他们没说回来住几日?”“这倒是没有,只说岭南如今风貌,物产,人口远胜往昔。说过几日荔枝也就到了。”“孩子们有心,先生的福分啊!”“哈哈!好像不是你姑娘一样?”“嫁出去了,不想她,不想她。”“子义啊!你知道你那句话先生最受用么?”“末将不知。”“就是那一句句的,末将领命啊!”“先生,这是末将本分啊!”“是啊!是本分,但是别人说,先生未曾当真,但是只要子义说,先生只用准备庆功宴就是。”“先生,谬赞了,玄甲军本就是替先生分忧的。”奉先此时,慢走几步到院中石桌道:“子义,坐下说,坐下说。”子义入座,奉先一捋长须道:“子义,人生如路,你我将帅已然走了很多年,我懂你,你也了解先生。子义,你给先生说句实话,朱氏一族灭门了么?”子义,闻言半晌无语,起身叹道:“先生,看见的都死了,还有一个一听哭声就是孩子,末将放了他,请先生治罪。”奉先连道:“不必如此,不必如此。你天性良善,凌强扶弱,先生岂会怪你!只是你那义子,欠思量啊!”“战时孤儿,能救一个是一个。”“嗯!前天你又发了恻隐。”“这秦鞅。”“别怪人家,你自己说的押回来交我发落的,现在人呢?”“先生,子义错了,罚我一人就是,无关人家孩子。”“谁说要罚?”“不罚那是?”“秦驷,来信说:于翁,有一独孙名曰子了,善音律,通歌舞,填词作曲皆是一流。且生的如玉一般,留下当个乐伶,足慰平生。”“先生,伶官误国啊!”奉先笑道:“李存勖,哪里呢?”“我看也快了。”“倒是有眼力,不过先生难受啊!”“这这这却是为何?”“李存勖天纵英雄,因为一些伶人你看看,朝野上下乌烟瘴气,传闻伶人敬新磨,当着百官一巴掌打他脸上了,哎!明主庸主都是他。”“那先生还要将于家小子,用作乐伶。”“先生,觉得梨园,左右教坊闲着也是闲着,太常寺的雅乐听的烦了,祭祀时听听也就罢了,每每宴饮也是雅乐,歌功颂德不舒服。封他个编辑官领乐营将,让他没事排排演演也好。”“末将领命。”
只见明月之下,一人抚琴,高歌道:“梅花凋,身似落花自在飘。军士笑,叹我残生无良宵。宁虚山上苍髯寇,老贼无德庙堂高。”“好好好好好,老贼无德庙堂高,唱的好。”“先生,莫要动怒。”“子义,多心先生不曾动怒。”言讫,奉先急步过去,那人一惊怒道:“老贼杀我全家,我与你不共戴天。”言罢持琴便掷,子义一见跃起一拳,琴在奉先面前落下,子义急步上前,一下拉住那人怒道:“按律你也死了,莫要不识好歹。”“那人伏地泣道:”王将军,杀了我吧!我我我我我。“月光一照,却见那人目似梨花春带雨,眉似流波映明月,唇粉齿白,悲泣有色,月下天人,奉先一见淡淡道:”子义,放开吧!一个娃娃,还能伤我。“言罢子义谓其人道:“好自为之!”言讫放开,那人站起,一身白衣,黑发白带,两目红晕更显凄楚,奉先低声道:“娃娃,今天死的是我,你会哭么?”“不会,巴不得,老贼速死。”“孩子倒是个好孩子,就是心术不正。”“老贼就会胡说,我哪里心术不正了?”“我与你爷爷都是人,他要杀了我你不哭,我要杀了他你哭什么?”“那那那,他要杀你我也哭。”“哈哈哈!”“你这老贼,你笑什么?”“笑我自己作恶多端啊!”“你还知道,我爷爷不对,你打他一顿就是了,为什么要杀他?呜呜呜呜呜!你这老贼,你这土匪,你这死豚,你这死犬,我要活着总有一天要杀了你替爷爷报仇。”“你见你爷爷死了么?”“没有,不过他们说你要杀我全家。”“不会,怎么会呢?”言讫子义附耳道:“此时秦鞅恐怕已经行刑。”“先生,知道。”“那你没杀他们,我骂错你了,你可以放我回家了吧?”“可以,放了你。但是你要答应我,回去找不到他们,就来天策府找我。”“嗯!”“有何凭证?”“嗯!这玉萧是我的随身之物,你拿走。”“好。”“但是我要找到他们了,你要把它还我的。”“嗯!你要记得,找不到就回来,我怕你爷爷怕我,躲远了。”“嗯!”“子义,配车一架,纹银百两送于。”“你叫什么?”“于子了,了然的了。”“送于子了回去。”“先生这。”“哎!”“末将领命。”“老头,就算找不到,你也要把玉萧还我哦!”“君子一言。去吧!去吧!”
未过片刻子义回转道:“先生何意?”“支会秦驷,秦鞅,刑场不必打扫,留给那孩子。”言讫拂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