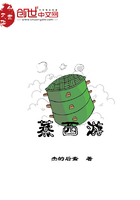民国三九年,大寒。
今年的冬天似乎走得特别的早,远山的积雪还没融化,温暖的风就徐徐吹来,干枯的枝头冒着几片绿芽儿,阳光翻过山岗,正热烈地照耀着滇东北大地。
麦家大宅却在这阳光中显得寂寥。这是一座仿京四合院,建于同治中期,由于融入滇东北居住习俗,要比北京四合院小得多,内设的小桥、流水和花园与大大小小的厢房规整地协调,倒也别致雅静。但四周的房屋建得高,整个冬天,早上的阳光照不进院内,庭院深深,好不寒意。
从南到北,从西到东,被踏陷的小石径证明它曾有过的繁忙和繁华,如今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已不复存在,唯有绿色的大门门楣上镶着的金色阿拉伯文“真主至大”向世人宣示着它的归属。
这是大宅的主人麦城从重庆回来的第二日,晨礼后,他静悄悄来到后院,绕过一片被冬雪拔得松软的草坪,站在院墙角落那棵他为她二十年前栽种的桃树下,站成一座雕像。
干涸的桃枝冒着嫩芽儿,随着漫进院墙的暖风轻轻舞动,勃勃生机,使人不禁想到春天不远了。但他的心却在这春天不远中悬空着,像一块不落地的石头,暗藏杀机,随时让人毙命。
他长长舒了一口气,闭着眼,默默念着古兰经“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全世界的主,至仁至慈的主,报应日的主。我们只崇拜您,只求您祐助,求您引导我们上正路,您所祐助者的路,不是受谴怒者的路,也不是迷误者的路。”
“桃树都长蕾了,花期不远了”大太太菊香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他身后,毕竟出身书香世家,话语都带着墨味,给人咀嚼。
“是啊——”他停住了默念,背着对她,抬头望了一眼蓝得一无所有的天,仿佛院外的太阳是一面多余的镜子,再怎么炽热的照耀,也照不进他悬空的心里。麦家到他手上,几尽人去楼空。
她且不了解他的心。他且不知道她有话要说。
但,彼此沉默。这两个同床共枕了二十年的人,****得只剩下心照不宣。
“老爷,您对那件事还没释怀?”如果不是一阵暖风扑面,菊香绝对不会此时提及绝口不提的往事,她有些后悔,两只手相互揉着,等着他的回答。
这问像抚琴的纤手,拨动麦城身上根根神经,使他悬空的心落了下来,碎成一面幽深的湖,层层波纹永远到不了彼岸。他定了定神,像一块不会风化的石头,把心裹得滴水不漏,转过身:“你是恩师临终前的嘱托,也是我麦城要娶的女人,不管发生什么,都是前定,我绝不抱怨绝不负你。”
他看着她,神情肯定,露出四十岁男人难得的柔情。
她看着他,含情脉脉,露出四十岁女人少有的温柔。
但彼此心里清楚,谁都没有把话说完,只是此情此景,这个麦家强悍的女人变成一只乖顺的羊,把头靠在他的肩膀,像两只落难的鸳鸯,乱世之中十指相扣,谁也舍不得先松开,庭院深深,时光静好。
“老爷,刘副官到访”管家李清不解风情在后面禀报,他脸有些红,心里却酸酸的,麦家经历太多事,很久没见老爷太太如此恩爱的场景了,心里狠狠骂道:“妈的!这****的来得真不是时候!”
“知道了,把他带到客堂,我随后就到”麦城吩咐道,李清低着头,领命退去。
松开手的刹那,菊香拉住了他:“还是我去吧。”他默默点点头,麦家到现在一直是她在撑着,更何况也只有她的精明能读懂那些官场人物的话中话。
两个士兵标本似的矗立在客堂门两端,这让五十米之外的菊香心里泛起小小的波动,现在的天一天一个样,以前只到院外,现在就到家门口了,风云叵测啊。但从做了麦家女主后,长期出入大场面养成的气度,使她加快了脚步。
刘副官正在客堂西墙边,两手插在裤兜里,出神盯着墙上一副麦家祖传的唐伯虎山水字画,一进门菊香就大大方方道:“看不出刘副官还有如此雅兴,难得,难得。”
“麦夫人见笑了,刘某就一粗人,哪懂这些文人的玩意儿,只是到过贵府诸多次,今天不知怎么就被它给迷住了”刘副官对着迎面而来的菊香露出一口洁白的牙,如果不是一身戎装,这笑还算迷人。
“哟——瞧您说的,好像成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刘副官可是出身江南,那是文人之乡啊,这罪麦家可担不起哟”菊香作了一个请坐的手势,一字一句,特意吐得绵而甜。随即吩咐身后唯一的丫鬟梅花:“上茶。”
刘副官坐下,依旧露着一口洁白的牙,道:“喝茶倒不必了,刘某公务缠身,是奉苟司令之命来抓壮丁的,路过贵府,特来拜访,也不知麦少爷近来可好?”
麦少爷这三个字像一颗钉子,定中菊香的要害,她狠狠捏扯着手里的白丝帕,片刻,才抬起梅花送来的青花“白头富贵”图茶盅,轻轻抿了一口后,用白丝帕擦擦嘴角,泛着微笑,字正腔圆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劳刘副官费心了,百忙之中还挂记着犬子,乃是麦家的福气。”说完向身旁的李清使了个眼神。
“瞧您说得见外了不是,谁不知道麦家有两宝,麦少爷可是宝中之宝,我们苟司令也是常常念叨啊,这不特意吩咐我路过贵府,一定拜访,替他问候”刘副官还是露着洁白的牙,好像这牙成了他的招牌,一字一句从牙缝过滤后,多少会有几分亲和力似的。话毕,他也抬起青花“白头富贵”图茶盅,喝茶的瞬间,瞄了一眼菊香。
菊香就像定海神针,笔直坐在黑色檀木靠椅上,“哼哼”笑了几声,道:“我们麦家心里有数,这不对苟司令的挂念深表感谢,麦家特派管家到过苟府,只是我一时疏忽,竟忘了也对刘副官表表感激之情,失礼失礼!”她欠欠身子,做出一个道歉的姿态。
刘副官哈哈大笑,一双大而有神的鹰眼活生生成了一条线缝,道:“跟夫人交道多次,今天才知道,麦家的大太太果真非女流之辈。”起身作了一个告辞的姿势,接过李清包好的唐伯虎字画,满意而去。
等李清送客的身影消失,菊香才深深吐了一口气:“虎落平原啊!”如果不是梅花在她真想好好为自己泪流一场,从进了麦家的大门,她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时刻不得消停。她拉起边为自己捏着肩边低声抽泣的梅花的手,轻轻的揉着,此时此刻就剩这个十五岁就陪她嫁到麦家的人心疼她了。
“小姐,这可是麦家的传家宝,您这么……少爷……他……”梅花一字一字弱下去,像只蜜蜂突然被粘住了双翼。
但菊香心里清楚,梅花说的正是麦城所不能释怀的,是她致命的死穴,一旦搬到阳光下,她将死无葬身之地。可她没有对替她一直保守秘密的梅花训斥,她似乎也没有理由训斥。从跟她那天起,梅花就受着守口如瓶的折磨,而她在梅花面前,心甘情愿做一个透明物,再说欠下的迟早要还,或许她在麦家一直过得不安生,是因为报应。她心平气和般果断吩咐道:“你去把老爷请到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