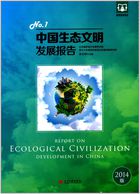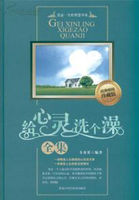况且,在宋辽双方的边境贸易中,银的贸易并不是单向流动的,而是双向的,既有辽向宋的流入,也有宋向辽的流出。例如,宋仁宗庆历五年二月,河东安抚使欧阳修言:“河东地形山险,馈运不通,每岁倾河东一路税赋、和籴、入中、博市斛斗,支往沿边州军。
人户既不能辇致,遂赍金、银、钱就匕界贵籴之。”又如宋神宗熙宁元年十月下诏将奉宸库两千多颗珠子带到河北沿边四榷场出卖或折博银,“其银别作一项封椿,准备买马”。粮食与马均是宋朝北部军备供应的重要项目,宋朝常需向辽朝购买,所费银两亦应占一定比例。但是在长期的边境贸易中,无论对宋还是对辽来说,银只是诸多贸易品种中之一项,既不是大宗贸易品,又无固定贸易额,因此,对榷场交易中银的贸易额不能估计过高。
这里,还需要提一下北宋末期的两条史料,这两条史料是持宋银无甚流失观点的学者籍以证明的依据。一条是宣和四年宋昭论榷场利害的一段话:
臣窃料,议者谓岁赐浩瀚,虚蠹国用,是不知祖宗建立榷场之本意也。盖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取之于虏,而复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也。比年以来,榷场之法寝坏,遂耗内帑。臣愿遴选健吏,讲究榷场利害,使复如祖宗之时,则岁赐之物不足虑也。
另一条则日:
议者谓祖宗虽循契丹岁输五十万之数,然后置榷场与之为市,以我不急,易彼所珍,岁相乘除,所失无几。今悉以物帛价出,榷场之法坏矣。
其实,宋昭等人的议论主要是针对宋与辽之间榷场贸易的得失而言,宋昭“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等语,只不过是指宋岁纳银绢所费可以从榷场盈利中来弥补,并未专指银的回流。因此,这样的材料恐怕难以为据。
总之,除北宋前期一度返流回来的银两较多外,北宋其余大部分时期返回宋境的银两不会很多,岁币银的流失应该是客观存在的。
关于南宋的岁币银流失问题,上面已提到加藤繁的观点,我亦认为尚可商榷。宋金对峙时期,宋朝每年交纳岁币银的数额虽有过三次变动,但最少的时期每年纳银也有二十万两,最多则达到三十万两,直到嘉定七年宋金关系破裂为止,累计纳银一千九百万两以上。更为严重的是,金朝在北宋末期的两次侵略战争中搜刮走巨额金银。据《靖康要录》记载,第一次入侵先后搜刮金达八十万两,银二千四百万两;第二次入侵汴京后,金人索要金一百万锭,银一千万锭,后来又将银减少到五百万锭。从靖康元年十二月到次年二月间,被金朝掳走之金不少于五十七万两,银亦高达二千五百多万两。总之,宋朝在北宋末期的浩劫中,流失金银不计其数,不仅中央府库、帝王宫室多年蓄积之金银被掠夺一空,京畿地区上至百官臣僚下至平民百姓之家亦被搜刮净尽。这次掠夺再加上其后年额二十万两以上的白银年年不断地流入金朝,大大地充实了金朝的府库。南宋嘉定八年(1215年)蒙古军队攻破金朝都城燕京之后,获得金朝府库大量的金银货财。“其所积货财,初无所用,至以银为马槽,金为酒瓮。萨木哈所居至用金饰:晓床,足踏金杌子。”这一记载充分说明金朝政府长期以来积聚了大量的金银财富,其来源绝大部分当出自宋朝。
加藤繁先生认为宋朝因与金进行茶业贸易而得到的巨额银两完全可以弥补其在岁币方面的损失。这一论断的依据仅是一条史料,现照录于下:
(金)宣宗元光二年(1223)三月,省臣以国蹙财竭,奏日:“金币钱谷,世不可一日阙者也。茶本出于宋地,非饮食之急,而自昔商贾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间尝禁止之,后以宋人求和,乃罢。兵兴以来,复举行之,然犯者不少衰,而边民又窥利越境私易,恐因泄军情,或盗贼入境。今河南陕西凡五十余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银二两,是一岁之中,妄费民银三十余万也。奈何以吾有用之费而资敌乎?”
加藤繁又依据矢野仁一博士的考证指出:每郡饮茶日须二十袋,每一袋之值以二两计算,则五十郡一年的饮茶数额当为七十二万两。如果加藤繁先生引用的这条史料可信,毫无疑问,宋朝依据茶叶贸易的收入应是银两入超之国。但是金在与宋之间进行茶业贸易时是否完全以银支付呢?事实并不如此。上述话中有这样两句值得注意:“自昔商贾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间尝禁止之,后以宋人求和,乃罢。”那么,金朝是怎样进行茶业交易的?泰和问又是如何禁止的?《金史·食货志》中有两条史料可以解答这些问题:
(泰和六年十一月)尚书省奏:“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比岁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荼肆相属。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是以有用之物而易无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财弥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不应留者,以斤两立罪赏。
(泰和)八年七月,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国丝绵锦绢有益之物,不可也。国家之盐货出于卤水,岁取不竭,可令易茶。省臣以为所易不广,遂奏令兼以杂物博易。
从上述史料可知,泰和六年(1206)以前,宋与金进行茶业贸易时得到的偿付品主要是丝织品类。泰和六年禁令后,又增加盐等杂物博易宋茶,杂物中估计包括银,但却无数量上的明确记载。另外,金宣宗贞占三年(1215)七月有一条记载:议欲听榷场互市用银,而计数税之。上日:“如此是公使银入外界也”。平章尽忠、权参知政事德升曰:“赏赐之用莫如银,而府库不足以给之。互市虽有禁,而私易者自如。若税之,则敛不及民而用可足”。平章高琪日:“小人敢犯法不行尔,况许之乎!今军未息,而产银之地皆在外界,不禁则公私指日罄矣”。上日:“当熟计之”。
这条材料说明,直到金宣宗贞占三年为止,金政府仍然是实行着榷场禁止用银贸易的政策。可见,在长时期的宋金茶业贸易中,银两从金朝流入宋朝的数额不会很多。只是到了金朝末期,情况才发生变化。那时金朝国内货币制度已面临崩溃,交钞日益贬值,铜钱又限制使用,于是出现“民但以银论价”的现象。上述金宣宗元光二年的材料,就是指这一时期茶业贸易的情况。然而,即使金朝此时有能力年付七十二万两银交易宋茶,到金亡为止的十数年间,所有输出之银也不会超过一千万两。
在南宋与金的榷场贸易活动中,亦出现与北宋时期宋辽榷场贸易类似的情形。即:虽然政府禁止白银出界,但仍存在白银的私下流通现象。如乾道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中书门下言:‘已降指挥,令淮南京西安抚转运司钤束榷场客人,不得已(以)银过淮博易。闻沿边州军全不约束。’诏行下沿边守臣督责巡尉并榷场主管使臣等,严行禁止”。明年三月二日,知扬州王之奇又提到:“准朝旨令措置禁止北界博易银绢。闻泗州榷场广将北绢低价易银。客人以厚利多,于江浙州军贩银,从建康府界东阳过渡至真州,取小路径至盱眙军过河博易,致镇江府街市铺户茶盐客人阙银请纳盐钞茶引等。除已行下淮南沿江州军,将应干私渡取会依条禁止外,有江东西、浙西、湖北州军沿江私渡,亦乞严赐禁止。”为此,宋政府还于淳熙元年十月“立金银出界罪赏”,并在后来的查处工作中予以执行。淳熙十六年三月,宋孝宗下诏将知盱眙军葛搂降两官,其罪名之一就是“透漏银两过河”。同年十一月,盱眙守臣霍篪捕获赵兴等透漏银两甚多,被“特与转一秩”。但是这些材料又说明,宋政府虽然有相关的禁令或赏罚措施,却依然挡不住宋朝银两向境外的流失,而且白银的这种流失是长期存在的。从金朝方面看,也可证实上述推论。金朝官吕鉴曾监息州榷场,当时每场交易“获布数千匹,银数百两”。仅息州榷场与宋朝的一次交易额就达数百两银,由此推算,通过榷场贸易由宋入金的银两数额恐怕不会太少。
总之,在北宋与南宋两个时期内,宋朝由于向辽、金输纳岁币银而又不能通过榷场贸易回收足够的银两,故宋朝白银的流失数目不可低估。在这种情况下,对白银的需求无疑促进了宋朝银矿生产的持续开发。
宋代金银矿业得以迅速发展,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政府采取的促进生产的政策、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的货币化及流通范围的日益广泛等等。这些问题学者们已多有论述,故本章只是探讨了宋政府金银收入中与矿冶业发展直接有关的几个问题。上述宋代中央财政中几项大宗的金银收入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各地交纳的金银数额中相当一部分出自产矿地区或由产矿之地代纳。因此,这种举措构成了宋代金银矿业兴盛发展的动力之一。同样,大量的销金与白银的流失亦成为影响金银矿业发展的因素之一。不过,金的耗失却造成了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极大浪费,以致减弱了宋代金矿开发的积极意义。
二、铜、铅、锡的社会需求
(一)铜钱铸造与铜、铅、锡的供应
宋代的法定货币种类很多,有铜钱,铁钱,纸币,白银也常在大宗贸易中充当货币支付使用。然而在各种货币中,铜钱仍是宋代特别是北宋时期最重要的一种货币。北宋时期,除四川地区限定使用铁钱和交子,陕西、河东路为铜钱、铁钱兼用地区外,其余诸路都是以铜钱作为法定货币的,民间进行广泛的商品交易活动的主要媒介物是铜钱,宋政府用以统计财政收支的主要货币单位也是铜钱,其重要地位是其它货币所不可取代的,因此,宋政府一直控制着铜钱铸造和流通的大权。
宋代铸造铜钱的主要原料是铜、铅、锡,而这三类矿产品又是宋政府垄断的禁榷品,不允许民间随意流通,宋政府将岁课所得大部分用于铸造铜钱,因此宋代岁铸铜钱数额的多少与这三类矿产品岁课额的多寡是密切相关的。请见表3—4:根据上表列举的数字,从北宋初到神宗熙宁、元丰之际(除真宗天禧时期一度降低外),是铜、铅、锡岁课逐步增长而达到顶点的时期,熙宁后期的岁课额均远远高于以前四朝,充分显示当时矿业开采的兴盛发达。这一现象也为铜钱铸造量的增长提供了契机。
北宋后期,上述三类矿课减少,但尚可与宋英宗时期相伯仲。南宋以后,矿课额骤减,一落千丈。虽然南宋的地域比北宋缩小了,但铜、铅、锡的主要产地是在南方,受地域缩小的影响不大,故南宋矿课数额的减少仍能说明当时铜、铅、锡矿业生产的衰落以及对铜钱铸造业的影响。上表尚缺少南宋末期矿课资料,但是我们可以从铜钱铸造额情况人手估计当时的矿业生产状况。据方回《续古今考》所载:“宁庙既位,在宥三十年,理庙四十一年,度庙十年,德占一年勿问,总计八十一年,新铜钱并入内藏库,未尝行用。庆元至咸淳几易年号,民问无此新铜钱一文,尽在内帑,计铜钱一千二百万贯。”可知南宋自宁宗至度宗的八十一年间,每年铸铜钱平均仅十五万贯。另外,生活在南宋末期的许月卿在《都大提点坑冶铸钱箴》中也明确指出:“今岁额十五万,而封桩、内藏各受其半,左藏咸无焉,宜版曹之日困。”这一现象说明,在南宋后期相当长的时期内,作为原料的铜、铅、锡数额只能满足年铸钱十五万贯的需求,矿冶业生产无疑也是一直处于衰败不兴的局面之中。如前所述,宋神宗熙宁后期铜、铅、锡岁课额已达到历史上的极盛点,与此相应,这一时期的岁铸铜钱额也达到两宋时期的顶点——五百零六万贯。那么,到底需要多少铸钱原料,才能满足当时岁铸额的需要呢?据宋人记载,自真宗咸平五年(1002)后,铸钱“用铜、铅、锡五斤八两,除火耗,收净五斤。”“凡铸铜钱用剂八十八两,得钱千重八十两。十分其剂,铜居六分,铅、锡居三分,皆有奇赢。”这一用料比例虽然不是长期固定不变的,有时用料量有所增减,但是至少在神宗时期,仍是“依旧法,用五斤八两收净五斤。”熙宁八年的诏令也规定:“铸钱监所铸钱,每缗熟重五斤。”依据这些记载,当时铸一贯铜钱所用原料的总量是五斤八两,其中铜占百分之六十以上,铅、锡两类原料共占百分之三十以上。另外,根据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对考古发掘出的北宋神宗时期熙宁元宝、元丰通宝铜钱所含金属成份进行的化学分析和测试结果,还可以更精确地推算出北宋神宗时期铜钱中平均含铜、铅、锡的比例。请见表3—5:
从上述计算结果可以看出,熙宁元宝和元丰通宝的总平均含铜量为66.78%~66.81%,含铅量为22.69%~23.26%,含锡量为7.9%~8.66%,三种金属用料比例正好与史料记载相符。如果按照一贯铜钱用料五斤八两计算,五百零六万贯铜钱总用料将达二千七百八十三万斤;其中至少需要66.78%的铜一千八百五十八万斤以上,22.69%的铅六百三十一万斤以上,7.9%的锡二百一十九万斤以上。显而易见,这些数额用熙宁后期的矿课额来应付是绰绰有余的;用元丰元年矿课中的铅、锡课额亦足以应付,铜课额虽然有所欠缺,但考虑到可以加上熙宁后期累积的赢余铜料,所以元丰元年的矿课额基本上也能满足岁铸五百零六万贯铜钱之需。
总之,两宋之际铜钱岁铸最高额之所以出现在神宗熙丰时期,应与当时矿冶业生产的发达、矿课收入的大幅度增加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