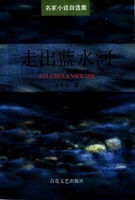幸福的生活,对我来说,就仿佛镜中月,水中花。
——柳池云语
2006年7月17日,我参加工作了。
中国北方集团亚华厂,是我参加工作的处女之作。不算精彩,却相当难忘。
亚华厂原本坐落在大山深处,躲的是帝国主义的惦记和阴谋,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深挖洞、广积粮",就是在那些年头喊出来的。后来,搬出了大山,来到蓉城,在上世纪末的一系列改革中,亚华厂推行公司制、债转股、中外合资、寓军于民……工厂发展十分迅速,逐渐扭亏为盈,效益年年上升。
掐指一算,也该知道这工厂的岁数了吧?对,已过不惑之年。
当年的建厂元老们,后来有的成了将军,而当年的小鬼,基本上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现已面临退休。因此,厂里风气醇厚,作风严谨。当然,也有少数人紧跟时代潮流,一转眼就扎进了市场经济的洪流之中。而我去的厂办,就是典型的扎进洪流之中、名利之中的部门。不过,这与其职能和工作环境是分不开的。试想,作为一个综合协调和对外接待部门,一味严谨,怕是上下关系都得罪完了,工作还怎么开展?
按规定,到厂先参加安全、保密等专项培训。培训结束后,得到工厂锻炼三个月,也就是作为普通工人,深入生产一线。其实我们这些初入职场的娃娃,一个个不懂工艺,工段长也不让我们真正上生产线,万一搞坏个零件,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一呼百应",带动一批次产品抽检不合格,损失少则几万,多则几百万。工段长可不愿担这风险。于是让我搞搬运,就是把码好的半成品推到下一工序。什么?搬运的方式还不够现代化?是的,他们依然沿用人力搬运的形式,不过由于产品特殊,附加值也高,因此搬运量不大。我们乐得清闲,每天没事就把搬运的小车推过来推过去,打发时间。
不到一个月,急需人手的厂办就等不及了,分厂领导告诉我,我不用到车间了,到厂办报到。主任分派我的岗位是:机要秘书,主要工作:送文件。
要说这送文件,本来也没什么技术含量,但关键是,文件多得出奇。而且,需要转送的领导、部门也很多。
厂长签"请某某部阅办",我就得爬跟头似地找到这个部门,把文件送到该领导手上;
厂长签"请某某、某某阅",我又依次把文件送给某某和某某;
郁闷的是,厂长签"请厂领导阅",我必须得把文件依次送到每一个厂领导手里;
最为恼火、尤其郁闷的是"请厂领导、党委委员、纪委委员、监事会成员阅之后,某某部阅办",这其间,又有人加批"请某某部复印留存",我的个天哪,神哪,这得送多少个领导哇,我哭;哪些是厂领导、党委委员、纪委委员、监事会成员,我都不知道哇……
更为可恨的是,一天文件多得起毛毛,集团公司办公厅、集团各部门、省上的文件、省上部门的文件、所在辖区的文件……刚开始,我脑壳大的哟。
不少时候,一份文件由于需要"阅"的领导和部门太多,以至于"阅"了两个月都没"阅"完。于是,有些领导两个月后才看到该文件,他们内心的光火我是可以体会的,要不是因为我是个年轻娃儿,估计还会以为我不重视他啥的,说不定就要开始整人了。
为此,临近办公室的厂领导经常"轻言细语"地教育我,还给我上课、出主意,主题是"如何实现文件的快速传递"。可问题的关键是,有些领导看文件一看就是一个星期,他看得慢,拖着不还,我又没法去索要,真让人伤透了脑筋。
由于文件太多,我脑袋发晕,有时会出现十分搞笑的错误。有一次,我经办一个文件,我记得是《国庆节放假通知》,嗒嗒嗒,满头大汗地发下去了。不一会儿,分厂的领导打电话来问,才知道出错了,原来,没加盖公章!又嗒嗒嗒收回来,去收文件的时候,我脸烧得跟有团火似的,简直想挖个地洞钻进去。
往事简直不堪回首。现在想来,十分感谢那些对我包容的领导们,尤其是张主任,他为此挨了不少批评,可他总替我兜着。还有位年近退休的厂领导,给我讲他刚参加工作时犯的错,以此激励我。可惜这位厂领导在我离厂后的2008年因病去世了,我是几个月后才得到的噩耗,悲恸不已,徒留遗憾。
功夫不负有心人。三个月后,我不仅熟悉了工厂的组织架构,各级各类"委员"、各单位的正副领导、各部门秘书也都混熟了,这为工作创造了极大的便利。我终于实实在在地把文件流转的工作担起来了。
同时,在我的建议下,工厂的信息员制度也建立起来,各部门定期传送信息成为常态,不久,工厂的信息工作从全集团倒数第三成为名列前茅。
军工企业的机关工作虽然轻松,但对具体业务的管理却缜密而严格。说是八点开会,没人说八点过两分钟到的;秘密级文件复印须登记,则是严格登记,没人敢越雷池一步;产品只能称呼代号,则没人会直呼其名。因为一旦出事,不但自己吃不了兜着走,还会连累一大批人——直管领导、专职保密员等。
单位的性质决定人们在工作中必须严谨、求实,所谓近朱者赤,久而久之,我也迅速养成了较好的工作习惯。当然,作为年轻人无法克服的一些毛躁心绪除外。更重要的是,日常的工作程序、文稿起草等工作都十分规范,压根儿就是来自公务员考试的《行政职业能力测试》的"公共基础部分",但是它远比书本上的要生动得多,这也为日后的公考复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好景不长,2007年1月,随着亚华厂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一些管理部门被撤并,一些同志充实到厂办。张主任对分工进行了调整,我改行搞行政事务,说白了,就是陪吃陪喝,跑腿打杂。这比送文件好一点点,但也相当郁闷。饭局接待的都是些重要客人,必须谨慎,但也得会插科打诨,适时调节气氛。我一个精钩子(精钩子,方言,光屁股的意思)娃儿,哪里知道这些,时常显得力不从心。
倒是张主任,上班时间,有事没事来一句:"小柳,到我办公室来!"一去,就把烟点起,我是来者不拒。云雾缭绕的,张主任就给我讲一些待客之道,还介绍某领导、某领导的花边新闻,目的就是增进我对领导的认识,以便于搞接待时能放得开。
张主任,子弟校高中毕业之后,考大学无望,便参加工作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工人。当然,之后又函授本科甚至研究生,这可以忽略,按他自己的话说,这些函授班对他的文化程度基本没有影响。其后,又参加迁厂工作,负责基建,后提为厂办副主任,又一年后,扶正。
张主任是个性格开朗、随和自在的人,他的一句话,往往能把尴尬的场面活跃起来,能把一潭死水说得微波荡漾,能把一局死棋说得左右逢源。由于在基层工作二十多年,他又很能体会作为办事人员的辛苦,因此,这也使得他很是体察下情。
张主任实施的是"宽松管理",其实就是不管,不知他是否信奉道家的"无为而治",反正每个人手里的工作,他平时是不过问的;你人在哪儿,他也基本不管。在其英明的"无为而治"之下,厂办的同志们都以大错不犯为原则,尽量搞"小错工程"。
厂里规定8∶00上班。我一般准时到岗,依次打开饮水机,打开电脑,泡好茶。然后溜之。到哪儿去?我起那么早,我能吃过早饭了么?8∶30~9∶00,是我准时的早饭时间。
我们习惯早上吃米粉。重庆口味的胖米粉,被烫得滑滑溜溜的,油、盐、酱、醋、辣一样不少,且用量适中。一大清早,尤其是冬天,喝点麻辣滚烫的米粉汤,就能立刻唤醒全身的细胞,真是十分快意。
有一次,我正溜号趴在店里挥汗如雨地吃着米粉,突然,看到前排一个熟悉的身影,啊!是工会甘主席,甘主席是吃完打算结账了,我现在跑也来不及了,况且不付钱就跑,老板也不让啊。被看见可咋整?说时迟,那时快,甘主席一转身就看到了我:"小柳啊!你也在这里!"我心想死定了,要知道,历次中干会上,这老太婆说得最多的就是员工纪律,我这不是被抓个正着吗。我此时正伸长脖子,等着甘主席宣判,"老板,来一起结了!"原来,她把我的账也一块结了,末了还说,"小娃娃,慢慢吃!"
我马上站起来,嘴里含着米线,挥了挥筷子,就差鞠躬了:"甘主席,再见!"
接下来说点实际的吧。厂里工资不高(集团有控制,必须按绩效记发),但福利待遇不错。职工都是五险一金(普通工人也一律如此),我们年轻人,医疗卡每月定期汇入50元,一年600元医疗费,哪里用得完;住房公积金扣了12%,据说是按规定的最高比例。算起来,我也有好几千的公积金了。可惜,现在已全部是死账,取不出来了。
逢年过节,甭管大节小节,一律发钱发物,少则三五百,多则上千。每个月都会发洗衣粉、肥皂。说到这儿,我也埋怨一句,厂里简直是忒没创意了,每次都是洗衣粉、肥皂的,我离厂的时候,单身宿舍里堆了好大一堆肥皂,远远看去,还以为是金砖呢!
有时候,开个会也发钱,季度会、半年会、座谈会,无不如此。
说到开会,有件事不得不说。厂里每季度都会举行一次经济活动分析会,这种会从来都在郊区举行,上午开会,下午消遣。2007年3月底,厂里如期举行一季度经济活动分析会,我负责会务。宾馆、会场、会标、话筒、座次牌、就餐,一切准备妥当,接下来,该到财务借款,准备发慰问金的事儿。按规定借出了几万,然后领款人要签字,然后凭此报销,用信封一个个封好。开会当日,职能部门汇报、分管领导发言、厂长作指示……
转眼到12点,会议结束,准备领钱、就餐了,与会人员排起"短龙",一个个到我座位前签字、领钱,发到最后,少了一个信封!
我看了装信封的背包,没有!看了座位下面,还是没有!
我傻眼了,里面可装着好几千现金呢!怎么说丢就丢了?
仔细回忆各个细节,应该没有问题。其实,至今我也不知道那一个信封丢在哪儿了。
年轻人心浮气躁,这话一点不假。尤其是年轻的男人,一天上蹿下跳,鸡飞狗跳的。当然,我那个走选调生的兄弟华子除外。此外,女同胞可能要好一些。理财、管物之类的事儿,交给男人来干,这不要命么。
总之,那次我就一下子丢了几千块钱。
张主任看到我这个情形,也郁闷不已。他赶紧把自己那一份掏出来,摆在我面前,让其他人先领走。看他表情严肃的样子,我估计这次完蛋了。下午,我没有在会场继续逗留,回到宿舍又找了一遍,还是没有!当时打电话告诉了张主任这个坏消息,他未置可否地挂断了电话。
郁闷,彻底的郁闷了。
第二天一早,主任把我招呼到办公室,他看我郁闷的样子,也没多说什么,向我宣布,我的会务组织费泡汤了,至于其余损失是如何填补的,我不知道,也没敢问。最后,主任交代我,马上开职代会了,一定把厂长的报告写好,以此作为回报。我的感激涕零自不待言。
我原本以为我在为厂办造成损失方面创下一个不可打破的纪录,没想到,小车班的一个兄弟迅速将我的纪录刷新。2008年10月,当然,这已是我离厂一年之后了,小车办的一位年轻驾驶员,在完成任务之后,到茶馆喝茶,把一辆帕萨特给丢了。
男人哪,男人,你为什么就这么粗心呢?
按理说,工厂的生活是舒适而安逸的。不紧不慢,没有压力,团结和谐,日子能过下去。
工厂的效益越来越好,2007年1月份,兼并了另一家业务相近的工厂,业务范围、销售额、科研团队都得到了进一步补充。厂里安排我兼任了机关团总支书记。对于将来,我也有了些许希望。
作为厂办工作人员,陪吃陪喝的生活是一如既往的。
作为涉世不深的年轻人,面对成天的灯红酒绿、觥筹交错,我也渐渐有所适应。看来,时间长了,任何事情都能适应,这就是马克思他老人家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为了生活,为了吃饱饭,人是啥事都能适应,啥事都能干出来的。
以往一提起"接待",我的头就会如发酵的面粉一样,膨胀再膨胀,但现在,我总会想,既然我吃的就是这口饭,那参与"接待"就应是理所当然的。就如历史书所说的"万恶的旧社会"的坐台小姐一样,一开始总有点处女的羞涩和反抗,而一旦放开了,就会有"既然反抗无用,还不如静静地享受"的思想。
一天下午,我正在会议室组织召开团总支全委会,会议即将结束时,我的电话响了起来。一看是张主任,我暗想:"看来一定有重要事情!"因为没事儿他很少打我手机的,我按下接听键:"张主任!你好!"
"你赶快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我说"好",然后宣布散会。
来到主任办公室门口,张主任一见我,就心急火燎地说:"快!跟我走!"
"啥事哦,这么急?"
"一个重要客户,今天必须接待好,这是死命令!"
他边说边往外走,我提起公文包就跟了出去。
来到酒店,定好包间,开好空调,摆好座次,安排好酒水,一番热汗淋漓,可算是准备到位。
过一会儿张主任又看看座次安排:"不对哦!客人咋能坐这个位置呢?这不是让人家等着付账吗?不好不好……快!服务员!来把这个座次牌换一下!"
看他心急火燎的样子,我不禁脱口而出:"不会吧,老大!跟你搞过这么多次接待了,没见你今天这样啊,用得着这么紧张吗?"
他瞪大了眼睛:"你才不懂哦,你知道今天这位管着我们多少产品吗?告诉你小子!30%,整整30%啊!"
我不屑道:"那有什么嘛,我们卖他们买,这不很正常嘛。"
张主任边丢给我一支香烟,边给自己也点燃:"这是客户,顾客,顾客是啥子?上帝!"
我默默地点燃香烟,心想:"说的也是,虽说是军品,人家不买你的,买别人的不也一样的事儿嘛。"
都安排妥当之后,我俩在楼下静静地候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半包烟即将告罄的时候,一行军牌车缓缓驶来,张主任迅速将手里的烟头掐灭,弹进垃圾桶,快步来到第一辆军车前,打开后车门,迎下一位一身戎装、英气逼人的军人,跟在后面的素来严肃的厂长,今天脸上也堆满了笑容。
一行人簇拥着,将客人迎到了雅间,我赶紧招呼服务员上茶,主客双双落座之后,我静静打量着这位客人,首先注意到其肩章,不数不知道,一数不得了,肩上的星星已经满得装不下了!两杠四星,二毛四!离将军一步之遥的大校!
"这么大的人物!难怪哦,弄得如此紧张。"我暗自思忖着。
接下来的事情就很程序化了,主客之间相互介绍随行人员,拉家常,互相交流对成都气候和时下天气的看法,其乐融融之后,厂长满面红光地端起酒杯:"各位!唐总代表一直以来都十分支持亚华厂的建设和发展,今天又千里迢迢来厂指导工作,让我们对唐总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唐总干练地举起酒杯,与厂长碰杯:"十分高兴再次见面,感谢盛情款待!"
厂长:"各位,干杯!"
一桌人举杯相祝,一饮而尽,我也端起酒杯,将喉咙的入口开到最大,一杯酒狠狠浇进去。见面三杯酒,作为开场白,然后才是"推磨子",这是四川的老规矩了。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推磨子",以酒局上的我为例,我要"推磨子",就得先将桌上的客人按尊贵程度,逐一敬上一圈,如一桌是十人,这就是九杯,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其他九人仍会"推磨子"推上一圈,我就又喝九杯。"推磨子"之后还没完,还得有针对、有重点地对最尊贵的客人互敬三杯。这还没完,还得对相互有点缘分的,比如老乡、校友等能拉上一点关系的互敬三杯。这桌酒局下来,每人都在30杯以上,八两左右。
虽说大学时代与兄弟们时常有"举杯邀明月"的时候,但也很少来白酒,可这接待工作又大多不喝啤酒,我就十分郁闷了。
喝到20杯的时候,我就有老牛拉破车的感觉了,吃力得难受!
看着坐在座位上偃旗息鼓的我,张主任使劲向我使眼色:"上啊!兄弟!你不支援我,我就要趴下了!"
我看看他那红得像猪腰子一样的脸,只好端起酒杯,继续战斗了。
饭局结束,我和张主任都奄奄一息了。将客人送到宾馆,我俩一齐倒在大堂的沙发上。
我递给张主任一支烟,给他点上:"老大!我今天彻底残废了,估计半个月不敢沾酒了……"
他打断我的话:"说啥子哦,半个月?半周你都跑不脱!你不上我一个人咋弄?副主任你也是知道的,他是闻酒就倒的人!"
"你战斗力够强啊!没我你照样把那些酒仙干趴下!你是酒圣哦!"
"我XXX的!这酒局太多了,铜墙铁壁的也让酒腐蚀烂了啊……"
我呵呵笑道:"你是不败金身哦,比铜墙铁壁厉害!对了,老大!你喝这么多,回去嫂子和侄女不说你啊?"
他狠狠吸了口烟:"哼!不说,不说才怪呢!"他像喷雾器一样把烟雾喷出去,惆怅地说:"但是又没有办法,办公室的工作,就是这个样子嘛!家人说自己,也是对自己好啊!"
我说:"也是哦!你反正家在厂里,再怎么的,也有人关心你呀!"
听到这儿,张主任抬起头,问道:"唉,说到这儿,你和企企谈了多长时间了?啥时候办喜事哦?"
我把念书时与企企交往的过程一一道来,又叹道:"老大啊,你看我现在的情况,两人相距这样远,结婚就分居,日子咋过?我是实在没有信心啊……"
他抬起手,使劲摆着打断我的话:"你这才不懂!一个人独处异地,人生地不熟,有个伴侣牵挂着,你才有生活的动力!可长期这样拖着也不是个事儿啊,两个人谈了这么久,你总得给人个交代吧!让人家这样等着算个什么事!"他喝口茶,"我就是个现实的例子嘛!当年我和你嫂子刚结婚的时候,还没度完蜜月,厂里就把我抽调到迁厂办,来到了成都,你嫂子一人在家照顾家人,这一分居就是十年!两人隔得远,有时也难免郁闷,可想着老婆孩子,这工作也就有目标了。每天想着给小孩儿挣奶粉钱,养家糊口,这不才有今天嘛……"他边说还不好意思地笑了。
张主任的一席话让我感慨不已,加上酒劲一上来,躺下就难受,翻来覆去难以入眠。我这样天天上着班有啥意思、有啥奔头呢,图个啥?
"你总得给人个交代吧!让人家这样等着算个什么事!"
"有个伴侣牵挂着,你才有生活的动力!"
张主任的话一遍遍在我耳边萦绕着,企企每周在车站送我时泪花闪闪的样子又浮现在我眼前。是该给企企个交代了!我默默地告诉自己。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迫不及待地拿起电话,给企企拨了过去,刚接通电话,那头就传来惊喜的声音:"呀!云哥,你给我打电话!我一起床就接到你的电话,我可高兴可高兴了!"
我故意搞怪地说:"哼!别高兴得这么早!"
听这话,企企明显郁闷了:"呀?咋的了?"
我嘿嘿笑着:"更高兴的事儿在后面呢!我这周末铁定能回来,而且有更惊喜的事儿跟你说!"
企企咯咯笑了:"真的呀!快告诉我嘛,什么好事情?"
"坚决不说!我回来就知道啦!"
周五一早,我就向张主任请了下周一的假。
回到虎钥市,我一下车就直奔花店,买了大大的一束红玫瑰,直奔企企的住处。企企一见我,惊讶得张大了嘴,直愣愣地盯着我,我走上前去,用手托起她的下巴,她眼睛一眨不眨地说:"云哥!你要干啥!"
"话都递到嘴边了!机会来了!"我暗想,"此时不下手,更待何时!"
我立即单膝着地,双手举起玫瑰花:"企企,嫁给我吧!"
企企眼睛闪动着泪花,面庞比玫瑰花还红,看我诚恳的样子,她点了点头,连忙拉我起来。
我说:"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企企将玫瑰接了过来,深呼吸一样闻了又闻,陶醉地娇嗔道:"谁没答应你了!我都点头了!"
一听这话,我啥都明白了,抱着企企在寝室里转着圈:"我有老婆了!我有老婆了!"
我"趁火打劫"地说:"我请过假了哟,明天就去领证!"
"假都请了?你咋知道我会答应你的?"
"哼!你不答应我,能天天接到我的电话这么激动吗?"我还学着她的语调,"呀!云哥打电话回来啦!云哥打电话给我啦!"
企企不好意思地转过身:"讨厌!我啥都被你看穿了!讨厌!"
我突然想起,结婚得选个好日子吧:"别忙,让我看看,明天是不是良辰吉日!"
企企嘟起嘴巴:"封建!"
我认真道:"哼!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当然得看一看了,虽说不信这个,可也得避开有忌讳的日子吧!"
一翻日历——宜婚嫁,我忙拉着企企:"企企,快看!快看!宜婚嫁耶!看来真是老天有眼,天意如此哦,呵呵,咱明天就去办了吧!"
企企将头使劲埋到我的怀里,说:"你说的,天意都如此了,还有啥说的……"
我悄悄低头看,原来她正咯咯笑呢。
周一一大早,我和企企踏上赴"围城"之路。
车上,企企附在我耳边低声说:"云哥,听说结婚是围城,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哦,你不怕吗?"
我坚定地抛出一句"柳池云"式的哲语:"爱情是婚姻的花朵,婚姻是爱情的果实。既然真正相爱,何不开花结果呢?"
企企一听这话,如释重负:"哦,还有这个道理哦。我没听说过,不过还挺有道理哈?!"
我心想:"那是!这是我的理论,你能听说过吗!"
公交车在虎钥市宽阔洁净的大道上奔驰着,天是蔚蓝的,行人是带笑的,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美好。
按照事先咨询的,先到派出所打印户籍证明,复印好身份证,赶赴民政局。
没进门,就发现很长的队,今天结婚的不少啊。
细看才发现,结婚的很多,离婚的也不少。排在前面的那对儿,明显就是离婚的,工作人员厉声问道:"离婚的?财产分割协议呢?!离婚协议呢?!什么?没有?一边商量去!商量好了再来!"
一旁的小孩儿则哇哇大哭,看样子娃娃才三岁,估计他也搞懂了离婚的含义,不论父母有怎样的感情纠葛,至少,以后爸妈不能跟他在一起了,这就是他的第一直观感受,对儿时有记忆的人都应该明白,此情此景,娃娃没有理由不感伤。
排到我了,工作人员:"离婚结婚?"
我怒了,心想这不晦气吗,没有好气地说:"哪儿有这样问的!当然结婚了!"
一听我这话,工作人员满含歉意地说:"哦!不好意思哈!那请你领表,一边填好,交到我这里吧!"
我想,对结婚的态度咋就好了许多呢?
我和企企挥笔刷刷地填好表格,交上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工作人员挥舞着公章,咔咔咔!两本大红的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的结婚证就OK了!
工作人员拿着结婚证:"好了!祝你们幸福!"
我惊讶道:"啊!这就办好了?!"
"对呀!好了!"
拿着大红的本本,我又惊又喜。一直以来,我都以为结婚很神秘,很复杂,这可是决定两个人一生的大事!程序应该很复杂才对呀!可没想到的是,填表、粘贴照片、加盖公章等等,不到10分钟,全部齐活儿了!
手捧着结婚证,我和企企会心地笑了。一直盼着的这一天终于来了,可当它到来的时候,却又感受到些许的不真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没来的时候,你天天盼着、想着,可它来了,你又不知所措。
走出大厅,就在虎钥市的大街上,我揽过企企,深深地吻了下去,我们俩手里,都捏着一本大红的、喜庆的结婚证……
结婚并未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太大的变化,只是我从成都回虎钥市的频率更快了,每周至少回家一次,成虎高速路上寄托着我对企企的爱恋。
越是如此,越是衬托出我在成都生活的"前途无亮",逐渐酝酿起让人难以忍受的孤独和落寞。
每个星期天下午,我都必须离开家,离开虎钥市,这熟悉的一切近在眼前,我却仿佛触摸不到,幸福的生活对我来说,就仿佛镜中月,水中花。
一个半小时的客车,再有一个小时的公交,抵达工厂已是晚饭之后。胡乱吃点面条,上上网,躺在床上想着未来的日子,想着这没有尽头的两地分居生活,然后默默地混着日子,期待星期五的到来。
星期一,还没回过神来。
星期二,稍微回过点神了。
星期三,开始正常工作。
星期四,盼着星期五的到来。
星期五,已经进入回家的预备状态,随时等着下班的铃声。
星期六,在虎钥市,高兴。
星期天,下午就得离开,又郁闷了。
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循环往复。
然而,我是如此地喜欢虎钥这个城市,我的企企在这里,我的大学在这里,我的那么多老师和朋友在这里。
每个周五,每当我乘坐的大巴驶出高速,向虎钥市区奔驰而去,此时的虎钥市总是这样多情而妩媚。宽阔的大道上几乎没有车辆,行人很少,如此宁静,如此安详;华灯初上,霓虹倒映在江面,微风抚过,波光粼粼的江水仿佛向你诉说虎钥市的安宁和美好。此时的我,一扫疲惫,心情总是为之一振。
虎钥市,我是如此地喜欢你,我舍不得你。
然而,偌大一个城市,哪里有我的所在,哪里有我的位置呢?
难道,偌大一个城市,就容不下一个小小的我吗?
渐渐地,我郁闷得有些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