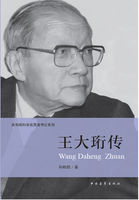这时太平军西征节节胜利。咸丰四年(1854)二月在黄州大败清军,湖广总督吴文镕投水死。咸丰急不可耐,亲笔朱批督促曾国藩出兵的上谕如连珠而下,一会儿说是:“曾国藩素明大义,谅不至专顾桑梓,置全局于不问,北重于南,皖鄂重于楚南,此不易之局也”。一会儿又说:“此时得力舟师,专恃曾国藩水师一军,倘涉迟滞,至令汉阳大股窜踞武昌,则江路更形阻隔。朕既以剿贼重任,畀之曾国藩,一切军情,不为遥制”。甚至说:“曾国藩以在籍绅士,专顾湖南,不为通筹大局之计,平日所以自许者何在?”几同于哀求。曾国藩至此踌躇满志,遂于二月率湘军倾巢出动,于太平军激战于湘潭、靖港等地,双方伤亡惨重。九月,湘军与湖北清军又反扑武汉,武昌、汉阳相继失守。咸丰五年(1855)初,湘军进逼九江,此时曾国藩的气焰更加嚣张,叫嚷要“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咸丰帝最初要各地组织团练的原意,是为了维持地方治安,但到此时不得不依靠湘军出省作战,表明清廷穷蹙到了极点。然而,客观形势却造成了曾国藩与湘军的崛起,到太平军失败时,曾国藩直接指挥的湘军就达10余万人,而湖南省参加镇压太平军的人数则达20万,相当于全国绿营兵的三分之一。除了李鸿章的几万淮军外,清廷在长江流域和江南的战局,几乎完全依靠湘军支撑。从此清朝军事的中心从中央移至地方,给晚清政局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湘军强盛之由在于水师之建,水师又始于郭嵩焘的建议,而始作厘金,也始于郭嵩焘。
由于清政府不惜倾全国财力兵力镇压太平军,至三年六月间,已拨军饷2963万两,户部库存正项待支银仅剩22.7万两。而战事仍在不断扩大,户部日形见绌,便以空文指拨,但久之空无可指,诸将帅亦知其无益,乃各自为计,其计有二:捐输、厘金。捐输即劝有钱的出钱,补助政府财政馈乏之缺。但富豪多与政府勾结,或本家就有人当官,从来只知道从别人身上搜刮,现在要从他们身上拔毛,谈何容易!捐输之道难行,那就只好向民众开刀。但农民破产,铤而走险的日多一日,如再向他们摊派新捐税,无异火上浇油。思来想去,唯有向还剩一线生机的商人伸手,增加厘金。即“于行商坐贾中视其买卖之数,每百文捐取一文,而小本经纪者免。居者设局,行者设卡,月会其数,以济军需。所取甚廉,故商贾不病。所入甚钜,故军饷有资,源源而来,取不尽而用不竭……”这是对商人征收的一种新税,货物值百抽一,无论坐贾、行商皆在劫难逃,说是小本经纪者免,实际上一开征收,任谁也难免。
这个办法,据清代官书记载,都认为是帮办江北军务刑部侍郎雷以咸采用幕僚钱江的建议首创的,实际上同时或先后想出这个招法的人不只一个,湖南厘捐就是郭嵩焘最先出的主意。大约在咸丰三年(1853)四月间,时郭嵩焘在湘阴家居,他虽“不复以仕宦为意,而于经营国计,保卫地方,无敢稍释于心,始终未一任事,而在湖南筹兵筹饷,一皆发端自鄙人。曾文正公始出,提用经费,支绌百端……黄南坡(冕)任铸炮,私设厘局常德,嵩焘以为此筹饷之一大端,言之骆文忠公(秉章),开办通省厘捐”。从此,郭嵩焘几年之内,东奔西走,以厘金为主,为湘军积极筹饷。湘军之所以能在前方放手屠杀太平军,与郭嵩焘这位后勤部长在湖南筹饷有直接关系。他的弟弟郭崑焘也与乃兄一样卖力气,亲自负责湘省厘金总局。郭嵩焘说曾国藩“办理军务,终赖此三项(湘省厘捐及粤、淮盐厘)以济军食,而湖南亦恃此以为富强之基,支柱东南数省”。这话不是吹牛。他曾与人洋洋得意地谈论过征收厘金的“高妙”之处:“今天下之利一出于商贾,取之以厘计,至约也。所取于商贾者,为厘以二三计;商贾所加于民率四五计。是仍取之于民也,于商贾何害?然使竟取之于民,则足以致乱,取之商贾,而民安焉。是又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这种变相取之于民的榨取方法,确实比一般赤裸裸的搜刮高明。郭嵩焘不仅能想出这种点子,而且能从“理论”上给予说明,认为是得了孔孟愚民政策的真谛。即有“实践”,又有“理论”,难怪曾国藩等人争相请他入幕府,当高参。
自雷以咸、郭嵩焘等人倡办厘金之后,各地统兵大员竞相效仿。咸丰四年(1854)后,厘金在河南、江苏等地广泛推行,而且得到了清政府的正式批准。从五年起,湘、鄂、川、赣、奉、吉、皖、闽等相继仿行。七年,胜保又奏准在全国各省一律办理。厘捐本是临时性筹款,不算正税,但太平军失败后,清政府并未撤销,反而变本加厉,征收范围日广,税额也各地不等,严重阻碍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直到清政府覆灭,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这块绊脚石始终未能被踢开。
从咸丰三年(1853)到六年,郭嵩焘一直奉曾国藩之命,在湖南、浙江等处办理捐务、盐务为湘军筹军饷。同时为曾氏兄弟献计献策。咸丰四年(1854)春,曾国藩督师东下,郭与刘蓉同行。至岳州,刘留曾营,以赞军务;郭则归里,治饷湖南。五年秋,曾国藩水师溃于湖口,间道走江西,收揖郭嵩焘之军,郭驰赴南昌相见,曾国藩甚喜,作《会合诗一首赠刘蓉郭伯琛》。诗的后几句是这样的:
困穷念本根,风雨思君子。
艰难复相逢,得非天所祉。
回首廿年前,志亢声亦侈。
忧忠阅千变,反听观无始。
郭嵩焘亦作《会合诗一首奉和曾少司马》。诗中云:
微生砚朝绿,守拙归田里。
结发贤哲徒,涉念每日喜。
谐谈契性命,此外均敝履。
浮名浸推许,力薄宁办此!
与世相背趋,放浪安所止。
欲持微贱躯,为人负弩矢。
髀肉虽丰硕,其实易与耳。
艰难纪会合,高论谅非侈。
人事如转园,谁能究终始?
顾惟蹇劣姿,野哉砼砼鄙。
群材斐然集,内省为愧耻。
同时,刘蓉亦作《次韵和曾涤生侍郎会合诗呈郭筠仙编修,兼简罗研生别驾》,诗中有“故人千里来,宛转相依倚,苦语杂讥嘲,中夜掀髯起”之句。郭嵩焘也《再和会合诗奉答刘孟容兄》:“东西楚连疆,中间亦千里。闻来杂疑信,乍见各悲喜。”时人余云焕读郭嵩焘等《会合诗》,撰《味疏诗话》,称此诗“造语奇倔,神与古会,直登昌黎之堂而入其奥”,“读之可想见轻裘缓带、雅歌投壶气度”。虽说是游戏之作,但仍真切地写出了当时江西战局的险恶与湘军处境的艰难。
咸丰六年(1856),郭嵩焘奉命赴上海,为湘军购置洋枪洋炮,开始结识西洋人,同时也接触到了自然科学知识,这使他在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