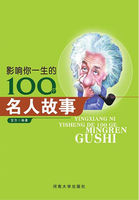七月底的上海,气象局发布了橙色高温警报,曾叔叔的夫人亲自切了西瓜递给我和她一双儿女,一边说:“老曾啊,天这么热,明天放小凝假,让她别去了。”
曾叔叔看报纸,随口应道:“没问题,小凝在家歇歇吧,辅导辅导弟弟妹妹功课。”
曾小弟从头到尾玩PSP,头都不抬,而Hello kitty一样嗲的曾妹妹跟她爹转的显然不是一个心思,扯扯我:“太好了,姐姐,我们去逛街。”
我吃着西瓜,很郁闷的想,果然我就是个托关系的闲人,律所那儿,我去不去完全一回事。
“对了。”曾叔叔折起报纸,对夫人道:“老齐你记得吧,他儿子明天过来。”
“小伙子挺大了吧?”
“那是,二十三四了总得,上回我去陵城见着一回,不错,很精神,小凝大概认识,那个小哥哥,小时候还抱你照过相呢!”
“没听说过,那时我多大啊?”
“好像是84年,是84年吧?”
“85。”他夫人提醒:“我刚怀上他们俩。”
“对对,后来三个人再也没聚上,你爸和老齐可能酒桌上倒不少见,总之跑不掉公检法这一块。”
我摇摇头,我爸偶尔感慨,他这个职位,有时候头天散步遇见还在点头打招呼的,第二天就进去面对着交代问题了,说不清,所以基本只做君子之交,点到即止。
翌日曾妹妹拉我出行,临走跟她娘说去逛徐家汇,结果地铁上她说:“姐姐,我提前两站下,你自己去逛好吗?”
“……”
“我,我谈了个男朋友,我妈不让。姐姐,你帮帮忙好不好,好嘛。”她抱着我胳膊晃来晃去:“下午我去找你,一起回去。”
“……好,好吧,那你自己小心。”
“哎呀,谢谢姐姐。”她跳起来“啪”亲我一下:“回头我给你电话!你自己慢慢逛!”
到了站她蹦跳着下去,车厢呼啸而过的时候,我看见站台上她正扑进一个绿发少年怀里,对方张开手臂,拥住她。
年轻的拥抱,充满义无反顾的味道。
下一秒地铁钻进黑暗的隧道,那对小恋人被抛在后头,我用力扯住吊环,对自己笑笑。
这里是不负盛名的商业区,繁华是很繁华的,没有购物欲望的时候,无趣也格外强烈,比如此刻的我,举一杯带麦当劳LOGO的可乐晃来晃去,店员看着我,招呼如同太监面对女人,欲望实在无从产生。
我还是很自得其乐的,看看时间到了吃饭的点,附近一家面店律所曾有人大力推荐,于是徒步过去,刚接下菜单,有人从背后拍拍我。
我回头。熟脸孔,律所里另一位律师带的小助,姓白。
“真的是你啊。”她坐到我对面:“进来看着就像。”
“呵呵,你怎么在这?”
“别提了。”她垂头丧气:“还不是上头指派,来客户这边取资料呗,你呢?”
我总不能说,领导特批,不用上了:“跟你一样,一样。”
“跑的累死了。”她用手扇风:“你说,用传真不行么?非说重要资料,得专人取送,唉--不说了,吃点什么,我请。”
“不不,你这样我都不好意思吃饱了。”
“你这个小姑娘,还真客气。”她笑:“好吧,那就AA。”
她边翻菜单,说:“带你们的那位李律师,案源多得不得了,手指缝漏一点出来,至少够养活三五个小的,不过听说他很小气?”
我想说,可不是吗,我到现在,根本没接触过他任何客户,我一个学生,两个月就走人的,至于这么防贼一样防着?
不过这话在我大脑和喉咙之间那一线涤荡一下,出来的是:“没有吧,我不知道,我觉得李律师人挺好的。”
“不过这个行业,本来男女就不平等。”她没接话,一边喝水一边说:“就像我跟的这个,王律师,本来混的还可以,回家生场孩子,好了,人家客户一看,唷,孩子妈了,估计时间精力啦都跟不上,脑子也被奶水糊住了,还是男律师靠谱,得,全流失光了。”
她敲敲包:“你看,好不容易拢住一个,紧张死了。”
我虽然觉得她稍微有一点交浅言深,但也生了知己之感,点头:“对啊,我来实习一个月,也觉得女律师怪不容易的。”
她杯子凑在嘴边,问:“你有男朋友了没?”
“……没。”
“哦,有了你就知道,女人还是嫁得好比较重要。”
她的语气我不喜欢,多大一点,二十二三岁的人,这么腐朽。她,我,加上曾妹妹,我有了老中青三代的感觉。
不过人各有志。我惆怅地想,如果是沈思博,要我当全职太太我也干。
结完账,白助理去洗手间补妆补了一刻钟不止,冷气打得很足,我趴在收拾干净的桌上,百无聊赖地往外张望。
我当然看不见,远处一列火车正停靠上海站。
我更加看不见,更远的地方,沈思博正站在我一直想带他去的溧湖岸边,一个女孩向他走近,她其实是欣喜的,却强作镇定,你,你怎么会来?
你,你怎么会来?这句话我也想问。
不是每个人逛了一天,回到住处刚进门就要客厅受这么一场惊吓--坐在沙发的青年闻声转头,正撞上我瞪着他,一只手卸掉脚上的鞋,然后我就这么把它递给了身后的曾妹妹,再把印有商厦LOGO的购物袋塞进鞋橱。
“小凝回来了?快来坐。”曾叔叔招呼我:“这位就是你齐叔叔的儿子。”
没完没了了,没完没了了还。生活如此戏剧的对待我,到底想干点啥?反抗不能,我和曾家小妹,坐到齐享对面的沙发。曾妹妹已经从接过鞋的那一阵茫然中醒过来,扯扯我:“姐姐,你看这个哥哥像谁?”
“谁?”
“最近那个韩剧的男主角啊,就是那个女主爱上了自己叔叔又被弟弟痴恋结果发现妈妈是姐姐最后得了绝症死光光那个。”
在她跟我详述这个科幻片的同时,她娘慈祥地问:
“小齐,有女朋友了没?”
“没有。”齐享目不斜视,很礼貌地回答,完了还补充一句:“暂时不想考虑。”
曾叔叔接道:“好好,男孩子,立业为本。”
“那也不能不考虑啊,喜欢什么样的?”
我下意识地侧脸,往窗玻璃那看一眼,短头发,尖下巴,有点二。我也不知道我看自己的倒影作甚。
齐享顿了一顿:“居家的,安静的,哦,有一点,最好是滴酒不沾。”
他说得特正经。曾夫人频频点头:“对对,喝酒的女孩的确不好--听见了吧?”
最后一句顺带教育她女儿的,曾妹妹乖巧地点头:“我才不呢,我鄙视。”
曾叔叔也附和:“酒场上最能体现一个女孩的教养--当然你们俩都是好孩子。”
我疯了。什么叫哑巴亏,这就是现行的。我除了闭嘴,没人注意时瞪他一眼,按照自某大师被用滥的描写来讲,就是眼光戳进他身体,再从后背透出几英寸去之外,基本无计可施。
但这个男人一察觉到我的目光,竟然立刻丝毫不避让地看回来,大概有十几秒的时间,他右手握成空拳抵在唇上,面无表情地看着我,直接的,压迫的,心无旁骛似的,哪怕一旁曾叔叔换了专业话题,正侃侃而谈。我或者他再不转开视线,难堪的不止一个。
我抓抓头发,把视线垂下来。
齐享放下手臂,轻咳一声,接过曾叔叔的话头,半个磕绊都不打,刚刚眼神的偏移,这么一来也就是一番思考斟酌,一点都不唐突。
而我彻底无事可做。
据说人年幼的志愿十分强大,可以影响成年后的行为。我怀疑曾叔叔小时候,立志要在家里开一间招待所,否则怎么来者不拒,统统热情的往家里招呼呢。
说实话,这我也不意外,让我意外的是曾小弟。
这小少年我一直偷偷怀疑他面瘫加交流障碍,我来了这么久,他跟我说的话一只手数都嫌浪费,只头一次见面时在他妈的要求下含糊不清道:“……姐好。”
再奉送一个抬眼皮的动作,抬没抬起来不得而知。
吃完饭齐享在客厅用笔记本陪他打了一会帝国时代,大约两小时之后曾小弟手下狼烟四起,国破山河在,十分惨烈。
曾小弟怒了。这个男孩表达愤怒的方式是这样的--撸了一把头发,沉默地关掉画面,再重新进入,咻咻的气息全藏在牙关里,瞪着齐享憋出来两个字:
“再来。”
齐享微笑着看他,我觉得他的样子很像是想拍拍对方的脑袋:“下次吧,得走了。”
曾叔叔夫妇还没来及开口,小男孩站起来,跑过去啪把大门给落了锁:“再来。”
他妈非常尴尬:“别胡闹!多大了,也不嫌丢人。”
曾小弟把钥匙塞巴塞巴搁进T恤里,烈女一样拢着领口,警惕地看着一众人。
曾叔叔看着儿子摇摇头,又转脸对齐享道:“你看,小齐啊,弟弟妹妹都留你,别走了,住这儿回头陪叔叔再好好聊聊。”
曾妹妹站我旁边,很乖的配合:“哥哥,留下来嘛。”
他的视线越过曾小弟看向我,我翻一下眼睛,转过身听见他说:
“好吧,再来。”
我在二楼刚洗完澡出来,就听见曾妹妹在隔壁房间激烈地反驳:“没有!我没有!”
“没有?那这怎么搞的?”她妈听上去也激动,声音打颤。
我很窘,刚想踮脚溜过去,曾妹妹却一眼看见我,喊道:“不信,不信你问姐姐!”
没办法我只能走进门。曾太太却不看我,只盯着女儿,脸色十分难看:“我谁都不问,我就问你今天到底干什么去了?”
我这才看见她手上拿一个胸罩,一边带子断裂开来,不是施了大力绝不可能扯成这样。
“谁让你乱翻我东西!”曾妹妹冲她喊:“我放在枕头底下的!你还去翻出来,你侵犯我隐私!”
“隐私?你是我生的,我是你妈!”
“我不是你私人财产!”
这对话怎么这么耳熟呢?我青春期的时候也这么说过,大概,一个字都不差。
母女两个对峙,曾妹妹神情倔强,但我接触到她手,手冰凉,在抖。
“阿姨,你别急,我还以为什么事呢。”我试图轻松地笑:“这不就是今天我们去逛文胸店的时候,试的时候,她一着急扯坏的嘛?都怪我,我当时也在试,没帮上她,很贵是不是?”
曾太太瞧瞧我,脸色稍稍平静,但明显还是不怎么信。
“哦,您看。”我捞过购物袋,摸出一对透明肩带:“当场都买下来了,才发现是固定的,不能换,您说多讨厌。”
曾妹妹使劲点头,她母亲看清发票上,的确是南京西路某商厦的章,总算是半信半疑:“扯坏就扯坏了,藏着掖着做什么?”
“怕您多想呗。”做女儿得了理,没好气。
曾太太沉默一会,把胸罩团成一团:“算了,我给你洗了吧。”
又说:“小凝,出来下好么。”
曾妹妹扯一扯我。我对她使个眼色,对曾太太应道:“好的。”
曾太太在走廊上对我说:
“小凝,我真怕她在外头吃点亏,被人家骗。她才十五岁。”
“……”那个发育状况,我还以为她至少成年了。
“说吧又不听,打又下不去手,你比她大不了几年,帮我说说她,行吗?”
我回去曾小妹在看电视,漫不经心地问:
“我妈又跟你说什么了?”
“没什么,让我说说你呗。”
“说呗。”她笑嘻嘻地往床上一躺:“我听着。”
“没这力气,我不爱管闲事。”
“看出来了,还是你好,不像我妈,老顽固。”她一只手拎起那对肩带:“幸亏有这个,你怎么想起来的?好巧哦。”
“那是因为,我也就买得起这个。”
“改天我送你衣服呗。”
“不用了,你省点心就行了,你才几岁?用得着那么着急吗?”
“啊?”
“别装傻。”
她嘿嘿地笑了:“姐姐,难道你还是处女?”
“……别提我,话说你才多大?”
“我十六了。”她挺起胸膛:“我该有的都有了。”
她穿少女型内衣,上面有白色的猫脸和蝴蝶结。
我捂着额头,真是电闪雷鸣的一个夜晚啊:“别告诉我你已经……”
“还没有,我这次那个来了。”她用遗憾的语气说。
我松了口气,我也不知道自己松哪门子气。
“姐姐,你难道不想跟自己喜欢的人,那个?”
我正把肩带绕起来,手上顿了一顿。
我唯一一件可以换透明肩带的内衣,是去年为了配那条黑色的小礼服裙。你说我想不想?他随时要,我随时可以给。可惜。
夜里我又做梦了,梦见沈思博娶了别人。醒来第一个念头,是梦啊,下一秒又想起来,现实其实相去不远。
再也没有睡意。我想抽支烟,这个念头突然无可遏制,我爬起来踮着脚,往楼下走。
曾叔叔家的这个楼梯结构,环绕型,转个弯才能看见客厅的情形。
沙发上有人,他闻声抬起头,我站在拐弯处那个平面上,手放在木扶梯上,和他面面相觑。
我一声不吭,转身上楼。
“下来。”
我停步,大哥,识相点能死不。
“我不下来。”我居高临下地看他:“我找东西,现在不找我要回去睡了。”
他淡淡的回道:“要睡你早睡了。”
“……哼。”
“来坐下,别跑来跑去的扰民。”他不看我,拍拍身旁的空位置。
我想起刚才的辗转反侧,慢慢走下楼梯,坐下来。
“来一支?”
我矜持地说:“不要。”
他就自己点上。我抱着膝盖,隔了一会问:“你为什么睡不着?”
“生物钟。”
“一点了,你生活习惯真差。”我鄙视地说:“你肯定会早衰。”
他看我一眼:“那你呢?”
“不告诉你。”我过了两秒补充:“我说这话可不是让你猜的意思。”
“你多虑了,我也没这个准备。”
我顿了顿,下了决心道:“我跟你说--”
他等着我说完。
我又没词了。
“你不就是想说,我因为你来的?让我少转念头?”
“哼。”
齐享侧脸,掸一掸烟灰,空的手来摸我头发:“没治了,你。”
我一闪,他的手长了眼一样跟上来,落在我肩膀,但我还没来及挣一挣,他旋即放开。
“道个歉我就算了。”
他往后靠靠,找个舒服的姿势架起腿:“不好意思庄凝,我又没有强迫你,我看不出来有什么可道歉。”
我其实说完那句就后悔了,的确矫情,此时悻悻的:“你为老不尊。”
齐享咬着烟,瞠视我,我还没任何心理准备呢,他哧就笑了,烟也掉到地上。
我吓一跳。
这位仁兄,我从没见他这么过,无声地,却是舒展地笑起来,整个人都仿佛打上了一层柔光,一下还不算,接二连三。
“有什么好笑的。”
他用手掌抹抹脸,俯身把烟从地上拾起来,总算正色:“那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你都忘了是吧?”
“当然了,记着干什么。”
“忘了就好,我也忘了。”
“最好。”
“不过还有一件事。”他在烟灰缸里把烟摁灭,抬头看着漫漫黑夜:“那个吻,是你第一次吧?”
“……哼。”
“否认没用,看得出来。”齐享起身,上楼梯:“晚安。”
他离开有五分钟我才反应过来,什么叫做看得出来?我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