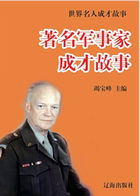漫天飞舞的雪花沉寂下来时,祖父在一片热闹声中过完了他的八十大寿。一脸酒色的祖父背着手缓步至门口,门嘎吱的响了一声,一阵刺骨的寒风扑在他脸上转眼便朝房子深处跑去。
祖父挺了挺他虾米状的身子,咳嗽了一声,从嘴巴里呼出的热气打着转儿暴露在空气中,很快就被凛冽的寒风裹住融化了。躬着背的祖父微抬着头,眼神落在四野的白色上,一脸苍茫。
凛冽的寒风裹着冷气再次朝屋子深处窜去时,祖父轻轻把门关上,一声轻微的叹息淹没在门嘎吱的响声里。
祖父的叹息声还是被敏感的父母亲捕捉到了,他们适才忙碌的双手忽然停在半空中,微张着嘴巴,一脸疑惑。
“爹,你哪里不舒服吗?”灯光暗处的母亲试探着问了一声。
祖父回头望了母亲一眼,就进屋去了,从窗的缝隙窜进来的寒风把他头上最顶端的那根白发吹的老高。
“死老头子,你又是怎么了,刚刚还这么高兴。”满头银发的祖母习惯性地骂了一句。
庄里的人都说祖父已经很圆满地走到人生边缘,年轻时参加抗美援朝冲锋陷阵,又养了四个挺棒的儿子,而今每个月还有600块的政府补贴,庄里的那些老人依旧津津有味地说着祖父的那些转眼便成云烟的事儿,眼里满是嫉妒与羡慕。
祖父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祖母藏着这点心思左思右想着,却依旧一脸疑惑。父母亲哪有这么多时间管一个已在棺材边缘打瞌睡的老人,他们为每天深陷在家里过多的事情里而烦恼不已。
过完寿的祖父心底藏着事,表面没什么变化,没事便拿着烟斗悠悠地走在云庄的小路上,跟庄里的那些小孩津津有味地讲他年轻时冲锋陷阵的事儿。祖父刚张口,露出几颗破碎的牙齿,云庄的小孩扭头便跑了。
“这个糟老头,总是缠着我跟我讲他年轻时打仗的事,我都听腻了,还不如去看动画片。”
祖父隐隐地听了,紧握烟斗的双手竟止不住颤抖起来。
“老头子,你这是怎么了?老毛病又犯了?”祖母驼着背走上来,看见祖父颤抖的双手,一脸茫然地说。
在一个深夜,整个云庄沉浸在一片梦境时,辗转难眠的祖母终于发现祖父的心病所在。
“走!走出云庄!我不能一辈子都窝在这里,我要出去看看。”面对祖父的呓语,这个已经陪伴了他一生的女人竟有些不知所措。祖母寻着记忆的藤蔓,恍惚记起祖父曾经是个诗人,忽然落下泪来。
整个云庄的人大都一辈子蜗居在庄里,等待尘起尘落。
几日后,祖母穿越巴掌大的云庄,来到了云庄之外的那家当铺。瘦小的祖母徘徊在门口,摸着那只藏匿了许多年的手镯,拿出来又放回去。在大肚子商人的注视下,祖母颤抖着双手害羞地掏出来递了过去,仿佛待嫁的姑娘。
大肚子商人接过来,便急不可待的扯下一层层手帕,一旁的祖母见了,心隐隐地疼。那是祖父年轻时向她求婚时,送给她的礼物。
落雨的黄昏,当祖母以商量的口吻把想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的想法告诉祖父时,祖父苍白如纸的脸因久藏的兴奋而红润起来,转瞬,却又黯淡下去。当祖母谎称自己有足够的私房钱时,祖父又恢复了原有的兴奋。
对于祖父祖母的决定,父母亲表面上是极其赞成的,但面对日子的捉襟见肘,暗地里又一脸冷淡,满腹牢骚。
深秋时节,整个云庄沉浸在一片金黄的诗意里。祖父祖母左右斟酌,终于选定了这个日子出门远行。临行前祖母整夜忙碌着,牙膏毛巾衣服还有刚腌好的韭菜,她装了满满的一袋子。祖父则坐在一旁,抽一口烟,望一眼祖母。偶尔站起来,在屋里踱着步子,或者望一眼窗外苍茫的夜。
当祖父祖母收拾妥当,滑入梦的深处,门外却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祖母匆忙起来,推开门,见是在外漂泊多年满脸疲惫的二叔,忍不住抽泣起来。娘,我回来,以后再也不出去了。祖母连连地说好。
那是个漫长的夜晚,六年不曾回家的二叔跟祖父祖母讲他的遭遇,直至昏黄的灯光映着二叔模糊的泪眼。
面对二叔的诉说,祖父祖母对于即将的远行不禁顾虑重重起来。
次日清晨,紧闭的大门开了,我听见细碎的脚步声,却始终不知道那是谁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