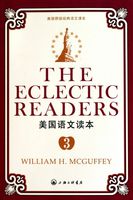“古来征战兮,几人归呀,马革裹尸兮,化尘土呀。壮士一去兮,难复返呀,瑟瑟风雪兮,空伤感呀。一将成名兮,万骨枯呀,名留史书兮,有几人呀……”
这风雪连天中,突然有人轻轻吟唱起悠远的古调,在曹军各大营帐中,由一人而起,再由他人接唱,一遍遍,伴着这风雪中萧瑟的气息,悄然引起诸将士心中共鸣,传开了,传到了虎贲营中。
“是谁在唱?”立在大帐百米外的典韦眉头微皱,问不远处的亲兵。
“好像是从我军军马场那个方向传过来的……”亲兵答道。
典韦一摆手,那亲兵退了下去。
歌声摄人心魄,饱含着浓重的哀伤和肃杀,把人心中的怨念和伤感勾动着,渐渐澎湃冲撞着心海!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数日来曹军高度战备,诸将士皆都是神经极为紧绷,积蓄着可怕的精神能量……在此歌的引动之下,一旦那弦被绷断,军中很可能出现营啸!
此歌太过于悲凉颓唐!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就在这个时候,典韦身侧不远处的许褚突然高声吟唱起了无衣战歌!他的声音哄亮通透,显然是集聚了可怕的内力而发出。
好一个无衣战歌!好一个天下虎痴!
典韦哈哈大笑,这生死至交的歌声令他极是畅快,也合着许褚,在内力引动下大声吟唱了起来。
曹操军中两大顶级的武神高唱起鼓舞士气的战歌,气势可非同凡响。受他们影响,他们身边的虎贲军乃至更远处的军营也渐渐传而唱起这无衣战歌,悲悲戚戚的精神一下子振奋了起来!
一场可怕的杀机,慢慢被平复。
曹军各营无衣战歌此起彼伏,声势颇是壮观,传出了百余里之外!
只剩下离着飞雪军营最近的军马场中,还有一个人儿在哼唱着悲伤古调。
……
英雄宝马,纵横天下!都说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可不久之前,这世间曾经还有另一人另一马在奉先军中——那个人武勇可敌吕布,那匹马速度可追赤兔。
只可惜,文远已死!只可叹,雪龙已盲!
飞雪噙着满眼的泪水,一手轻抚着一头瘦削到极限的骨架般的白色战马,另一手拿着草料在不断的强逼着哀求着它吃上一点。那白色战马虽然时不时的用脸贴贴飞雪,感激她的好意,但是绝大多数的时候,却是打着响鼻,马头别来别去,四蹄无力的踩踏着地面,极力的抗拒着食物。
“飞雪将军啊……这马是抱了死志,没了主人,便断了生念。自丞相手下亲兵牵来那日,便已几近绝食了。这些时日,我们这些经验老到的马夫们用尽了手段,也只能迫这马儿吃极少许的马料……越来越瘦,越来越弱,恐怕是撑不了三五天了。这是一头义马烈马啊!马性如人性,忠义无双啊!你看看那吕布的赤兔马,被丞相养得多肥多壮,主人崩逝,似乎与它没甚关系,正如吕奉先变幻无常,小人一般的心性!别再试了别再试了……一只因主人之死而生生哭出血泪、生生哭瞎双眼的马,它的死志,是任何人也不能改变的。”飞雪的身后,军马营中的一个老者劝道。
飞雪哪里会理他的唠叨哀叹,依旧噙着眼泪,很机械的向马嘴塞草料。
雪龙马……这便是天下少有的神驹之一雪龙马!因张文远之死,和大兵一个样子,哭出了血泪!只不过,某人的大白眼仁子没瞎,而这匹马却没某人那般好命。(雪龙马残念中)
数日前,飞雪将军跑到这军马场为飞雪营中几个新拔擢的女将寻些好马,无意中遇到了这雪龙马,看这瘦弱神驹气度不凡,再细问之下,便知道了前因后果。飞雪自幼是个男儿心性,喜武艺,极爱马,在曹军之中是出了名的,她坐下的良驹飞雪马便是伴着她在行伍之中一步步成长起来。这瘦弱神驹不凡,加之与飞雪宝马一般的毛色,她便对它有了特殊感情。女儿家在内心深处又是善良温柔,极不忍雪龙马绝食虐已,便三不五时的来陪它,想用少女温情感化这抱了死志的义马,让它能生出几许活下去的心意。
今晚的风雪之中,看着这半死不活的雪龙马,想着那张文远战死沙场,想着那北海城下十余万尸骨,一时心中感怀,飞雪便在刚才吟唱起了悲戚古调。她无心之唱,却差点让曹军出大事。
一人一马就这样温情而互不妥协的僵持着,足足过去了数个时辰。那军马场的老者摇了摇头,无奈的离去。
“没人了……就你和我,倔马,你就吃点,我替你保密便是。我知道我知道,你是马中王者,面子是要顾到的。现在没人了,你就别硬扛着了……你这个小倔马。”飞雪见老者走掉,终于停了歌声,凑到雪龙马儿的耳旁,小声对它说道。
马儿哪里能够听懂人话,只不过是飞雪想用温柔的语气继续感化雪龙马罢了。
雪龙马儿只照例回贴了她的脸,便继续别马头,不做退让。
飞雪哭的更加伤心,无力地坐在雪龙马的旁边,美目饱含着委屈和无力,哭出了声音,越哭越肆无忌惮……
这场面,和虎贲军统领营中的情景倒有几分相像,都是不听话的主把另外几个着急上火的主气到无语。
……
大兵就是个活宝,绝对是个活宝。外面一阵阵战歌飞扬,天寒地冻中,这个异类竟然倚着被打翻的火盆睡着了。从起初的梦呓到后来的鼾声如雷,真是傻人无愁事,天地皆是宽啊。
营帐之外,许典二人正唱的兴起,突然间看到风雪深处一队人马越来越近,他二人两张粗豪的眼眸中立刻闪现异彩。
独目煞星,大刀横持,纵马而驰,豪气冲天!
“元让!你怎么来了……我二人正唱得兴起,可没功夫招呼你。”
“元让!风雪连天的,碍了视距,前方高冷,你一只眼睛恐是看不清楚,却跑的如闪电一般,小心落马再把另一只眼睛摔瞎了。”
许典二人停唱歌声,冲着那来者打起了哈哈。
“军中刚刚生了些诡异气息,原本想四处查看一下安定军心,却没有想到,虎贲军士心神不乱,无衣歌起,全军悲殇之气尽去。便一路找来,到了二位大营所在。讨扰了……我顺便也来看看那人。听说最近他有些麻烦……”独目煞星见许典二人嘴上缺德,苦笑两声,跃马而下,朗声答道。
听到这话,许典二人冷哼,刚刚的一腔高歌豪情又被某个痴人的事给冲的七零八落。
三人结伴而行,走进营帐之中。
“尤那匹夫!真是必死贱命!如此时候,竟还能呼呼大睡!气死我也!气死我也!”营帐之中,重新传出了喝骂。
这一次,狂虐大兵之人又多了一个。
许褚典韦是动了真怒,怒极之下手脚便不再留力,虽然不驱动内力,却也是极恼怒的出拳抬腿。可怜的大兵在睡梦中正梦着老母亲和幺妹,转瞬间被生生打醒,然后是鼻青脸肿。更可恶的是,夏侯元让也时不时挤身上前,抡几个大巴掌。
好一顿暴揍之下,大兵虽然吃痛,但眼前这三人皆是自己军中很有感情之人,哪里会还手?只任这三人一直打下去。希望他们三人打够了,怒火消了便罢。在这件事情上,大兵心中也窝火,可是他知道那三人是出于好心担心自己违抗军令没命才如此气急败坏。
果然,打着打着,许褚、典韦、元让三人心中渐渐生出了不舍与怜惜……这个活宝成了猪头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活脱脱的受虐狂!
暴风骤雨渐停,四个粗壮异常的汉子喘着粗气。
“北海……张文远……无宝刀……成劣势!刀在哪里?刀在你的手中!你在哪里?你在北海城中拿着文远宝刀大杀四方!于是……我不武之胜……重伤文远……文远死志……最后一刻……故意撞我刀锋战死明志!文远死前对我说:有一个人,将来可胜他十倍百倍,就在那北海血肉尸海之中……无论如何……留下那人性命……或可助当世真豪杰孟德平天下……那人既是个傻子也是个圣人……那人既是个孬种也是个英雄……那个人心中有一个乌托之邦……那个乌托之邦是这乱世之中真正的仁武者心魂所归。”元让死死盯着大兵,第一次提到了北海城外两大绝世强者对战的细节。
这些日子来,这是大兵最不愿意去想,元让最不愿意去提的禁忌!因为,想到这些大兵会心胆俱碎,提到这些元让会深怀悲耻!
“张文远是什么样的人?忠义千秋,智勇双全!他临死之前遥指着北海那座血城,紧紧抓住我的臂膀,咳着血一字一句的说……死时,他的眼睛圆睁!还看着那座血城里的那个你!就算是死,他还那样的记挂着你!在他的心中,你就是他生死相依的袍泽兄弟!能被一代战神智神张文远如此看重的人,不会是凡夫俗子。文远是将你托付给了我!对于我而言,这是多么重的一份期许?”元让紧咬着牙关,声音既高亢又颤抖。他的虎躯也在颤抖!
大兵的眼中,闪过一阵阵炙热的悲伤,他只感觉到又要心死一会,是被撕裂一般的慢慢的死去。
“张将军……张将军……张将军……啊……”一口热血喷射,大兵哭得天崩地裂。血!又是血!血泪!眼中再度流出了血泪!
“文远啊文远!我对不起你!看看啊看看啊,你心梦所系的那个人,现在是个什么熊样?我夏侯元让不仅在北海城下仗宝刀之利才杀得了你,而且还注定要辜负你死前的重托。我堂堂九尺男儿,真是颜面尽丢,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你我都看错了人,他天生就是个蠢货孬种!他就是个天大的笑话……哈哈哈哈哈哈……也罢也罢,便让那个混蛋坦然的赴死去吧!到那个世界,再让文远你好好整治!我夏侯元让亦是个蠢材!他日若兵戈中陨命,便也去那个世界好好给你文远赔罪。”元让说到激动处,一阵阵残笑。
许褚和典韦静静立在元让和大兵身侧,两双虎目里也涌出了泪水。英雄相惜,元让口中的那个文远是他们做梦都想较量和相交的武中同道。今天元让这一番话,讲述了北海那场武神之战,怎不令他们动容和向往?
“我不是孬种!我不是蠢货!我不是笑话!”大兵流着血泪,双手嵌住夏侯元让的腿,咬牙说着。
“不要给我说!去给文远说!”夏侯元让突然一声长啸,巨手一抓,直接提起了大兵身子,迈开大步就向营帐外走去。
许典二人相视一眼,皆是目露些许不解。
给张文远说?张文远不是得道升仙了吗?莫不是元让也被这活宝给气疯了?胡说八道起来?一时无解之下,许典二人也只能紧随元让,疾步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