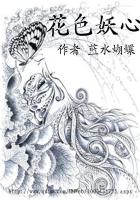不知霓霓在牢狱中受到了何等刑讯逼供,当她被送回了梦阁时,光鲜不复,还患上了见不得生人的怪毛病——谁敢在她面前晃悠,受不住控制的霓霓就要扑上去把对方好一顿蹂躏。故而押解她的官差将霓霓的指甲全磨秃露了,有的手指甲根断裂了,血痂结了几层。
官差丙说:“她是个疯子。牢里没那么多地方养闲人,还是让她回来吃你们的米饭吧。”
绵姨眼见这个头牌姑娘落得如此凄凉下场,怒由心生:“你们到底对她做了什么,她那么机灵的一个人为什么变得痴痴傻傻疯疯癫癫?”
官差丁不由分说地把拴住霓霓脖颈的粗麻绳塞进绵姨手中,道:“没有特别的,就是审犯人的惯例呗。”
“呸,我看你们是屈打成招!这个案子是怎么结的?”绵姨把笨拙如牲畜的霓霓揽在怀里。
官差丙冷笑数声:“婆娘,你可知就凭刚才几句话,完全可以让你也沦为阶下囚。”
官差丁恶讽:“兄弟可不能这么较真。毕竟是从前的红倌人,老鸨儿指着她赚钱呢,现在成了赔钱货,口出怨言是难免的。”
绵姨看着这两颗油头脑袋,真想拿瓢子掺了粪水浇他们个透心凉。
许是这中年女子浓妆艳抹的妆容上带着极度的仇恨,看起来不亚于饿狼扑食的嘴脸,官差丁有些退缩。他和官差丙交换了眼神,道:“好了好了,你不要这么看我们,怎么审怎么判是上头做的决定,我们也是被使唤的……她自己招供,说是那两个嫖客醉酒寻衅、互殴致死,咱们可没拿铁烙、指板夹手威胁过她!至于弄得这般破落,全因她自己在牢房里候审时臆想成病,指着谁都说妖魔,见人就挠,你说要不要拿绳子捆了,把指甲剪了呢?”
绵姨捧着霓霓堆满污泥老垢的脸,叹一声:“可怜了我的儿。”
“你这老妈子算是有情义的了,”官差丁道,“会把这种女的当人看。我以前见过的老鸨,逼良为娼羞辱凌虐的大有人在。”
绵姨扶着霓霓往了梦阁里走,头也不回地说:“都是跑江湖混口饭吃的,何必往死里逼?说不准就有求着我们这些下等贱民的时候,这世上哪有认死理的事。”
官差丙和丁临了没讨着口头上的便宜,无趣地走了。
都道风水轮流转,昔日登徒浪子们心尖上的香饽饽霓霓再没人愿意多看一眼,绵姨遣了她在后厨帮忙,只干些扫炉抹灰的轻便活,望她少受点刺激。
与此同时,老姑娘红漪却发迹了。当年,她和绵姨一同入这行当,踌躇至今,绵姨靠着软硬手段成了老板,红漪却还是无人问津,她曾经自嘲:“只怕进了棺材连臭蟞虫都懒得亲我一口。”但霓霓和纹如出事后,年轻的客人来得越发少了,倒是新增了几个年岁稍长的,对和他们年龄相近的红漪颇有好感。
才送走一个爱语绵绵的熟客,红漪又被点着去伺候另外三位爷。
提着两壶玉露琼浆,红漪早在心里筹谋好要怎样劝他们多多地喝这种昂贵的酒。轻敲了敲房门,里面叫声“进来”,红漪便满面桃花地进去了。
“你坐在一边不要出声。”一个肥脸盘的男人命令。
“三位爷点我来不是为陪酒吗?”红漪有些发蒙。
那个尖下巴的男人斜视她一眼,道:“喝你的酒就行,不用说话。”
红漪心想遇到这伙人也是倒霉,酒都是自己喝了,不能算在客人的账上,也就没法折钱到自己的荷包里了。
肥脸盘又上下打量了红漪一番,道:“我现在记住你的脸了。今天我们几个说的话,但凡泄漏出去一句,你也别想活命了!”
红漪乖顺地点着头,知道这三人来青楼是为谈事时避人耳目,又叫了姑娘作陪更能消除耳目们的疑心。她好容易红火起来,惜命的很,是决计不会多嘴的。
尖下巴叩了叩桌子,向一直不出声的第三人道:“储老弟,你这个脑子怎么就不知变通呢?”
第三人面不改色,说道:“要我乱国之纲法?前辈还是省下口舌吧。”
肥脸盘向尖下巴努努嘴,道:“哎呀,修梁啊修梁,咱们不要一开口就剑拔弩张的。令堂身体怎么样啊?我和他也算老相识了,你看哪天方便,我与胞弟一同登门拜访?”
储修梁一口回绝:“两位贾大人不必费心了。家父与我同食朝廷俸禄,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坦坦荡荡自然万般皆宜。”
尖下巴没好气地说:“后生,你说话拿腔作势得真叫人反感。这官场我兄弟二人呆得比你久,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储洲那个老庸碌,要不是因为只会画画儿又没胆子,早就入了这泥水塘子了!”
“侮辱我可以,不能说我的父亲!”储修梁一拳锤在桌上,铿锵作响。
肥脸盘立刻鞠起满面笑容:“好孩子别动气,贾利这张嘴从来没好话。我知道你从小受的教导,从你名字里都看得出——修梁者,国之佳木栋梁也。储老大人在你身上投入了不少心血,你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想来也懂得感恩泽而厚报之的道理吧。”
储修梁睥睨此人,正色道:“贾顺大人为我操心过虑了。君子施恩,惠泽天下;君子报恩,润物无声。我为人善、为官仁,就是对家父最好的报答,别的一概不求。”
贾利忍耐不住,向贾顺道:“大哥,你看他满嘴君子仁义,不就是在贬损我等是小人嘛!他不入伙随他去,干嘛非得硬拽进来?”
贾顺沉默片刻,再向储修梁道:“你大概不是很了解我们的作为,这么跟你说吧,此番也算是善举。”
储修梁一把抓过酒壶,倒灌十数口,英气满面:“贾大人觉得我年轻好欺吗?这种事哪怕披上再美的皮囊,都是烂到骨子里朽腐!”
贾利猛地站起身,一把揪住储修梁的衣襟,骂道:“乳臭未干的小儿也敢猖狂?!今天非得好好教训你一顿!”
缄默无语的红漪一下子联想到霓霓和纹如的悲惨,忍不住劝道:“客官客官,大家都是好不容易才得到今天的风光体面的,不要为一点小事弄得身份尽失啊。”
贾利反手一个耳光,直打得红漪半边脸失去了知觉;她不敢大声哭闹,只能用帕子捂着嘴,悄没声地流泪。
储修梁额上青筋遍布:“你堂堂金部主事,竟向妇人动手?简直禽兽不如!”
贾利挥着拳头冲上来要打他,被贾顺从背后抱住,折腾了好久才平息下来。
两兄弟气喘吁吁。贾顺挥挥手,示意红漪出去:“管好你的嘴!”红漪如惊弓鸟般快步向房门而去,经过年轻人时报以感激一笑。
现下房内只剩此三人。
贾顺扒拉过翻倒的凳子,疲累地坐下,向储修梁道:“老小子,你这一根筋倒和我当年有几分相似。”
储修梁不屑地哼了一声。
“然而有什么用呢?官场就是个大染缸,管你有多清白,进来了就得惹一身乌七八糟。我知道你满心都是社稷大业,绝不肯屈就与我们同流合污。但是你得搞明白了,难道你不认可,这个事儿就不存在了吗?今天,假使贾顺和贾利被你的耿直感动,明天还是会有别的贾顺贾利冒出来,可未必就有别的储修梁顽强相抗啊!你往大染缸里撒一瓢清水,微不足道。”
“等我检举揭发了你们的恶行,让你们受吏法严惩、天下人唾弃,自然能警醒那些鼠辈。”储修梁凛然道。
贾顺毫不掩饰他的轻蔑:“想扳倒我们是这么容易的吗?你可知官场里层层节节都是缠绕着的人情世故?你一纸状子别想递到户部尚书手里,莫论圣上!”
“这个还是用不着大人忧心。但凡我掌握了你们十足的证据,无论如何都要到朝堂上死谏,将一桩一件肮脏事剖开了给皇上看,不信圣上不动雷霆怒!”储修梁气势如虹。
贾顺和贾利面面相觑,立时并不能把这个年轻人怎样。
“你就真的一点不动心,不考虑一下吗?”贾顺见他软硬不吃,终于词穷。
储修梁向房门走去,步履沉稳。
年轻人启门欲出,似乎想起来什么,回头向贾氏二人道:“若是你们懂得悔改收手,我仍礼遇二位前辈;否则,修梁就等着看你二人制私币、盈己利败露后被流放三千里蛮荒地,终年黄沙掩面,此生愧为人!”他将门大力地摔上,昂首而去。
贾利的脸煞白下来,他凑到门前左看右看,确保并无人偷听。
“他竟然这么大声嚷嚷制私币的事!大哥,为什么不让我打死他?”贾利目眦尽裂。
贾顺不耐烦道:“你傻不傻?一个朝廷命官,杀了另一个朝廷命官会引起多大的麻烦,你不知道?到时候别说我们制私币的事要败露,从前买官贿赂、搜刮民脂民膏的都要抖搂出来,还要脑袋吗?现在一切都得低调,绝不能叫人怀疑,所以我连谈话都搬到妓院里来,就是这个道理。”
“那怎么办,姓储的这小子肯定要妨碍我们啊!”贾利着急,“对方已经催促了,是时候行正事了。”
贾顺摸了摸他肥圆的下颌,道:“杀,只能杀了。”
“你不让我动手,还让谁动手?”
“江湖上有个刺客组织,给钱就办事的,也不问雇主是谁,正对了咱们胃口。”
贾利闻言,尖耸的下巴放松了些:“好,不管花多少银钱,我一定要叫储修梁见阎王爷去!敬他三分瞧不上,那只能献刀子了!”
贾氏两人大笑一番,筹谋起制私币之事,故意拖延了些时间方离开了梦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