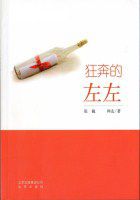甲乙
一般来说,在读者心目中,徐迅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散文创作上。但徐迅的写作并不只限于散文,在中短篇小说、现代诗歌等方面,他也很有建树。多年来,小说创作一直贯穿着他的文字生涯,也曾为之呕心沥血。近期,徐迅首部小说结集《梦里的事哪会都真实》即将出版。这让我们有机会全面认知徐迅小说写作的风格和特征。
对于我来说,可算是徐迅早期小说写作的一个见证者。这一点,倒是徐迅常帮我“温习”记忆,从中亦可见出其“点滴不忘”的敦厚秉性。近两年,我由于到龄赋闲,一直漂在京都。作为朋友和老乡的徐迅很热诚,每每把我招呼到他主持的饭局小聚,由此让我认识了京城不少作家大腕。他对初识者介绍我,总要开篇告白:“这是我的老师。”说多了,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做编辑发稿,这不就是我的本职吗?我几次试图劝止和修正,但徐迅始终坚持此说。时间一久,我也就心里甜甜地接受了。
回忆起来,我和徐迅确是由小说而结缘。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调入《安庆日报》副刊任小说编辑不久,还是个满脑子“小说构思”的准作者。一天,徐迅从郊县来,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时,他还是个很“文艺范”的小青年,精灵敏慧。有些鬈发,系着暖色格围巾;戴一副眼镜,镜片后的眼睛亮亮的。我们的话题自始至终没离开小说。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都有乡村背景,父辈都是值守大地的朴实农民。这让我们对乡土人事有着深切的体验和记忆,写作的素材也得之于乡野自然。在长江边的这座城池里,我们热烈地讨论着“乡村的小说”,竟不知不觉到午后,并由此有了“大地兄弟”般的投契。
现在我读徐迅这部小说集,仍感十分亲切。如果追根溯源,徐迅最早的文学实践自小说始。他的小说创作,虽有漫长的时间跨度,中间也曾有间断,但基本可以点线连缀,大致分为三个段落,第一阶段是在1980年代中后期;第二阶段是1990年代中期前后;第三阶段是21世纪头十年。仔细想想,徐迅小说写作的节点选择很有趣。他并不是一直都写小说,大多时间以散文写作为主,且取得极高成就。但他内心从未忘记小说,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小说不能“抛荒”,于是在每十年的某个期间又投入一定精力写小说,这说明他内心里是非常在意小说的——甚至超出散文。他曾向我表白:他丢不下这从年轻时就开始的梦想。也许他更爱的是小说。
徐迅早期的小说中,有一些篇什,我至今有很深印象,如《冬至》、《瞎爷》、《正月丧》、《奶奶不死》等篇,多取自亲身经历和体验,从他成长的那片乡野采撷而来,带有天然的朴实感和原初性。由于灵感泉源都发自培育他文学天赋的那片乡土,因此他早期的小说和散文相互漫漶,并无特别严格的区分,只是在对人物塑造和景物氛围的描写上各有侧重。
《梦里的事哪会都真实》是徐迅写于2006年的一部中篇。小说写的是精神废墟间的人生,再现了一个过往时代的语境。通过一座摇摇欲坠的老旧木板楼,几个偶然住到一起的青年的命运,倒映出一个时代的虚幻变形,以及废墟之上难以挺立的精神。“我知道,我是连拳头也握不紧的一个没有出息的男人!但世界上这样的男人远不止我一个,我过得窝窝囊囊,却也心安理得。”最为穿透人性的是小说的后半部分(可谓作者的神来之笔),深刻挞伐了人性深处的动摇和苟且——“我”终于要去为朱良复仇,也是为自己释放心中多时的愤懑和压抑,要去报复一个姓钱的坏官,但这仍然是一次无果而终的“行动”。那个姓钱的只是不着边际地说了几句话,就让“我”的冲动灰飞烟灭。这让我想起了鲁迅笔下的阿Q——国人灵魂深处的奴性,在历经所谓不同时代的近百年间,几无实质改变,并由不堪的精神及生存环境所延续,以此隐喻了人性的晦涩和陈腐现实的关联。但“我”最后毕竟从这环境中走出,这种微小的变化也是改变的开始。以此,徐迅赋予了这部中篇小说以超出那个时代同类小说的深度。
《一路平安》颇为奇特。一路平安实为“一路不安”。但这不安更多是来自命理中的,是人性中常有的对灾祸的预感。应该说,不舒展的生活和皱巴巴的精神总是同病相怜。车子行驶在蛇一般扭动的乡路当中,“我”在看自己手相时,突然对自己宣布“你多灾多难!”随之惊呼一声“这车子不能坐!”这很让人莫名其妙。但它揭示的是,我们的灵魂中总有灾祸临头的基因。这不是一个早晨、一段人生所能形成的。它证明的是我们心性中隐伏着某种“恐惧”。它如影随形,时时像绳索捆绑着我们。这更多是由负面主导的历史文化传统所带来。我在阅读时也一直提心吊胆。问题是最后小三轮车到达目的地,并未发生什么实质的灾祸。由此我这么认为:虽然现实中没有发生,可是“灾祸”却在我们灵魂中有准备地发生了。
《找人打架》中的张文,由于事事不顺,戾气难抑,青春期的冲动发作,不断萌生出“找人打架”的念头。但既悲且乐的是,真的有人陪他“打架”,他却是那么弱不禁风,让人忍俊不禁。以如此简短篇幅,演绎出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人物,可见作者对人性的洞察力。
《唱错了》写出了一个男子的失落和委屈。人生有时不知是对还是错,问题是当你发现“错了”的时候,一切都已于事无补。作者正是通过一种突临的悲恸表现出人生的大哀。
《等人喝酒》写的是酒足饭饱、志得意满的“办公室主任”杨和尚的人生。他世事练达,左右逢源,在一个油水和机会俱存的位置上运筹帷幄。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等人喝酒”——当然是上面下来的或有利害关系的重要人士。杨和尚是一本账。账本上记录着一个乡级政府及其周遭的酒欲和风情。这都没什么。小说笔锋一转,写到一直在乡里当计生干部,喝了一辈子酒的杨和尚老父,在临终前老是念叨一个“酒”字,就是不肯辞世归天。大家急切地猜测他关于酒的各种愿望,但就是猜不着。最后还是杨和尚心有灵犀,他对父亲说“不要喝酒?”父亲首肯,当即咽气。这最后一笔有如平地高山,异峰突起。
综观徐迅的小说,首先有着一个作家的独特视角。作品大多是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展开,让读者感到很强的写实性,显示出提炼和发掘的力度;但又不仅止于写实,它会通过一个转折节点连接上一定的荒诞性、梦幻性。这是徐迅小说有别于一般写实小说的突出特征。
徐迅小说的特征,我觉得还在于对直觉的运用。灵魂、自我、本能、窥探等,皆在其间运行,时有幽玄苍黄的意味。这些直觉、本性,是源自乡野的神秘、僻居的老屋、神魔的传说,以及随性所见所感,尤其是从心里所谓“第六感”走出。这和灵魂的特征相似,它在表达、挣脱或流泻。由现实场景和人性异秉形成小说叙事的玄妙。灵魂本能不可捉摸?莫名其妙的“事故”由此变成“故事”,变成让人难忘的“叙事”。
如果让我比较一下徐迅的散文和小说哪个更好,还真不好回答。但我可以辩证地说,假如站在小说立场上,你会觉得小说很有力度。而站在散文的立场,你会为其间的优美所陶醉。
2011年12月12日于京北大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