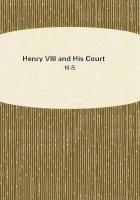按计划,王海波,邓君,毛猴子三个人每天驾着车满城的跑(他们的工作),替我留意天使的出现。肖海波也会在空闲的时候去几所中学玩。我们的宗旨是,无意中看到她而不让她知道我们在找她!
开学没多久,肖海波熟悉了几个同学之后,就把我的故事告诉了他们。
于是有几个女孩子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一个叫魏春玲。还有一个叫丘辉(女孩子)的老乡。一个人如其名叫谢远静的文气女孩。她们都非常热情的在我生活上给予帮助。而她们自己却说:她们很乐意有一个开小灶的地方。(后来其实我跟着她们去学校吃饭的时候很多)当然,她们既然是对我的故事感兴趣。我们的感情就很好的停留在了友谊的层面。肖海波却迷上了画画,是勤劳用功的好学生了。
魏春玲的身材丰满又匀称。任何人看见她,都会明白了“性感”的含义。在我第一眼看到她,却是明白了天使的身体为什么没有让我产生冲动的原因:她的身体美丽纯洁,却没有成熟的性的扩张气息。是教人爱惜呵护的,不是让人摘取拥有的。
这让我有了一种纯净等待的使命感。或者说更好的领会了天使留给我的信。于是我不再是急切的想看到天使。我在新的环境里和一帮新朋友们中。按部就班的开始熟悉新的生活。而我到桂林来的目的就不是那么单一了,开始了个人发展的内容。我更方便去买软件了是吧?我有更多懂电脑的朋友了吧?我在家里一个人玩着phptoshop,没有美术功底,给自己喜欢的电影做一个海报然后打印出来贴在自己的家里。现在有人帮助有人欣赏了吧?
到了晚上,邓君他们下班回来了,我们又是那样开心的在一起。于是我其乐融融的在这个环境里生活。
但在很多时候(他们上班或上课去了)我还是一个人。仔细的把对天使的思念放在心中。默默地走在车流边,人群里。仿佛是桂林市最闲的一个人,又仿佛是桂林市最坏的色狼:有青春少女移动之处。我的视线立刻敏锐的将其捕捉。大脑迅速将一系列数据分析。不是,不是,也不是……
有时候想念在心里太浓了,我会拿出她留给我的信。看看她略带稚气的字。想象她的小手如何在上面晃动着。有一次我才发现,信纸的边缘有半滴泪水。是泪水吗?我想应该是的。在她折了信准备放入信封时时候,落下一滴泪,打在了信纸的边缘。随即沾湿了半个圆印。我感慨,又希望不是。我希望她就象不懂事的孩子,开开心心的就搬家了。
白昼越来越短,风越来越凉。思念越来越长,梦想却仿佛越来越远。奇迹始终没有出现。再没有天使的任何消息。
******************
直到到寒假来临,时近春节。我生日的那一天。肖海波和我在屋子里。他画画,我在学剪纸。窗外的天空阴沉沉的,寒风刮过,呜呜作响。我们等着邓君他们三个人回来就一起去吃灵川狗肉,准备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来为我过生日。
突然邓君回来了,他一进屋就大喊一声:“下雪了!”我和肖海波都微笑着抬起头,看着他。因为我们经常用“下雪啦”这句话来表示自己正在遭受的寒冷。只见他慌乱的取下手套,把手伸向火炉。说:“是真的,我特意回来带你们出去看雪的!”见他不是说笑,我和肖海波这才停下手中的事。跑到窗户向外看。
这雪很有些突然,好象是因为风太大了才不小心吹落到了这南方的城市。而地面并没打算接受它们的意思。雪花是很大一团一团的直往下掉,但到了地面一下子就不见了。
我们坐在车里,感受到的世界静悄悄的,雪花却又以极为热闹的形式纷纷扑过来,扑过来……世界就仿佛在极安静却又极疯狂的舞动着。我们都为之惊讶了,报以安静和欣赏来表示对大自然神奇的尊敬。路上行人和车辆都越来越少,邓君把车开到了郊区。
在这里,灌木丛上已经覆盖了一层不薄的白雪。就是泥地上,也积起了一点雪了。有很多人都为这几年不见的大雪而欣喜。一群少男少女更是抓着树叶上干净的雪互相抛洒着,欢笑声随着雪团飞上天空。
邓军把车停下来。我们立在车边,微笑的看着他们。
突然有两个小男孩跑过来洒了我们一把雪。乐呵呵地跑了。邓军立刻就追了上去,肖海波紧随其后。我笑着,没有跑上去。我看到一个女孩子的身影很有些象楚楚,我的天使。但是当她回过头一笑,我知道了她和天使的距离。可我却不禁浮想联翩了。想象着和天使在雪地里打闹奔跑的欢乐。任雪不停的落在我头上,肩上……
天色越来越暗,估计已近黄昏。
我叫邓君他们回来了。他们笑着,低着头躲着身后的攻击跑回来。邓君意犹未尽,抓了车顶上的雪远远的向他的“敌人”“开了一炮”。我说不吵啦不吵啦。肖海波说:“搞点音乐来听听。”拧开了车上的收音机。唏哩哗啦一阵响过,一个男中音很清晰地传来:“现在是听众点播时间。首先是一位日本女孩来信为她的哥哥点播。来信说:楚雄哥哥,分别已经半年了。你还好吧。我现在在日本读书,很想你。今天是你的生日。为你点播一首《此情永不移》希望你能收到。我的祝福,我的思念。”
“看来是她的情哥哥啊,来自遥远的异国,这太难得了!”主持人笑了笑。接着念:“你的天使,欧阳楚楚”
我激动得大喊起来,一把抓住肖海波的肩:“你听到了吗?点给我的。你听到了吗?”他傻笑着:“是天使?”“是啊,她在日本!”说完我不等他说话,回头仰天长啸一声----
静下来,那些嘻闹着打雪仗的孩子们都静了下来,看着我。于是车里的歌声飞出来,我看着天上的雪就象是在随着音乐飘荡,最后又旋转着扑入了我的怀抱,亲吻了我的脸。向我诉说了无尽的离愁和想念。
我抹了一把,整个脸都湿了。回过头发现邓君正呆呆的看着我。肖海波则坐在车里,呆呆的在听。我招了招手,和邓君都上了车,但是没有发动车子。摇上车窗,外面孩子打闹的声音便宛如遥远的童年,把如今的爱的歌声反衬得无比真诚和惆怅。
我们静静听完了歌。邓君再发动车子时的声音是那样的刺耳。雪似乎小了很多,但仍有不停的扑上前窗。被雨刮器扫过,细沙般的画成圆弧。待到刚刚细融成水,便被雨刮器推开了,却又有新落下的雪被扫成了透明似的细沙圆弧……
时间就仿佛是这样的原地轮回。我们都在同一个问题上沉默。这半年的努力是否白费,接下来该如何是好呢?
回到家里,王海波和毛猴子已经在家等侯了。
“我们找到天使了。”邓君一笑起来就会露出两颗虎牙。
“哦?”王海波反应最快。“叫她晚上出来吃晚饭。”
“她在日本。”邓君带了一句粗话在后面。
“那你怎么知道。”
“她给###(我的诨名)点了一首歌。”
“……”
“不管她啦。”我挥了挥手,“走啦,我们吃饭去。”
“###(我的诨名)你想不想去日本打工啊!”在路上王海波对我说。
“我去能干什么啊?”
“去洗碗端盘子啊。”大家都笑起来。
王海波急了:“笑什么啊很多钱的。我就打算办了护照去的。”
“……”
“她怎么知道你生日啊?”毛猴子问我。
是啊!“可能是那天她看了我的身份证啦。”我不是很确定的说。
大家七嘴八舌的一路嚷着。最后肖海波说:“不怕啊她不是还想着###(我的诨名)吗?不知道哪天就回来了。”
大家都轻松了,我也真的很高兴起来。到了预订的饭馆,丘辉,魏春铃,谢远静还有一个腿很长的女孩都到了那里了。丘辉说正在给大家倒茶的长腿女孩是她的“干女儿”。大家都表示晕倒。(那时晕倒一词尚未发明或未流行到我们生活中来)因为她们是同班同学。
很自然,我的故事的新进展,她们都知道了。
丘辉问了:“你那天使多漂亮啊,你这样痴心!”
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爱别人有些不理解了,但这就算得上是痴心了么?我觉得自己很普通很正常啊。
男孩子们都沉默了。女孩子则都一副兴致勃勃的表情。王海波说话了:“你觉得张曼玉漂亮还是巩俐漂亮?张子怡?”
“哇,她们都是明星,都很漂亮哦!”
“那就这么跟你说”一向自以为帅过刘德华的王海波喝了一口茶:“天使往她们面前一站,她们就普通得跟大街上的女人没什么两样……”
我赶紧低头喝茶,看到女孩子们的脸上呈现出非常一致表情:刹那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
“别说得那么神,情人眼里出西施嘛,去看看菜怎么还不上来,我饿了……”
我必须这么说。
肖海波却来了劲头:“这么说吧,古今中外所有形容美女的词语都用在天使身上,你会觉得还不够。要么你会觉得自己知道的词语不够,或者觉得人类的语言还非常欠缺……”
“哇”女孩子尖叫起来。“太夸张了吧!”
我也不由得大笑起来。
“……”
“女人太漂亮了不好。”丘辉说。“你会为她累很多,吃很多苦的。”
“她不是女人,她是纯洁的女孩子……”我立刻纠正。
长腿女孩子(至今不记其名,万分抱歉)赶紧说:“哦,好啦,对不起我们的大情圣了!”
大家都又笑。
香喷喷的灵川狗肉来了。桂林一宝----三花酒来了。大家干杯:“祝我们的天使早日回来!”声音之响亮,余下满堂一片肃静。
我心里有句话一直没说,我一年几乎不听一次收音机。为什么惟独今天就收到了天使给我的生日礼物呢?我已经相信了缘分天定这句话了。饮酒过量,一路妙语豪笑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