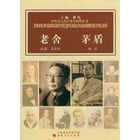——写在前面的话
1984年7月29日,总部位于美国洛衫矶市的全球第二大海外中文日报——《国际日报》(International Daily News)刊登了一篇署名方怡的文章——“航空界先驱王士倬”。文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
“凡了解中国航空界的人士,一定熟知王士倬。”同一日,香港《晶报》广州专稿栏目刊登特派记者林君的报道,文章的开头也是相同的一句话。在大陆的诸多航空界人士会不以为然,因为确有许多人不曾听说过这个名字。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了解到王士倬先生。以后是在国务院参事室一位领导同志的帮助下,与王士倬最小的儿子——王昌井先生取得了联系,并得到了王士倬先生生前写的一本自传。那是一个极为普通的笔记本,封面上写着“自传誊清本”几个字。字迹苍拙,用的那支圆珠笔似乎已经没有了油,笔画有点断续,有的地方划了几次。
自传的誊写显然是很用心的,极少修改,与封面的字迹不同,除最后几页略显粗疏外,总体是很工整的,像是一个好学生的语文作业本。
自传从他的祖上写起,直到1991年10月入住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之前,全文共3万余字。那时的王士倬先生患有严重眼疾,视力非常弱,在经历了80多年坎坷跌宕后,他努力地做了一件事——写下自己对人生的回忆和感悟。他想留给后人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
当一字一句把他的自传录入、在仔细辨认他书写习惯的异体字时,眼到、心到、手到。感受着他的思想、感情、精神,我们与这位老前辈进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交流。
他创造了中国航空工业历史上的几个第一
在整理王士倬先生自传的过程中,我们搜集了几乎所有能够搜集到的资料。从这些资料中了解到,他的一生曾经创造了中国航空工业历史上的几个第一:
“1934年至1935年间,由王士倬教授主持设计建成了我国第一座航空风洞,其试验段风洞直径最小为5英尺、最大约10英尺、长50余英尺。”(《清华历史中的航空工程系》清华校史研究室)
“1935年……清华招考专科生,专习航空,钱学森当选,在国内培训一年,由王士倬指导,后赴 MIT 及CIT,成为冯·卡门教授之高足,为航空工程权威。”(《九二自述》[美] 顾毓琇)
1935年“10月 10日,刘仙洲、王季绪、杨毅、李辑祥、庄前鼎、顾毓瑔和王士倬等人联名发函,在机械工程界征求成立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的发起人。……时至1936年1月,已征集到发起人152名。在北京清华大学成立了筹委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的早期历史)
“1936年,又由华腾多夫、王士倬等教授主持和当时的助教以及第一届毕业的学生十余人参加,设计了试验段直径为15英尺(必要时可扩大至20英尺)的大型航空风洞。该风洞的设计得到了当时欧美航空界的赞许,曾登载于英国第一流的飞机工程杂志及国际应用力学报告内。”(《清华历史中的航空工程系》清华校史研究室)
“1936年……5月,中国工程师学会在杭州举行联合年会,……王士倬、冯桂连、华敦德、张捷迁宣读《清华大学之航空风洞》得第一奖。同时,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成立。”(《九二自述》[美] 顾毓琇)
“……王士倬厂长到任,并不比其前任轻松,因为航空发动机批量生产是我国航空工业史上的第一遭。”(《乌鸦洞的奇迹》欧阳昌宇)
“……到1947年初,30台航空发动机终于完工。由航委会任抽一台装在昆明第一飞机制造厂生产的飞机上,由昆明直飞南京证明发动机性能良好。至此,大定厂已完成了我国自制第一批航空发动机的历史任务。”(《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与浙大校友》欧阳昌宇)
他的周围群星灿烂
在这本薄薄的、看起来十分简陋的笔记本里,记录了太多的历史人物。
有张任、顾毓琇、王昆仑、庄前鼎、叶企荪、李辑祥、王云五、梅贻琦、李耀滋、钱昌祚、许锡缵、叶玄、徐昌裕、黄光锐、王助、李柏龄、王造时、吴景超、孙承谔、梁思忠……
这些人都是在历史上有着影响和显赫家世及社会地位的。在这些人之外,还有更多的一些知名人士与他有过交往,他没有写到,也没有渲染。
被中央组织部誉为“中华民族英雄”的中国科普事业先驱高士其先生与王士倬同庚,同年考入清华,又同年赴美留学。在为他平反的事情上,完全是因高士其先生的影响,才得以引起高层重视。但他在自传中却只是淡淡地一笔带过,反而是高士其先生为与他的见面写下了一首诗。高士其先生是一位想象力极为丰富的科学家和杰出的科学普及工作者。他的作品像童话、像儿歌,纯真、阳光、美好……但在这首诗里,他写下了“一把辛酸泪”这样沉重的字眼。
1984年,钱学森先生给王士倬先生写过一封信,开头写着“士倬吾师”。钱老作为中国科学技术界的巨擘,他敬重师长的大家风范跃然纸上,其信中流露出的真挚情谊令人感动。
这些事在自传中都没有提及。
1997年,顾毓琇先生在知道戴振铎先生写了《纪念冯桂连教授》一文以后,不顾年届95岁高龄,“赶写”《纪念清华航空工程组创始人王士倬教授》一文,希望同时发表。1926年,王士倬先生对学习机械工程产生动摇的时候,是顾毓琇先生劝他学习航空的。这位学长满怀深情地回忆到王士倬先生自1933年1月被聘为“航空工程组教授,遂为清华航空工程组创始人”到设计建造中国第一个风洞实验室的经过。他写到:
“本文纪念王士倬教授只限于清华自制航空风洞。但王教授对航空航天人才之培养,实有不可磨灭之功绩。本人于 MIT 进修时,曾同住一年,而早出晚归,极少见面。在清华任教时期,则朝夕相处。其努力创始航空工程组,至今钦佩。”
那个时期的顾毓琇先生刚过30岁,王士倬先生则不到28岁。他们都是在13岁的时候,考进了清华。
如果我们把王先生的自传作为一个索引,会发现我们的历史上曾经有过那么多杰出的人物,拥有那样厚实而宽广的人文底蕴。通过对这些人的了解可以发现,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基础,我们的祖国即便在“黑夜”也有着灿烂的星空。
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的航空事业中,他没把自己当外人
从国务院参事室保存的资料中,王士倬先生还留下了一份上交组织的“王士倬的自传”。自传没有说明时间,也没有落款,文字的最后,是一个放在括号里的“完”字。细读之下,可以肯定该自传写于 1950年,而且是写给当时的重工业部组织的。
与这份自传在一起的还有三份资料:
一、建设航空工业意见书
二、我希望怎样做航空工业的准备工作
三、我所看到的几个问题
在“建设航空工业意见书”中他阐述了以下的观点:
“将来一定要办航空,这是中国人民没有异议的主张。今天呢,国家的财力不易照顾,这亦是大家很易了解的事实。但是,航空工业不是简单地说办就成,就是有了钱没有技术上的准备,亦是枉然。”
“飞机是在20世纪(1903年)始为人类发明创造成功的东西。它象征着现代最新颖的科学技术的结晶品,它的制造技术是复杂的。当然,我们不可望而生畏,我们要有步骤地、有重点地、并且有决心地克服困难。”
“检验做得好或坏,可以决定飞行人员的生死,可以延长或缩短飞机的有效寿命,可以使整个航空工业成功或失败。……我们要求一切合理化,科学化。科学的真理是可以用实验来证明的。从不断的实验中,我们可以获得新经验、新学识、新进步与改良。”
在“我希望怎样做航空工业的准备工作”中,他写下了这样的意见:
“调查工作,一开始由本人作广泛的旅行参观并与各方面负责人洽谈,逐渐走上通讯填写表格以及统计分析的轨道。”
“与空军及民航修护部门联系修护现用飞机的实际问题,我们必须了解。现在如此,将来我们能够制造飞机时,更应该如此。”
“飞行安全的因素非常重大,我们绝对不可以勉强,把不够好的东西充当好东西。怎样才算好东西呢?航空技术先进的国家,订制规范,用数目字规定怎样测验好歹。我们应搜集此项规范,以供参照。”
紧随其后,他秉笔直书,写了一个用词激烈的意见——“我所看到的几个问题”:
“我已介绍了自己的履历,提供了些意见,并表明自己希望做什么工作。以上都是比较简单的叙述,没有把复杂的问题提出来讨论。正因问题复杂,我一个人无法解答。但问题是存在着,不提出来请别人注意、要求大家研究讨论,更是不诚实而且不负责任。仅把问题提出,恕不详加解释,恐非一页二页的篇幅及数小时的思索所能办到。”
再接下来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不到千字的短文,竟然用了26个问号。尤其是在最后,竟然问到了:
“台湾什么时候可以解放?这个问题影响我们的计划很大。……重要的问题,或者是,解放台湾究竟需用多少空军威力?还需要重工业部来建造这样的威力吗?”
与王先生最后写下的自传对照一下,我们可以了解到写这些意见的一些背景,那个时候的航空工业筹备组应该是有着一个可以敞开心扉,畅所欲言的环境。
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和理解他的见解。
他提醒政府,航空工业必须要建设,但需要准备,尤其要量力而行。
“航空工业不是简单地说办就成,就是有了钱没有技术上的准备,亦是枉然。因为航空事业在国防上的重要,各国都寓军航于民航。否则纯粹军用航空赔累更大!”
这是中肯、睿智的建议。在我们今天大力宣传“寓军于民”的国防工业指导方针时,可能没有人知道,在半个世纪以前,有一个人已经提出了“寓军航于民航”的建议。
他批评了蒋介石时代的“自作聪明”、“不重视规范”和“迎合飞行的心理”。他为新政权的担心是不要学国民党,不要糟蹋“人民的金钱”。
王士倬先生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新政权的自己人来谈想法的,在他的意见中,很清晰地提出了要重视规范和检验:
“今后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的航空事业,大家注重学习,集体研究为什么这样做或那样做,检讨错误改进技术。这些学习的资料,起初可以参考外国的规范,进一步我们可以修改规范。运用规范的重要阶段,就是检验工作。”
王士倬先生对国民党“无目的地教育人才”提出了严厉批评。在这里,他举了钱学森的例子。他“主张教育要有目的,有的放矢,学以致用,尤其是像航空这样专门的科学技术,不可无计划地教育人才”。他谈的是航空工业,但他的思想却超越了工业和工程技术,他对教育和人才的看法,也是非常有见地的。
1928年,王士倬先生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继续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工程管理学科,并对当时的工厂管理进行过研究,是懂得科学管理企业的人。他被王云五先生看好,被聘为研究员,借鉴欧美经验,对商务印书馆的机械管理改革进行研究,提出改革建议,在贵州大定工厂任厂长时,也是一个锐意革新的改革家。
王士倬先生是一个干过大事业的人,他在撰写这些意见时,站在国家的高度、航空工业系统的高度、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度和科学管理的高度,目光不可谓不犀利,观点不可谓不明晰,思想不可谓不超前。如果真能襟怀坦荡地认真听取这样的意见,虚心一些,真诚一些,我们会少走多少弯路啊!
王先生是一个识时务的人,他没有跟着国民党跑到台湾。从他在邵阳的表现看,他真诚地选择了跟共产党走。在当时,这无疑是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正确选择。
他是一个“政治嗅觉”极低的人
这样一个有着辉煌业绩的人,应该有一个成功的人生。但这本自传所记录的却与我们的想象完全不同。在自传中他直述解放后在汉口工业学校时,“韦英(注:时任教育科长)很开明,也很虚心好学,她对我帮助很大。她说我的政治嗅觉很低,一语道破了我之为人。”对政治缺乏敏感,在“政治挂帅、突出政治”的年代,他是“落后群体中的落后分子”。看了自传,他确实是这样一个“政治嗅觉”极低的人。
他13岁进清华留美预备班,在清华学习 7年。1918年至1925年,正值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在北京,学生运动蓬蓬勃勃。那时候,王士倬先生是着童子军装的中等科的学生。对于这些,他应该能够写出一点令后人仰慕的经历。但在王士倬先生的自传中几乎只是淡淡地写了一笔。
“1919年的 ‘五四’ 运动,我是参加了。但老实说,当时我是莫名其妙的。今天回忆往事,我仍说自己是摇旗呐喊的盲从者。”
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他没有渲染自己的激进或顺应潮流,反而流露出一丝怨怼:“五月份快到大考复习功课时期,罢课罢考,使自己对基础课程没有学好,至今回忆,犹有遗憾。微分积分的基本概念模糊,一方面要怪美国教授Heinz的教法胡闹,另一方面要怪当时的学潮。”
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人:他并不在乎人们热衷的事物。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丝毫没有从政治或从迎合某种潮流的需要出发。在读过王士倬先生自传以后,我们不能不认真地想一想,为什么一定要人们那么热衷于政治呢?有必要使人人都成为政治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