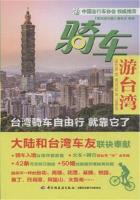小时候,我的家乡——山东省烟台市门楼水库南岸,松树茂密,杂草丛生。每年八九月份,粘菇会在雨后从烂草里钻出来,把山坡装扮得一片金黄。雨过天晴,我经常跟伙伴们拐着篓子翻山爬坡,争先恐后地采捡。半天功夫,各人就能采上满满一篓子。碰巧,还能采到榨菇、草菇,或熬或炒,味道鲜美极了,特别在当时生活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蘑菇成了招待亲友的美味佳肴。后来,我考入了大学,参加了工作,再没有孩童时采菇的体验,也就再没有尝到鲜菇的美味了。
去年春夏之交,我来到烟台对口支援的西藏聂拉木县工作。县城就挂在喜马拉雅山西坡上。在缺少新鲜蔬菜时,脑海里时常再现当年采菇吃的情景。许多同事告诉我:“快了,等到8月份,喜马拉雅山里盛产一种大蘑菇,做成汤菜,好吃极了。”馋得我直流口水。8月初,县里组织机关干部修渠那天,我正拉肚子,但考虑是头次义务劳动,就强忍疼痛上了山。走了很长一段山路,忽见淄博籍的成希峰副县长举着两个大蘑菇对我说:“老权,这是途中捡的,给你做菜吃。”我急忙接过,连声道谢:“土济济、土济济(藏语即为感谢之意),太谢谢你了。”他接着道:“你走过头了,后面老远的地方才是你们县委系统包修的水渠。”无法,我只好拄着铁锹沿渠后撤,眼里不时地瞅着水渠两旁。果然,在灌木和杂草丛生的山凹处有两个大蘑菇映入眼帘,我兴高采烈地上去用双手轻轻拔起,放在身上背的挎包里。修完水渠归来,我立即用清水洗净,做成汤菜,邀请援藏干部前来尝鲜,大家喝着菇汤,说着、赞美着,别有一番情趣。成副县长说:“东面的喜马拉雅山凹里有片桦树林,蘑菇老多了,一小时就能采到一大筐。”说得我们个个跃跃欲试,急于早一天光顾那片桦树林。
一连几个双休日,老天好像故意跟我们作对似的,总是下着绵绵细雨。终于在9月份的一个星期天,我和其他援藏干部备好干粮、挎包和竹筐,由向导带路,向东山上的桦树林进发。大家用手挣扯着灌木,艰难地爬上了陡坡,大约走了一个小时,才来到桦树林的边缘。再往里走,从外面根本见不到的山凹处,上千亩桦树林枝繁叶茂,密不透风,每走一步,都要低着头,躬着腰,用双手掰开树枝,缓慢行进;脚底下则是曲折幽深的涓涓细流,一不小心,就会弄湿鞋子。来到纵深处,如同到了原始森林。我突发奇想:要是哪国的鬼子侵入西藏,把龟孙们诱骗到此,那真成了肉包子打狗——有来无回。
我们边走边搜寻着蘑菇,可总也寻不到,倒看见了许多野兽的粪便。同行的几个县级领导拿着手枪,丝毫不敢大意,生怕大家受到豺狼、雪豹等野兽的袭击。无奈,我就蹲在草地上用双眼搜索着,折根树枝拨弄着草丛,很快发现了几个蘑菇,拿给向导看,向导说这蘑菇有毒;再找到一些蘑菇,向导又说不能食用;偶尔找到了那种食用蘑菇,却早已霉烂。向导解释说:“过去这里的蘑菇确实遍地都是,原因是藏族同胞不吃它。近几年,四川人到聂拉木县经商打工的特多,到了采菇时节,成群结队前来。而到内地学习的藏族干部、学生对蘑菇也情有独钟,在暑假纷至沓来,所以蘑菇早被他们差不多采光了。”我仍不甘心,一直搜寻到桦树林的顶端,还是一无所获。
时近中午,我来到一个小山头,上面有藏族群众用石板垒成的几个人形石柱,中央插有一根长长的木棍。我坐在人形石柱上,心想:今天采不到蘑菇,总算登了一次喜马拉雅山,领略一下大自然的风光也蛮好。放眼西眺,喜马拉雅山层层叠嶂,峰峦犬牙交错,白雪皑皑。远处的珠穆朗玛峰气势雄伟,高耸云端;近处的聂拉木县城成排,鳞次栉比;波曲河水和朋曲河水奔泻直下,声响千里;中尼公路上的汽车满载货物,来来往往;穿着花花绿绿服装的藏族姑娘和小伙子们正在山下忙碌着收割青稞,刨挖土豆。蓝天、白云、雪山、绿草、牛羊、人群、楼房、车辆,构成了一幅绝妙的图画,令我禁不住大喊:多好的金秋景色,好一派雪域风光。
我顺手拿起石板,添加在人形石柱上,尔后又拔起木棍,挥舞着,吆喝着同伴们的名字。但他们也许是太想吃蘑菇了,仍在不停地搜寻着。我只好沿着西侧的桦树林边缘,拄着木棍,拽着树枝,边下山边寻菇。一步踩空,要不是有手中的木棍支撑,非跌在乱石中无疑。“好险啊。”我自言自语着。忽然,我眼前一亮,两个大蘑菇出现在左上方。我喜上眉梢,上前一看,好大好大的蘑菇啊,菇盖比碗口还大,菇腿比锨柄粗,每个足有一斤多。采进挎包里,心中象吃了蜂蜜,甜滋滋的。我在其周围反复寻找着,果然不出所料,又捡到两个,其中一个菇盖光亮光亮的,油墨墨的,菇腿雪白雪白的,就象出生百天的娃娃,令人爱不释手。
大家在山下相聚,同伴们的竹筐内、挎包里空空的,独我有所收获。但他们的脸上却洋溢着笑容。周波副书记拿出几片爆裂散落在地的桦树皮,风趣地说:“看,这就是收获,在烟台上学的女儿,就喜欢这玩意儿。”常务副县长栾军波接着说:“今天我虽没采到蘑菇,但却在喜马拉雅山上攀登了几百米,征服了桦树林,倒也不虚此行。”说罢,大家一路欢歌笑语,平安地回到了县城。啊,喜马拉雅山,您以高大巍峨而赢得世人的敬意,您身上长出来的大蘑菇,谁说不是一种无私奉献呢。但愿您多奉献出一些,以犒赏开发建设您的人们。
(1996年《胶东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