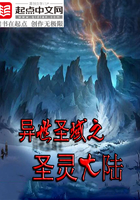刺鼻的消毒水味道窜入鼻中,我才恍惚的想起自己在哪里。有些自嘲的扯动嘴角,想来生病了都容易胡思乱想啊。
医院里很清冷,莫名的还感觉到一股儿阴冷的气息传入身体里,大抵也是因为明天要动手术的缘故,总是不安。
想来,变成这样,也是自作自受的。大学那会儿,上午没课,偷懒的不起床,连带着早饭都省了,后来时间长了,也就烙下了胃病。在家的时候,母亲总是会帮忙的调理身体,这一次长时间的住在公司附近的公寓里,饥一顿饱一顿的,闹得又疼了。
起初,还是以为胃病又犯了,就胡乱的咽了俩颗药没有在意,毕竟我也不是特别娇贵的女子。可到了下午,整个人都不对了。小腹那边非但没有舒缓些,反而更加的疼了,让我连腰都直不起来。
还是暴龙女主管看出我的不对劲才问,“你哪里不舒服啊,脸色那么差?”
“疼……”彼此脑袋里已经溢满了冷汗,说一句,都是煎熬。后来,那女主管见我不对劲,就送来了医院,一检查,竟然是急性的盲肠炎。
据说,要是再晚一点,就要通知爹妈来签病危通知的。
输液的手凉飕飕的,连带着心都有些寒意。住的病房是三人间的,隔壁床上那个姑娘好像是阑尾的手术,似乎开完了刀在修养。她和她的母亲絮絮叨叨的说着话,温暖极了。
突然间,我也想我那鼓噪额老妈了。
拿了手机拨通母亲的电话,我吸了吸鼻子,喊了声,“老妈。”
“在呢,丫头,怎么了呀?”
那头很嘈杂,隔着听筒我也听出来了,就问,“么事,就是好久没回去,想你了呗。对了,妈,你在哪里啊,那么吵?”
“我啊,和你舅妈来杭州玩了。”母亲兴致昂扬的说,“对了,丫头啊,这个星期别回来,我不在家,下个星期才回来呢。”
“知道了,你好好的玩。”
“恩,你也好好的照顾自己,别太拼命工作,妈还是养的起你的。”
“好。”
“那我就不说了,你舅妈叫我了,拜拜。”说完,就挂断了,我那一句再见卡在喉咙里,咽不下去,吐不出来的,难受的要命。不过,也不再打算回拨过去,难得的母亲有这样的心情,好似这还是她和爸爸离婚之后,第一次出去旅游。
轻微的挪动了身子,握着手机定神了,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不过从18点10分看到了18点16,却觉得有半个世纪之长。环抱着自己,将身子挪着往被窝里塞,祈求借此可以有更多的温暖。
头埋入被子里,苦笑,原来,我也是怕孤单的人。
空荡的病房,时钟滴滴答答的响着,击打在人心上。突然间,就有那么一个冲动,想打电话给他,想和他说说话。
如此想的时候,我就拨通了他的号码,而且在按键下去时还给自己找了合适的理由:无聊了。手机里嘟嘟的响了,也有那么一会儿了,就是没有人接听,一直到移动公司那标准的女声响起时,才挂断。
说不上来是什么心情,但懊恼站了大多数。因为,我猛然想起,那日他冷清的话语,是不是就表明了是没有要继续的意思呢?而我这般的主动,也真是不该了。
匆忙的按下了关机键,闭上眼睛。
医生说,明早的手术要养精蓄锐。
一夜,混混沌沌,半梦半醒的,一直到打上麻药上手术台。
半身的麻醉,人也昏昏沉沉的,但是没有完全的失去感觉。那期间,我察觉到了有人抱着我到床上,很温柔的样子。我挣扎着想要看清楚是谁,奈何眼皮实在太重,怎么也睁不开。
梦里,阳光明媚,繁花似锦。我似乎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胖乎乎的,跟在一群小男生身后拼命的追逐,很是努力的想要追赶上他们,让他们带我玩耍。
可是,早产的缘故,身体不好的我总是拖他们的后腿,久了,都不愿意带我。除了他,一个喜欢欺负我,却又不许别人欺负我的宋启勋了,也就是在那之后,我的玩伴就固定成了他,从小到大,直到他家搬迁。
迷迷糊糊的,又想了许多,等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余晖从窗外透进来,照的整个屋子都暖了起来。我看着被单上阴影,一点点的将脑袋挪了过去。
也不知是梦还是幻觉,他居然站在窗边,宋启勋居然站在了窗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