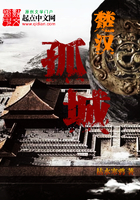今天的天色出奇阴沉,闷热的令人心浮气躁,阴森的乌云中不时有厚重雷声连声响起,偏是雨水欲落不落,闹得人浑身不自在。
柳辉焦急的在田间小路上一路小跑,匆匆往远处赶路,不时伸手抹去脸上汗水,看看前方已然不远的一处民房。
民房前有一名端着大碗杯饮茶的老妪,端坐在一个小板凳之上,老妪身形已然有些佝偻,额上皱纹深深叠叠如同道道蜿蜒山川,流淌着无数古意与岁月。她抬头看着这风雨欲来的天色与乌云下一路疾奔的叶辉,脸上带着些许阴森与不甘,颤了颤因久坐有些麻木的腿脚,起身向着柳辉迎去。
“柳老,我老婆快生了!求您搭把手!”柳辉见到老妪,大喜喊道。
老妪皱眉,起身示意自己听到了。
“天意,天意,万鬼夜行……“老妪看着远处盖天乌云,喃喃叹道,将手里的茶水一饮而尽,朝着柳辉做了个带路的手势,一同前去。
遥不可及的云端之上,彷如响应老妪的奇异话语,倏然出现了无数虚幻佝偻人影,密密麻麻匍匐在一起,缓缓前行,看得人心生寒意,直冒冷气。
轰--
在老妪和柳辉刚迈入屋内,一声巨大的轰雷声震撼天地,整个地面都仿佛颤抖了一下,外面酝酿许久暴雨顷刻剥离了天际,如同洪水般簌簌而下,毫不留情倾泻到这片大地之上。
“啊--啊--“房内传出一道道尖锐痛苦嘶叫女声,柳辉惊得面色全无,手足无措,连声催促老妪进房。
老妪皱眉,不再言语,低头叹气进房。
轰--轰--轰--
道道雷声如同洪荒巨兽嘶喊,毫不停歇的震荡回响着整片天空,震得人心头直跳,条条闪电如同巨大蟒蛇蜿蜒曲行,遮掩了大半个天空。
柳辉坐在外间,手脚冰冷,耳中丝毫听不到房外的风雨交加声,只有妻子那痛苦呻吟声如同一把石锤,一下又一下敲击在心头,敲得他脑中一片空白。
嘭-嘭-
不知老妪进了房内多久,叶辉忽然被一阵房门板剧烈叩击声惊醒。
是村民来串门?柳辉放眼窗外,视野内只有茫茫一片撕连不断的雨幕,连一米开外的树干都辨识不清,怎会有人前来,柳辉一颗心尽吊在内房动静,心想可能是被飓风吹起了什么重物石子敲击门上。
嘭-嘭-嘭-
又是三声叩门声,整齐的规律绝然不是什么石子撞击造成。
有人敲门?柳辉大奇,起身准备开门。
“不准开!!”房内老妪如同听到了世间最恐怖的声音,骇然惊叫,飞速打开了内间房门,站在内间内死死盯住那尚在颤抖的木板门。
老妪冷汗涔涔而下,手里尚自死死抓住一条给柳辉妻子接生用的布巾,嘴唇控制不住的颤抖,双目睁得如同龙眼,瞳内血丝成片,看着十分骇人。
“记住,无论谁敲门,谁叫唤,午夜十二点前都绝对不能开门!”老妪定了心神,面色严肃,对柳辉说道,又似心有余悸,斜眼望了大门一眼,叹气回身。
柳辉不敢多问,这老妪乃是方圆数十里内唯一的神婆与接生婆,在村中威望极大,向来说一是一,容不得别人忤逆。
柳辉被这一情景一惊,反倒清醒了几分,发现不知觉间,时间已然到了晚上。倒是不怪柳辉懵然,只是下午时分接踵而至的暴雨致使天色早早昏暗,心神又大半系在生产的妻子身上,倒是没有察觉时间的变化。
柳辉嘟囔了几句,想着等下房内妻子与老妪接生完毕,必然要吃点东西,也就不管房外异状,站起身来烧火起灶,弄点粥饭备着。
外面风雨越发的大了,猛烈飓风刮得老旧的窗棂颤抖着发出不负重压的吱吱声,尖锐的呼啸风声和无数暴雨敲击地面的巨大嘈杂声混杂在一起,就连房中妻子的痛苦叫声都被压低了几分。
咣!
一声如同巨大重物撞击木板的声音骤然响起,就连灶上的碗盆都震了起来,柳辉被吓得跳起,转身看去,木门尚在晃荡,门中间凸出一个奇异的弯弧,门后的碗口门栓都欲断未断,可想而知这撞击的力量绝对大得离谱。
然而没等柳辉反应过来,他竟然再次看到了这门中间的弯弧竟然就咔擦一声又弯了一分进来,像是有什么巨大东西尚在拼命的往里面挤压。
木门和门栓已然不堪重负,不住发出吱呀声,很快就要被这巨大的力量生生从中折断,而柳辉望着木门,脑中一片空白,整个后背被自己流下的冷汗浸湿。
木板门被撞击得有些弯曲,中间的门缝被撑得大了几分,而他站的角度刚好可以窥见那木缝外的动静。然而谁也不知道他究竟看到了什么东西,因为究其他活得并不长的后半生中,他再从来没提起过他今夜的经历,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也像再也没有丝毫的记忆,就连醉酒说癫话,也没有泄露过丝毫。
他只是疯了般扑了过去,用整个身子死死的抵住木门,双腿死死扎根在地上,十指扣住门栓,连指甲被木屑深深刺进都不自觉。
柳辉只想到外面的东西绝对不应是自己能看见的,那劈天盖地般的东西在暴风雨中无法用肉眼辨识,心底涌现出的无以复加的恐惧填满了自己常年劳作显得健壮的身躯,他在刹那间精神显得有些迷茫,更有些恍惚,他倏然觉得自己的五官变得异常的灵敏,能感触到自己额上与身上的冷汗顺着肌肉的纹理滑落的冰凉,喉咙里不自觉的大叫嘶喊。
“滚!滚出去!!“
啪嗒--轰!
厚实的木板门终究被那股诡异力量生生撕裂,柳辉如同遭受了山洪那般不可抗拒的巨大冲力,瞬间被击飞,轰然一声重重磕在了内室门上,连同内室门都一同砸烂,整个人都飞进了内室。
内室老妪和柳辉妻子早听见了外间的巨大动静,偏是生产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孩子大半个身躯已然半个在外,根本不敢分散心神。柳辉妻子急得眼泪止不住的横流,但潮水般的剧痛迫使她根本无法有所动作,她唯一能做到的只有死死的用牙齿咬住嘴唇,拼命让自己的呻吟哭泣声放低一点,再放低一点。
她不知道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她能想象到那个性格坚毅体格粗壮的丈夫肯定遇到了极大的麻烦,所以她尽到自己的极限,不愿给自己的丈夫再添一份担心与麻烦。
横飞而进的柳辉在内室地板上直直滑行了半个房间,她努力的偏移头部望去,看见柳辉头破血流,细小的木屑插满了他整个身躯与四肢,鲜血像漏了洞的水缸哗啦啦的流满了周围的地板,他头颅偏在了另一方向,让她看不见他丈夫那熟悉的容貌究竟如何了。
她再也遮掩不住自己心中的惊慌与恐惧--
“柳辉!!”
突如其来的恐慌和积累了不短时间的惧意充斥满了她的一切情绪,因长时间生产而失力的身躯不知从哪来生出了一股新力,她惊叫,她不停大声的叫着丈夫的名字,双手紧紧搂在一起,眼泪不要钱般流下,身体不自觉的贴紧用力。
“哇--”孩子就在如此奇特的情况下,在他妈妈因恐慌不自觉抽搐身子的情况下被挤压了出来,发出了清脆的第一声啼哭。
孩子,你终于出来了--
柳辉妻子绷紧了整天整夜夜的情绪终于在这一刻完全宣泄了出来,她痛哭流涕,双手撑在床上挪动着身躯,想起身去看看生死不知的柳辉。
她刚挪了半分位置,一阵晕眩袭上脑袋,双眼一黑,因极度绷紧的惊悸情绪瞬间转换太快,更因难产的过多失血,她刹那间挣扎的举动致使她就那么毫无预兆的昏迷了过去。
老妪露出怜惜神色,将孩子抱至柳辉妻子身边,给这对可怜母子盖上被子,也没有去看地上的柳辉,神色自若的拿手巾擦拭了下因接产而沾染上的满手鲜血,缓缓走出了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