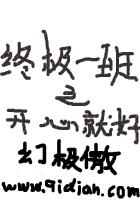却说一使者执金牌飞奔至天虞城下,姜素业亲自迎接,姜鲁门、朱达二人陪伴在侧。那使者原是熟人,是镇南将军府的亲信儿郎,姜素业是认得的。使者见过公子,施礼道:“公子在上,小人奉将军之命,执赤金之牌,前来传达军信。”
姜素业急道:“怎讲?”
使者清了清嗓子,宣读起军令:“经由国相斡旋,中都方面态度有所缓和,现急令公子素业撤走兵马,仅留原先各城池守卫即可。此事处理完毕,公子立刻回返南都,不得有误。”
姜素业如闻晴天霹雳,急追问道:“怎会如此!父亲怎会做出如此决策!”
使者也是无可奈何,道:“公子问小人,小人又哪里知道!只知国相前日星夜赶回南都,面见镇南将军,随后便有此决策,特命小人以飞鸟符箓幻化,衔着金牌送来急信。”
姜素业又惊又怒,遣返使者,与姜鲁门、朱达二人回到太守府。朱达忍不住道:“事出突然,公子宜速执行。”
“我拒不执行!”
回到府内的姜素业刚刚坐下,复又跳了起来,压低声吼道:“父亲必是受了洛中平蛊惑,才下了这个命令!”
姜鲁门一头雾水,道:“何出此言?”
姜素业便把搜到汉官仪身上蜡丸密信一事告知叔父。姜鲁门闻言大惊,道:“怎会……确定无误吗?”
姜素业气得双手在空气中乱舞,全无往日风度:“若我等把防军撤走,那压过大江的司隶军顷刻间就能进逼天虞、柜城、鹊城,守军本就不多,如何抵挡得住?天南连壁失守,赤岭以北的半国藩地便都丢了!”
身为剑豪的姜鲁门有些不知所措,接不上话,还是朱达镇定老到,只听他柔声劝道:“公子切莫太过着急,看来洛中平确实是公孙兄弟埋在将军身边的暗桩。公子现在手握虎符,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且不去管他,看他有何应对方法。”
姜素业点了点头,却不知道此时此刻另外一处地方正酝酿着一场大战。
-=-=-=-=
朴山之北,大军集结。
汉开边早早接到命令,率部与司隶南下大军会合,单骑入大营面见总指挥官洞庭王公孙浒。入了中军大帐,汉开边诚惶诚恐,但见居中坐着一人,皮肤黝黑,相貌雄阔,好似怒目金刚一般端坐,气魄摄人,不怒而威,正是洞庭王。汉开边连忙施礼道:“末将汉开边,甲胄在身,不便跪拜,还请洞庭王宽宥。”
这是武将的礼数,军营中带甲之人皆可免去跪拜之礼。
公孙浒不认识汉开边,但他对百里中正没什么好感,因此对汉开边也不会有什么好脸色。只听他朗声道:“本王听过你的姓名。辛苦你了,且在本王帐下听候差遣。”
“是,末将遵命。”汉开边头也不敢抬,退居末座,坐定下来,这才有机会抬眼观察帐内其他人士。
洞庭王右手边副座上是一员大将,五十来岁光景,两鬓已白,两道短粗眉毛,一部络腮虎须,身躯高大,坐着稳如泰山,眼光暗藏杀机,一看便知久经沙场,能征惯战。
“能坐在五王爷旁边,应是梁庆老将军了。”汉开边暗自苦笑,“也没有徐猛说的那么老嘛!”
左边坐着梁庆的次子梁弘,依旧是老样子,胡子拉碴,一头散发,外表落拓不羁却掩不住双目的炯炯有神。
“那时候无皋城外一战,梁弘便与东方独并驾齐驱,不落下风,确实是青年将才。”汉开边暗忖,“这副长相,若不是生在将门,他恐怕就成了江湖上数一数二的大侠客了。”
还有一个长相温文的男子,衣着华丽,嘴角浅笑,坐在梁弘对面。汉开边坐在他身旁,觉得眼熟,却不认识他,只能推断出他的官职在梁弘之上,因此才能坐在右首,地位仅次于洞庭王和梁庆。
“啊呀,在下来迟了。”
众人循着声音齐向帐外看去,却见张时披一袭雪白僧衣,飘然而至。
汉开边颇为吃惊,暗道:“他怎么在这?”
公孙浒见了张时,并无责备之意,反道:“先生请坐本王身侧。”
好高的待遇!
见梁庆铁青着脸,老大不快,张时是何等机敏,立即谦让道:“岂敢。在下无尺寸之功,无一官半职,怎可与王爷、梁老将军并肩而坐?愿居末座。”
公孙浒应允了他,他便悠然走到梁弘身边坐下,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正好面对着汉开边。
二人目光瞬间交会,虽无声息,却胜过万千话语。
“对了,在下刚刚见东边来了一支军,约三千人,应是东国的援军。”张时道。
果然一个小校来帐外报称:“禀告王爷,东国徐猛率军来投。”
“哦?”公孙浒道,“快请他进来。”
汉开边喜不自胜,睁大眼睛望着帐外,只见一条魁梧身影虎虎生威,大步流星,径直走了进来,站定施礼道:“王爷在上,俺是徐猛,奉东海王之命前来增援,听候王爷调遣。”
汉开边正激动不已,猛然却想起梁庆还坐在上头。果然未等公孙浒答话,梁庆便断然一声喝道:“你这逆贼,还敢来此见我!”
徐猛这才看见梁庆,吓得说不出话来,道:“俺……俺这不是……”
公孙浒不明就里,梁弘却是知道底细的,连忙起身道:“父亲且勿发怒……”
“你给老子让开!”梁庆忽然自座位上弹了起来,推开梁弘,身形如电,早扑到徐猛面前,伸手便是一掌!徐猛见他来势凶猛,不敢招架,又不能不躲,只好一个闪身堪堪躲开,嘴里求饶道:“泰山!饶了俺吧!”
听他喊自己“泰山”,梁庆更是怒上加怒,自旁边武器架上抽出一把刀来,誓要把他斩杀,惹得众人尽皆愕然。梁弘连忙飞身扑过去,扯住父亲手臂,苦劝道:“中军大帐之内怎可动刀!”
那衣着华丽的男人冷笑道:“原来是翁婿关系,倒也是奇了。”
“洛京云!”梁庆怒道,“轮不到你小子插嘴!”
洛京云不再言语,只是报以轻蔑笑容。汉开边这才悟起:“原来他便是镇东将军洛京云!这厮甚是可疑,须多加提防……”
此时洞庭王公孙浒才以洪钟般的声音喝道:“荒唐!这里是中军大帐,都给本王住手!”
梁庆虽性情猛烈,但也不敢违抗洞庭王的命令,方才实是一时冲动,此刻渐渐冷静下来,“锵”地一声收刀回鞘,仍放回武器架上,再走回自己位子上坐下。徐猛松了一口气,只听洞庭王说道:“徐将军既是东国派来的客将,且入座来,自有你立功的机会。”徐猛拜谢,此时已留意到汉开边的存在,自觉地走到他身边站定,二人久别重逢,甚是欢喜,只是甲胄在身,不好拥抱,于是徐猛一把捧起汉开边的双手,道:“原来兄弟你在这!可想死俺了!”
“自那时一别,我无时不在挂念徐兄,可惜俗务缠身,未能常写书信寄去。”汉开边亦是激动不已,握着徐猛的手不愿松开。
公孙浒见状不禁问道:“你们早就相识?”
“禀王爷,徐兄是我的恩人,又情同手足,正如自家兄弟。”汉开边回道。
公孙浒笑道:“如此甚好,诸位若能精诚团结,此战岂能不胜?”
梁庆犹自脸色铁青,不予置评,公孙浒也不好问他缘由,只好装作没事发生,话归正题:“朴山道上,白宗布下大阵,拦住我等南下之路,宜速破之,诸位将军可有想法,尽管献计。”
洛京云也不言语,一脸僵硬的浅笑,全然好似个局外人一般。还是梁弘先开口道:“今早我已亲自前去侦查,敌阵甚为严密,正面强攻恐怕难以奏效。既然先前经略王已布下秘计,还是耐心等待为好。”
公孙浒眉毛一扬,说道:“我军挟势而来,正应一鼓作气,击破敌人,难道还要在此与之相持?况且大部队耗损粮草甚巨,速战速决方为上策。”
梁弘道:“我军初到,敌军以逸待劳,仓促开战怕是我军吃亏。”
说完他便把目光投向了洛京云,希望他能表示赞同,谁料洛京云刻意避开了那道目光,神情漠然,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梁弘又看了看张时,哪知张时低头微笑,推聋作哑。公孙浒见状,便道:“区区一个白宗,怎的抵挡得了诸位名将?”
汉开边忍不住进言道:“王爷三思,敌阵布置巧妙,又牢据地利,确实不好对付。”
公孙浒看了开边一眼,道:“你虽然已是四品野战校尉,但毕竟是战场新人,怎知士气的重要性!”
这句话显然也是说给梁弘听的。在军事上,汉开边与梁弘都只能算初出茅庐的新手,而公孙浒却是在北国成长起来,自十五岁以来便常年在一线对抗外族侵略的亲王,早就身经百战,自然有资格居高临下,指点江山。
这时候徐猛忽然站出来道:“末将不才,愿作先锋,前去进攻敌营!”
徐猛声如洪钟,让公孙浒赞许地点了点头,道:“壮哉!徐将军不愧是东海王派来的猛将,果然胆气非凡,好!来人,取酒来!”
公孙浒命人取来一碗米酒,递给徐猛,道:“这碗酒是本王敬徐将军的,希望徐将军不负众望,斩下白宗的首级!”
徐猛接过碗,一饮而尽,道:“末将遵命!”
公孙浒道:“且带士卒用饭,午后进攻!诸位大将也退下准备,协助徐将军作战。”
“是。”众人齐声应答,却是各有各的语调和心思。
于是会议结束,众人解散。出了大帐,汉开边快步赶上徐猛,拉住他的衣袖,道:“徐大哥为何要冒这个险!”
徐猛道:“有仗不打,俺坐在那也是火燎般的焦躁。那些高官惜命,俺却不怕死,管教那个什么白宗知道厉害!”
汉开边急道:“那几人分明是演了一出戏,一个红脸一个白脸,激你出来请缨!大哥是客将,带的队伍损失了,对他们而言不痛不痒。”
徐猛叹了口气,道:“贤弟你有所不知,俺在东国受尽鸟气,那东海王让俺带着手下士卒还有粮饷去做买卖,俺怎生做得?俺万万没想到这天底下还有军队是可以做生意赚钱的!”
汉开边听了只有苦笑,道:“东海王一贯如此,太平盛世,他最喜欢玩这一套。”
“恁的腐化!这分明是侮辱俺嘛!”徐猛道,“俺是个粗人,你也是知道的。猛虎俺能打死几只,叫俺低买高卖,却是做不来。若是你在身边,俺便不愁此事了!现在有给俺施展拳脚的所在,俺能不上阵么!”
汉开边道:“请大哥听我一言。虽然大哥天生神力,但这敌阵非同小可,不可大意,进攻只可浅尝辄止,要懂得知难而退。”
徐猛摆摆手道:“不妨事,俺在梁家手下做了多年军官,这点事情还是懂的。俺先去安排炊饭,吃饱再说。”
看着徐猛走了,汉开边摇了摇头,忽听身后一人道:“好个汉开边,这么快便在拉拢助力,果然善于收买人心。”
汉开边回头一看,惊诧道:“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