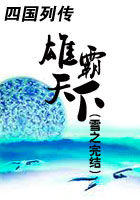可连深意都搞不清楚,就更别提破解画中奥秘了。又或许,这奥秘不是画的内容,而是画的本身。比如说,这画挂这儿,是为了遮挡什么东西!
马钰撩开画布,露出后面的墙来,毫无瑕疵。他还不死心,又拿手仔细得敲了,希望能发现密室机关之类的。
但这显然徒劳,耗费了许多时间,他确定这就是一面墙,很实在。
“前辈知道这画的秘密么?”他回身问老道,却见偌大的厅堂里,哪还有半个人影?那老道,正如他来得奇异,去得也是无声无息。
马钰不知怎的一个激灵。振奋下精神,他将注意力又移到这幅画上。他已是明白,问道仙阁的考验不那么简单,更没什么漏洞可钻,非得迎难而上不可。
他细细的观察其中每一个细节,纸张的纹理,作画的笔法,以致美妙的线条,还有玄之又玄的意境。
渐渐地,他分不清哪是现实哪是画中,亦真亦幻。他甚至觉得,只要他想,抬步就能迈入画中。
这想法太无稽,马钰一阵甩头,要把这念头甩出去。他觉得自己肯定疯了。可这念头却挥之不去,越想越觉得有道理。何况试试又怎的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
他又看了这幅画,山虽巍峨却不极高,林虽奇骏却不茂密。山腰处,一座若隐若现的道观,遗世而独立,只有一条羊肠小道与世俗相连。他又看到那首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他心中一动,鬼使神差地伸手屈指,扣动画幅,像扣动门扉。
随着扣动,耳边响起敲门声。过了会儿,“吱呀”一声响,门开,出来的是个道童。他稽首问:“道观远僻,不知道友为何而来?”
马钰这才发觉,自己已身在山中。其时似乎是深秋,气温有些低了,他这身衣服还有些冷。加之山风强劲,这么会儿功夫,他已经有些打寒颤了。
他不知道,这寒颤是冷的,还是吓的。眼前场景突然变幻,他一时间搞不清楚,这是真实还是在画中,更担心其中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但眼下再惶恐也是无用,既来之则安之,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
他见眼前这道童眉清目秀的,不像歹人。这道观又是在深山中,远离尘世,想必在这儿修行的即便不是高僧大德之类的人物也相去不远。他便想着先糊弄过去,只说是上山游玩的旅人,误入深山迷失方向,不想见到道观,便前来问询,一来问明道路,二来也是讨点吃的歇息歇息。
心中想得很好,他出口却是:“在下山野老道,听闻玉虚道人在此修行,特来拜会。”
马钰言不由衷,心中却更加害怕,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恨不得不管不顾撒丫子狂奔逃跑。可心中想着,脚下却动不了,好像身体不是自己的。
“道友来得不巧,师父他入山采药去了。”
注意到道童对自己的称呼,马钰看向自己。这才发现,自己已不是一身麻布短褐,而是一身素青色道袍。道袍剪裁简单,也没什么花纹图案装饰,但面料很好,轻薄丝滑,感觉像丝绸。
再看手脚,还算结实,但比马钰来说却瘦弱一些,毕竟这十几年的农活不是白干的。手上没拿拂尘什么的,右手手指上却带着一个扳指。这扳指手感有些奇怪。若非他看见了扳指,根本感觉不到它,想来不是凡物。
脚下穿着双薄底青色布鞋,颜色与道袍一致。但这布鞋,底子太薄,走不得远路,更走不了山路。他自忖,穿着这鞋若是走山路,脚就废了。
他越看越奇,越看心里越不平静。这桩桩件件明白无误的告诉他,这身体根本就不是他的。这也不是穿越夺舍之类,更像是有人将他的意识封印到这躯体里,就如同一个盒子,只可以如同旁观者一样的看。
那就看吧。
马钰自忖到了这地步,挣扎不挣扎的也就那样了,索性走着瞧也就是了,权当看场3D电影。
这样想着的时候,他已是问话了:“不知他什么时候回来?”
“或是两三日,或是三四日,若是遇到什么事了,一个月也是有的。”
马钰皱眉想了半晌:“我来一趟不容易。若是就这样离去了,下次就不知什么时候能来了。”他问道童:“可能让我住这儿,等你师父回来?”
“道观中只我师徒两人,如今师父入山采药,就只剩下我一人了。若是道友能住下,正好与我解闷。”道童先是一喜,继而为难:“只是道观中没有多余厢房,若是道友要住这儿,唯有跟我挤在一处了。”
马钰笑说:“这有什么的?修道之人餐风饮露都是常态,只睡觉时候挤挤,简直是神仙般的生活了。”
道童也是欣喜,让出大门:“如此,请进。”
如此在道观中住了许多天,每天只吃些豆腐青菜,和水加盐煮,和水加盐凉拌之类的,直吃得他怀念起家里吃的咸菜疙瘩,更怀念起上辈子吃过的红烧肉。
这日天降大雪。白雪压着青松似也不那么挺直了。天气冷的厉害,他与道童窝在厢房里炖豆腐青菜吃。豆腐青菜用陶釜盛着。陶釜直接放在柴火上。
炖豆腐青菜用的是山泉水,豆腐青菜也是自家种自家做,两相一激,便有淡淡的甜味。初吃有别样的美味,但也架不住顿顿吃天天吃,如今觉得也就这么回事了。现在吃,一来是填饱肚子,二来天气实在太冷,炖些东西也能暖和暖和身子。
正在吃着,便听见有人敲道观的门。
这道观名为玄青观。山名为天姥山。无论是天姥山还是玄青观,都远离市井繁华,周围也没什么村镇,鲜少有人来。今儿居然有人敲门。
马钰正自疑惑,却见道童屈指一算,高兴说:“必然是观主回来了。”
马钰面上动不了声色,心里恨不得跪下:老天开眼,这劳什子观主总算回来了。
道童将自收拾整洁,便去开门。门开,门前立着个青年。青年面白无须,额发束成一股,在根部用白绳扎进,背在后面。其余让它自然垂下,及腰,末端则用白绳收束。两鬓发更是及胸,根部用白绳束住。
整个人看起来白白净净,柔柔弱弱,看着不像观主,倒比这道童更像道童。
“观主回来得巧,”道童递过包袱。这包袱一直在这人手里,看起来没放什么东西,就是做个样子。“家里正炖着,刚开锅,正可以吃个热乎的。”
观主笑说:“呦,那我可真来得巧了。”他这一笑,看得马钰怦然心动,竟移不开眼神。
观主注意到马钰的目光,看了他一眼,回头问道童:“家里有客人?什么时候来的?”
马钰一个激灵回过神来,忍不住一阵恶寒。他虽不歧视基佬,可别人一回事,自己亲自上是另一回事。
“来了有些时候了。”
马钰这时上前稽首:“老道行礼了。”
观主也是行礼:“贫道稽首。”趁着行礼他上下打量,见这人虽自称老道,却一点都不老,身穿青色道袍,脚下是青色布鞋,头上是最常见的道髻,用青色簪子簪住。只是他皮肤很黑,黑到好像特意晒了几个小时的日光浴过来的似的。
“贫道观小人稀,不知为何而来啊。”观主笑问。
马钰却没笑,神情郑重地从袖中掏出一东西来。
观主一见面上不动声色,心中却不敢怠慢,屏息凝神眼神不敢有丝毫晃动,便见他从袖中拿出一卷画轴来:“闲得无聊,便胡画了一些,权当心意。”
观主好奇拿来,打开一看,双眼直放光:“好画!”真是好画,马钰心中更是震惊得三魂丢了两魂。这画正是问道仙阁中挂的那副。
那么问题来了:画在这儿,他在哪?马钰心里乱如麻。
且说观主看了,大笑一声“好画”,便挽起马钰胳膊:“不想道友竟有如此精湛画技,实在让贫道大开眼界。”吩咐道童去附近镇甸打些酒水,又招呼马钰进屋:“道友此来可是有什么在下能帮得上忙的,尽管说就是。”
两人自炖煮着豆腐青菜的陶釜左右坐定,此时外出打酒的道童已经回来了。他给两人斟上酒。只见酒气氤氲,竟还是热的。
“不瞒道友说,”马钰抿了口酒:“我这次来,都是为了这次量劫之祸。”
观主一听,笑容倏得一下不在,挺直身形,彬彬有礼,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势:“哦,道友是要请贫道出山?”
马钰摇头:“非也。量劫牵连甚广,牵连一点就要化为灰灰。在下与道友无冤无仇,岂会陷道友于死地?”
观主一听不是自己猜的那样,尴尬一笑:“那不知道友的意思是?”
马钰却不直说:“我请问道友,可知这次量劫之祸是因何而来?”
观主虽不知马钰到底想说什么,却依然答:“自然是人妖之别。如今妖族末而人族兴,偏偏地上妖国,天上妖庭,根本没有人族立锥之地。如此人族自然不服,自然要战。”
马钰点头表示同意:“是啊,如今人族当兴,而妖族逆天行事,便有了这次量劫之祸。其后,人族搬了妖族这片大山,必然兴盛起来。但试想若干年后,人族末而别族兴,当何如?”
观主理所当然:“那必然是另一场大战。不过人族身体乃是先天道体,别族要取代人族的地位,可不容易。”
马钰笑说:“当年妖族初兴之时,也只道妖族体质乃是万中无一,难以替代,谁会想到人族的出现?况且即便没有别族,妖族也必然不甘心,必然要有所倒算。”
观主听出点意思了,笑问:“道友想说什么?”
“纵观古来战争,无一不是种族之战,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每一次种族之战,动辄便是量劫之祸。每一次大战,环境便被大破坏一次。如今修行道上,灵气不如上古。我想上古之时的灵气,想来也不如更前时候。如此下去,想必终有一天,我等修行便要灭绝在自己手里了。”
观主越听越觉得有道理,不由得点头:“不错。只是兴衰之替,天地之理,要想阻挡可不容易。”
“何必阻挡?何不融合?”
观主一愣,看上去很感兴趣:“融合?何为融合?”
马钰却不语。观主心领神会,示意道童出去,又挥手设了禁制。
禁制成的那一刹那,马钰便觉得浑身一沉,等回过神来,眼前是那副山水画,环视四周,已回到了问道仙阁了。
他懊丧得跟什么似的。正听到关键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