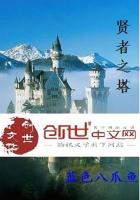“丁零零零……”
啧,人生一大苦,就是要早起,而更苦的是,早起是为了无所事事。
伸手往床边栏杆上挂篮里摸索一阵,抓到了那只正在叫唤的闹钟,恶狠狠地拍下它头顶的钮,我睁开了眼。
七点整。
转头看一眼,三个室友还没醒,睡得都挺沉,三个呼吸声平稳悠长,此起彼伏,同着闹钟嗒嗒的秒针一起,恍惚间似乎构成了某种和谐,打着连续不断的拍子。
蹑手蹑脚爬下床,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一线,果然,窗外太阳已经很大,阳光明亮而刺目,我没敢开窗,窗外很冷。入秋之后,冰城的温度就开始反了人类,太阳再大,该冷还是冷。太阳跨过赤道往南走,这之后的每一天对我而言都是煎熬:下午三点日落,凌晨三点日出,作息规律完全被打乱,更难熬的是那零下三、四十度的低温,满世界的白雪……这辈子没啥畏惧的,就是怕冷,讽刺的是,我身在冰城。
洗漱完回来,那哥仨儿依然在睡,看了看时间,七点二十五,我走过去拍了拍老王,“老王,快七点半了,起床!”又去掀了阿长和贱贱的被子。
老王睡眼惺忪地抬起头看我一眼,咂吧咂吧嘴,翻了个身,又躺了下去。贱贱艰难地爬起来,一脸生无可恋,双眼无神地扫来扫去。只有阿长一挺腰杆,弹簧一样从床上弹起,伸手抹了把脸,翻身下床。
我走回老王床前,“死胖子,再睡食堂没包子了。”
一听到吃的,老王马上睁圆了眼睛,也没见他动作,我话刚刚说完,下一秒钟他人就落地,抢了脸盆奔赴水房。
感叹一声这厮胖是胖,可也是真灵活。
我拉开包收拾课本,今天星期一,三节大课,经济法,商业银行业务经营与管理,下午还有一节选修课。作为一只大三狗,人送外号“挂科小王子”,我对上课没什么兴趣,早上的课就算了,带本小说打发打发,至于下午的选修……呵呵,吃完午饭睡个午觉醒来就到吃晚饭的时候了,选修课什么的,不是我该考虑的。
经济法课本挺厚重,懒得带了,挑挑拣拣装了本小说进包里。
收拾完书包,好吧其实也没怎么收拾,就背了本小说而已。我点上枝烟去楼道等那哥三儿吃早饭。
不喜欢自己一个人吃饭,有点儿孤独,容易让心情不好。
等他们洗完脸穿上衣服争着使完镜子一个个捯饬得人模狗样的,下楼吃饭。去回民餐厅要了三个煮鸡蛋一碗粥,吃到一半听到餐厅阿姨大骂刚离开的几个大一小朋友吃完饭竟然不把餐具送到回收处。那阿姨骂一声然后抬头对路过的同学笑一下,打个招呼,骂一声又对路过的另一个同学笑一下……满布皱纹的老脸上愤怒与笑容飞快地替换,看起来莫名惊悚。
经济法老师姓郝,长得本本分分,一开口,却并不是那么好。他公然在课堂上质疑社会主义,对其表示怀疑和不信任,大谈丑陋的中国人,嗯,学院就是思想碰撞的地方,即使他拾人牙慧,有些观念也蛮乐意接受,可惜他觉得人生应该追求物质至上,成功的标准即是手握大把钞票,对此,我就笑笑,作为人师,他的境界还是低了不止一点半点。
听他讲了会儿,觉得甚没意思,我掏出了小说。
后来的课过得就挺快了。我父亲就是银行的,我对这个行业深恶痛绝,恨不能炸了这世上每一间银行,所以,商业银行课程我注定了要挂科的,于是我连老师是男是女都没兴趣抬头看。
吃午饭时候有幸目睹食堂大妈使用了颠勺神技,只觉三生有幸。满满一勺红烧肉,大妈手腕一抖,落进我盘子里的就只有三块儿,嗯,破了记录了,昨天倒是有四块儿,虽然有两块是姜。
吃完饭就应该睡觉,一觉醒来,天已尽黑。没开窗,但能听到冷风呼啸,像是哀怨的鬼哭。订了份外卖,外卖小哥打电话叫我下楼取餐的时候打了个喷嚏,很响亮。
吃完晚饭,盯着窗外发呆,寝室在六楼,宿舍楼最高层,从窗户看出去,楼下人不小,天上星星不亮,尴尬的楼层,不算矮,也不高。
听了会儿歌,连打游戏的兴趣都没有,八点半,爬上床睡觉。
天气一凉,就容易疲惫,即使什么都不做,也会累得什么都做不了。
半夜十二点的时候醒过来,被冻醒的,暖气得过几天才开始供应,一年之中,北方的寒冷就是在这几天里纤毫毕现。
突然想起还没有洗脚呢,想要起身去打盆热水泡一泡,却发现离了被窝很冷,拽了拽被子把露出的半条腿盖好,算了,都睡了一半了,还洗个毛啊,继续睡。
“丁零零零……”
唉,每天听到闹钟响,莫名其妙地就火大,睡不够简直比砍头更让人难受。
拍灭闹钟,坐起身来,七点钟,转头看了一眼,三个室友还没醒,睡得都挺沉,三个呼吸声平稳悠长,此起彼伏,跟闹钟嗒嗒的声音缠绕在一起,成了一种莫名的和谐,像是在连绵不断地打着拍子。
我皱了下眉,这场景,看着熟悉。
下床把窗帘拉开一线,窗外太阳已经很大,阳光明亮而刺人眼。
等等,为什么只拉开一条缝?我给它全拉开!
手伸过去,又缩了回来,算了,那哥三儿还没醒,一拉窗帘太阳一照得嚎出来。
我自己驳斥着自己,心底突然间有了种莫名其妙的感觉,空空的,有一丝阴冷,像是恐惧,这大早上的在宿舍,我能恐惧什么?
也罢,不拉窗帘,那开个窗呗,吞吐了一晚的浑浊空气得换换。
手伸过去,又缩了回来,算了,开窗冷风一吹,那哥三儿嚎得更起劲了。
我突然间很害怕。
我本是脑袋里想起手上早就开始行动那种人,很少会伸出手还缩了回来,我明明想拉开窗帘打开窗的,可是又自己阻止了自己,这很奇怪。
大概是没睡醒,脑子有些乱,我需要冷静冷静。端了盆去水房,用凉水洗了把脸。
心底那抹害怕仍旧存在着,我知道我怕什么,那只需要一个动作就能证明,我强迫自己相信这只是没睡醒脑袋不清楚。
可是实际上我也知道此刻我无比清醒的。
回来后,我看一眼时间,七点二十五。
果然很熟悉。
听着室友的呼吸声和闹钟秒针走动声,我心里的恐惧被放大了,我用拇指挡住了手机屏幕时间显示的日期部分,我知道,日期就是答案。今天一早起来就不对劲,眼前的一切跟昨天发生过的太像,像得让人害怕。
我一点一点地挪开拇指,让出了日期。
我深吸一口气,忍不住骂了一句我能想到的最难听的脏话。
十月十二日。
星期一。
昨天就是十二号!我一大早起来那种奇怪的熟悉的感觉,是因为我昨天过过今天?
奇幻,以为这是拍电影呢。
我撇了撇嘴。
走到老王床前拍了拍他,“老王,快七点半了,起床!”
等等!我为什么要去叫老王起床?
我又走过去掀开了阿长和贱贱的被子。
这……我昨天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做过?
老王睡眼惺忪地抬头看了我一眼,咂吧咂吧嘴翻个身继续睡。贱贱艰难地坐起身,一双眼无神地到处扫,一张脸上大写着生无可恋。阿长一拧腰从床上弹起,抹了把脸下地。
看着眼前这一幕,我咽了口口水。
据说人们会觉得眼前的事情熟悉,像是梦里经历过,这是人大脑产生的幻想。那大多是偶尔的场景而已,但我现在这是什么?我昨天已经过过一个星期一,我能记得昨天经历的细节,现在我又在重新经历昨天。我敢打赌这不是梦境和现实重叠产生的熟悉,绝不是!我敢拿命保证不是。
我这是又在过昨天?
我走到老王面前,“死胖子,再睡食堂没包子了。”我知道下一秒他就要睁眼落地,拎起脸盆跑水房。
果然,老王睁开眼,麻溜儿地下了床,抓起脸盆去洗漱,那动作,敏捷得不像是个胖子。
我认命了。
出门点起一枝烟。
从一早上开始就奇怪,我昨天听到他们的呼吸就是那样子的,我本来想把窗帘开大点,可是只拉开了一线,我昨天就是只开了一线。我想开窗,但没有,我昨天就没开。我自己阻止了自己,可是我是那种手动得比脑子转得快得多的人。我竟然在过昨天?
见了鬼了,我喷出一团白烟,烟气升腾,蹿过眼睛,给我呛出了眼泪。
推门回去,我问阿长今天星期几。
“星期一,三节课,上午两节必修,下午选修。”
“哦……”
等他们收拾完,下楼,去回民餐厅,要了三个煮鸡蛋一碗粥,吃到一半,食堂阿姨大骂几个大一学生吃完饭不收拾餐具。有学生经过阿姨,同她打招呼,于是阿姨骂一声抬头对经过的学生笑一下,骂一声又笑一下……布满皱纹的脸上,愤怒和笑容交替出现。
我摇了摇头,强迫自己冷静,别去看她,吃完鸡蛋,却喝不下粥,剩了半碗全倒了,走出餐厅大门,隐约听见阿姨大声批评我浪费粮食。
经济法老师宣扬拜金,批判社会主义。
仍旧没注意商业银行老师,看小说入了迷,抬起头时候就下课了。
午饭时候食堂阿姨颠了个勺给了我三坨肉,本来满满一勺怎么说得有六、七块的样子。
睡完午觉天就黑了,外卖小哥叫我下楼取餐,挂电话前打了个喷嚏,很响亮。
吃完饭,什么都懒得做,看着窗外发呆,听了会儿歌,爬上床。
半夜十二点醒来,拽了拽被子盖住腿,没洗脸没洗脚,懒得下床了……
“丁零零零零……”
按灭闹钟,七点整,坐起身。
环顾寝室,他们三个没醒,睡得都挺沉,三个呼吸声平稳悠长,此起彼伏,同闹钟嗒嗒的秒针一起,恍惚间构成了某种和谐,像打着连续不断的拍子。
我咽了口口水,可是喉咙还是很干涩。
拿过手机,拇指死死按着日期的位置,我盯着拇指指甲,喘息得很沉重。
一点一点地挪开手指头。
先是看到了月份是“10”,又看到了“1”,紧跟着后边是“2”。
“10月12日”
星期一。
我盯着这日期看了一会,什么都不想想了。
爬下床,走到窗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