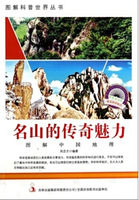希普顿大娘是约克郡那利斯镇的聪明的妇人,生于1488年左右。她的母亲,阿格瑟·松塞尔,十几岁就成了孤儿,不得不自己养活自己。究竟谁使得阿格瑟怀上尤俄苏拉这个孩子,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成了希普顿大娘。有一种说法认为那位神秘的父亲是一位高级牧师,而且可以确信男修道院院长贝沃利·敏斯特亲自去给这个婴儿洗礼,并且在以后的许多年一直照顾着她。另外一些关于希普顿大娘在娘胎及幼儿期间的说法认为,她的父亲是一贵族,一位旅行骑士,甚至是一位浪漫抒情诗人,当他经过那利斯镇时遇见了阿格瑟。
有一种说法是,阿格瑟把两岁的尤俄苏拉交给了当地一位护士照管,然后去了一个修女会。还有一种说法,当阿格瑟死去的时候,那位护士怜悯这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在那位护士照管下,尤俄苏拉婴儿时期最持久的传说之一是,她和她的摇篮不知怎的进入了一处村舍的烟囱,并挂在那里,人们看不出有什么方式可以支持它。
这类故事给这神秘的谣传添枝加叶,即她的神秘的不为人知的父亲是一位魔鬼,甚至也许是明亮之星。
具有特别意义的是给她选了尤俄苏拉这个名字,它的意思是熊。和几个古老的英国家族一样,传说中的阿瑟王与古代神秘的熊部落有关。尤俄苏拉的父亲是那个神秘的部落成员吗?是不是受了阿瑟王的唆使,贝沃利·敏斯特才扮演了远距离的但却有效的监护人的角色来保护年幼的尤俄苏拉呢?实际上,是不是男修道院院长应不在现场的父亲的特别请求,不仅走了九十千米给这个婴儿洗礼,而且还告诉了阿格瑟孩子的父亲对他们新出生的女儿选择了什么名字?男修道院院长会不会也是一个熊部落的成员。
尤俄苏拉被送到那利斯地区的一所学校,在那儿,她的关节炎成了其他孩子们的笑柄。她的关节炎也许是她幼儿时在尼德河边一处潮湿的洞穴里生活的结果,阿格瑟曾在这儿避过难。尽管在学校里学生们的态度不友善,但是尤俄苏拉与老师们相处得很好,并且她证明了自己是非常聪明的。她还有非同寻常的与鸟类和动物交流的天才。
在二十四岁时,她遇到了托比·希普顿,他是一位好心肠的木匠。尽管她身体上的畸形使她的同辈们在学校里嘲笑她,他还是非常高兴地娶了她。自从她结婚时起,她就被人们称为希普顿大娘。
她的预言和格言的最早的记录之一好像是由琼·沃勒编辑的,此人在1561年94岁时去世,同年希普顿大娘也去世了。希普顿大娘事先准确预言了她自身的死亡,她静静地准备着,然后安静地躺在她的床上,等待着她预言的结果。
希普顿大娘预言的一些最早版本出版于1641年、1684年和1686年。这些出版物是调查者调查像她这样事情的一种重要因素。研究经常揭示,所谓的“令人迷惑的预言”和“奇怪的先知片段”,实际上是由其他人在事情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所写的,并且被更准确地描写成被歪曲了与年代不符的历史,而不是预言。
希普顿大娘的预言通常是押韵的,就像诺查丹玛斯的那些令人费解的四行诗歌一样,并且两者的意思常常被符号化和隐匿起来。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对联:
母牛骑上公牛背之时,
是牧师当心脑袋之日。
注释者巧妙地暗示,母牛是享利八世,因为这是他的盾牌标志之一,公牛是安·伯利恩,伯利恩还可拼成公牛奥艾恩。她的父亲在其盾牌标志上有的一个黑色的公牛头。他们结婚不久,亨利拆除了神庙和其他宗教房屋,并且怂恿对许多牧师进行刁难和迫害。
更为众所周知的是希普顿大娘的关于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统治的预言:
执政多年的一位少女王后,
会成为英格兰好战的熊王。
在同一时期,她还预言了德雷克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西方独裁者的木马,
将被德雷克军队击垮。
她最著名的两个预言是关于黑死病与伦敦大火的。她写道:
得意扬扬的死神穿过伦敦
人们在房顶上离去……
在大火造成的混乱和恐慌期间,人们的确爬上房顶去看火势朝哪个方向上烧,塞缪尔·佩皮斯在1666年10月20日的日记里记录的是关于杰利米·史密斯先生的事。佩皮斯写道:
他说,当传来伦敦着火的消息时,他正在“王子”号船上;整个“王子”号所说的是,现在,希普顿的预言出现了。
同佩皮拓日记中所记载的一样,虽然历史上某些清楚事情平息了对希普顿预言的反对意见,即希普顿的所谓的预言是在事件之后所写的,然而这并没有克服对预言上的模棱两可的争论——如果泰晤士河泛滥成灾,人们很可能由于一次巨大的洪水而爬上房顶,这种情况也许会被认为与希普顿的令人费解的词语所吻合。这种有特点的模棱两可的话,自从最早的时代起,已经是预言的一种特色。最典型的例子是为里达的克罗伊斯做的预报,当时他问特尔斐神谕:如果他进攻波斯人将发生什么事情。克罗伊斯被告知“一个伟大的帝国将会倾覆”。他高兴地断定这意味着他会获胜,克罗伊斯发动了对波斯人的强大攻势。然而,倾覆的伟大帝国恰恰是他的。
希普顿大娘十分确切的预言之一,与大主教沃尔西的命运有关,他曾发誓,在他抵达约克时他要把她烧死在柱子上。她曾轻蔑地称他为“屠夫的孩子”(沃尔西的父亲是伊普斯维奇的屠夫)及“戴着主教冠的孔雀”。当得知沃尔西的意图时,她大笑道,他会看见约克的,但永远不会进入到那里。到达卡吾德城堡后,他爬上塔楼,观察了这座城市。那天夜里,当沃尔西在卡吾德举行庆祝宴会时,诺森伯兰郡的伯爵来了,他根据亨利八世国王的命令逮捕了他并把他带往伦敦,以接受叛国罪的审判。这是亨利统治时期的一种经历,它几乎总是以与塔上的刽子手的简短会面而结束!比起大多数对暴躁的国王感到愤慨的那些人来说,沃尔西还算比较幸运,他在解往伦敦的途中自然死亡。
她应验的另一个悲剧预言是对约克市市长大人的警告:
当有一位市长大人住在约克敏斯特院的时候,他要当心被谋刺……
一位住处在敏斯特院的约克市市长大人,一天夜里,受到小偷们的致命谋刺。
在阿根廷,巴塔哥尼亚的威尔士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努力保存着少量的希普顿传统格言。一些研究者,包括大卫·陶尔森,认为她在下面的几行预言可能指的是福克兰群岛战争:
从此之后,
我们的土地将由两位女人统治。
我们的孩子将与
西班牙的孩子战斗
此时,将会流血,
但孩子不会倒下。
那时英国是在玛格丽特·撒切尔和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的统治下。英国的“孩子”可能指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的“西班牙的孩子”试图得到它,双方都死去了许多人。
虽然就她的一些最有趣的预言的日期存有某些争论,人们怀疑这些预言为事件发生以后被编写进的东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她预言了汽车、火车在山间穿行,她想到了眨眼之间环绕世界飞行,那是因特网的一个绝妙音符、电子邮件服务和全世界网络,想想看,在因特网出现500年以前,她就写下了!
希普顿大娘的预言提出了不仅对学院神学家、玄学家及哲学家非常重要的问题,对我们大家也一样。首先,如果预言者能瞥见将来,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将来已经存在于一种不能改变的状态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没有自由意志及自主性。正如我们不能控制行星或电子的运动那样,我们天真地认为我们自己的选择和决定是我们控制不了的。如果我们不能做出选择,那么道德和伦理就像自由意志一样是死的。如果“撕人魔”杰克在白礼拜堂的可怕表现全是他出生前就命里注定的话,那么,“撕人魔”杰克就不能因为是“撕人魔”杰克而受到责备。百万富翁、奥斯卡及诺贝尔奖金得主就不配得到感谢和祝贺,因为超越他们控制的某种力量给了他们天才,并且打开了他们必然成功的道路。如果将来已经被确定,那么,自从世界开始起,总统和总理们没有赢得一次选举,因为这全为他们定好了。世界上最伟大及最热诚的恋人们从没有互相感觉到任何自由的、真诚的、自发的感情,因为在他们出世之前,这全为他们制定出来了……等等,等等……这是对人类所有努力作出的绝望的、宿命论的嘲笑,并且剥夺了生命中最后的那么一点意义……因此,必须有另一种假设……
查尔斯·狄更斯在《圣诞颂歌》书中对此做了描述。
看见还未到来的圣诞节中各种不受欢迎的景象之后,他绝望地问道,它们能否会被避开,灵魂向他保证能的,所有的事物都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对它不采取行动,斯克鲁奇看到的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情的影子。换句话说,当时被斯克鲁奇看见的极有可能是会出现的事物的迹象,它是基于目前数据的推断而对未来做出的最合理的预测。
那好像是希普顿大娘看见的东西。当然,它提出了另一种惊人的可能性,即那些可替换的现实的确存在于某个地方……只是我们没有走在那条特别的靠经验走过的道路上。当预言家看见并且听到还没有来临的事物时,他们也许正在考虑另一种抉择,实际上别的地方经历着这种抉择……或者预言家们也许正在看永远不离开画板的未来的朦胧蓝图。
像埃比尼泽·斯克鲁奇一样,我们对未来不随人意的可能情况的“预见性的”感觉,应当使我们成为既不是宿命论者,也不是悲观论者,而是能动的决定论者。对于超自然的不受欢迎的未来景象的幻影,最佳的反应就是拼命工作,以避免它的来临。正像莎士比亚在《裘力斯·凯撒》中说的:“错误不在我们的星球中,而是在我们自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