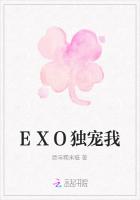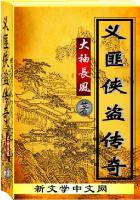莫无为躺在村前小河的石板上,闭着眼睛,思念着明天。偏偏,此时的莫大却来打扰他的美梦。
“婊子。”莫无为欢笑地骂着莫大。
打骂成了他们之间的另一种交流方式,在打骂之间他们似乎才更感到亲昵。
那在海边所激发的诗情所体现出的一种优雅的表现,在乡土的气息中消失了,或许这里才体现出最真实的东西。然而,在莫无为的心里却是存在着那样一块纯净的土地。
“好嫩的皮肤,比王家的寡妇的还要好呢?”莫大再次伸手想要触摸莫无为。
对于这样的对比,莫无为感到是对他的一种轻蔑。
莫大是个从不愿意学习的人,他的社会经验远比从书本上学来得丰富。或许莫大对女体最初的向往,也是来源于王家寡妇的肌体诱惑。
王家寡妇再给孩子喂奶的时候,村里的少年以莫大为首,总围在她的周围,像在瞻仰伟大领袖的仪容般你拥我挤的。
少年的目光紧盯着那怀中的婴儿,无比的羡慕。
想吃吗?王家寡妇有时会大笑着这样故意调侃他们。
他们有的便使劲地点头,一边的莫大一个巴掌就狠狠打在他们的头上。
他们看了一眼莫大,摸着脑袋便不做声了。
回家吃你娘的去,王家寡妇大笑了起来,有时眼角总会笑出泪来。
那泪中的意味,是村里少年不能理解的。
村里欢笑的少年被一哄而散,他们往往并不注意在角落里的一个莫无为,他同样渴求的目光却萎缩得找不到目标。
莫大总喜欢爬上王寡妇家的墙头,偷看她洗澡。
莫无为迅速地穿上了尚未晾干的上衣,这上衣仿佛一只无比巨大的手,把他的肌体所散发出的带着青春气息的美完全地遮掩。
身体的特征告诉莫无为,他并不是女人,却同样追逐着自由,那颗追求自由的心,却在中途坠落。
“婊子。”莫无为又骂了句,他感觉左脸的温度足以让整个池水瞬间的沸腾。
欲望在身体里蔓延,转化成一种温度灼烧着肌肤,吱吱作响像烤串上的肉质散发出的香。
“你像圣女一样纯洁,再也无法骂出更加恶毒的话了,对,我就是婊子,我就是恶魔,我就是犹大,罪恶的门徒。”莫大连珠的话语,让莫无为感到了一种亲近感。
正是这样的一种亲切感让他们走得很近,让莫无为被莫大的粗俗真实所包裹着,莫无为所真正想要追求的文明优雅诗情画意的心也无法绽放。
圣女和婊子犹如一对住在对门的姐妹,她们都难以割舍对方,正如莫无为和莫大一样。
莫大又躺了下去,吸着烟,久久地陶醉着。
莫无为凝望着河岸随风摇曳的柳枝,那一棵棵粗壮的柳树的枝干像莫大健壮的身躯般,招揽着过往的目光。不管人们欣赏它的目光是多么的热烈与多情,它依旧残酷的把岁月把记忆摇曳成为昨天。
有时,莫无为总在想,他所经历的苦难,比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还要多一些,至少耶稣拥有在马厩里享受爱的幸福时光,即便钉在了十字架上,十字架的血迹未干,他已经在第三天复活了。而莫无为的心却永远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从不幻想着他也有复活的那个日子。
莫大屈肘而躺着,那裸露的肌肉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
久久地,莫无为就这样坐在莫大的身边,注视着石板上这鲜活的肉体,借着他所散发出的力量感来驱赶内心的懦弱。
莫大坐起了身,又摸出了一支卷烟,卷烟的烟丝撒落在石板上,他轻轻地把烟纸摊平,把散落的烟丝一点点地放到纸上,然后慢慢的卷起,用唾液把纸缝粘合。这一套的工序是那么的熟练。莫大摸出了压扁的柴盒,抽了一支火柴,用力的划了一下,火柴头带着微弱的火星断裂了,又划了一支,燃烧的火柴又被风吹灭。
“妈的,什么破玩意。”莫大急了,骂了句,把卷烟从嘴唇上拿了下来。
莫无为一把夺过火柴,挡着风给他点了火。
“你爸,不打你?”莫无为问了句。
“不偷他的烟都经常打,妈的,想想就来气。”莫大愤愤的说,狠狠地吸着烟。
莫大笑得有几分男人的柔情,更多的是有几分真诚。莫无为无数次被这样的他所认为的真诚所打动,从而忘却有种火燎的心痛。每每深夜来临时,那些被暂时隐藏的东西又像万千蚂蚁般爬食着,爬食着他那颗已经被钉得千疮百孔的残缺的心。
“做梦了这几天?”莫大神秘的问莫无为。
“天天做梦。”
“梦见女人了没有,寺庙中的那个?”
“没有。”
莫大听到这样的回答,有点失望的低着头。
莫无为似乎并不愿意提这样的话题,因为那身影太过模糊,即便那个笑容也不能清晰地呈现那个女子的全貌。
莫无为随后又躺了下去,阳光洒在他白嫩的脸庞,有点微微的热,莫大忙拿着一件衬衫盖在了他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