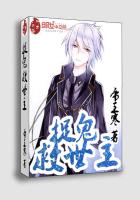我看到那口牙齿,脑袋都要炸开了!
我和那戏子就这样隔着块地对望着,身子动不了,那女人也没动作。仿佛时间停滞了。
不一会,那女子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了,两颊的肌肉松弛下来却没有复原,全都耷拉在脸上,像只哈巴狗。然后她慢慢的向我走来了。
与其说是走,不如说飘。她穿过草地的时候居然没有发出半点声响。她瓢上了小路,离我越来越近,容貌也看得更加清晰。
原本那张美丽的脸,现在反而给我凃增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因为她的脸并不完整!就如同一张拼图,我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她脸上的裂纹,如同龟裂的土地一般!她下巴明显缺了一块,显得格外骇人。
我大骂自己瞎了狗眼,之前居然还觉得她漂亮。不过我也纳闷,都这时候怎么脑子还这么清醒?居然还有工夫想这些事。
仅仅几秒的时间,碎脸戏子就已经来到我跟前,她似乎不急着要我的小命,一人一鬼就这么面对面站着,貌似相安无事。
我以为会有个痛快的,可现在这情况,好像是这女鬼是想猫玩老鼠一样的把我弄死。
怎么办?跑不了,又死不了,还得看着这张烂脸。
“妈的,老子死猪不怕开水烫!反正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我心里这样想着。
这时,女人居然微微张开了嘴,她嘴角慢慢裂开,脸颊上便有很多碎片掉了下来,嘴角的裂痕一直蔓延到耳根,“咔嘣”一声,一条黑线像蛇一样又蔓延到了额头。
我尿都快吓出来了,不一会那张脸就已经支离破碎。就在那它碎得只剩下一只眼睛的时候,女鬼猛地推了我一把,我像根木头似的,硬邦邦的就向后倒去!
我心头一凉啊,暗骂道:“原来要我当替死鬼啊——”我身后就是黄泥塘了。
清脆的落水声在他脑中环绕着,随之而来的便是刺骨的寒冷。但在我快要失去意识的时候,一个幽怨的声音出现在我脑海里——
求求你,帮帮我。
——————
“青哥!青哥!”我突然恢复了意识,连着吸了几口大气,躺在床上差点没闭过去。
刚睁开眼,就看到了孙伟那张长满麻子的脸。
“没死?!”我全身一哆嗦,原来身子已经被水倒得湿透了,或许也是我的冷汗吧。
我坐起来立马扇了自己一耳光——哎呦!还疼!哈哈!真自己没死啊!
孙伟长舒一口气,说““老天爷!你终于醒了,刚才我一直敲门,可偏偏没听见你动静。我怕你出事,便把门撞开了,见你板在床上跟个死尸似的,脸上青一会红一会,以为你鬼压床了。扇了你好几个大耳巴子都没用哦!多亏了这一盆水啊!”
孙伟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刚才看是吓的不轻。我仰天一笑,说:“老子中气足,哪个鬼敢压我?”我用力拍了拍孙伟肩膀,看来自己是做噩梦,还好他来的及时啊。
可我不禁打了个寒战,要说是梦的话,这是我唯一一个从头到尾记得清清楚楚的梦了,
到现在那戏子的脸还在我脑海中浮现,每一个场景我都能回忆起来。
甩了甩头,我努力不去想它,这次“历险”就让它过去吧。
“诶?青哥,你脸这怎么回事啊?”孙伟说着指了指自己脸颊。我一摸,右边正脸颊隐隐作痛。
我忽然全身一抖,“娘的,这不是昨晚,我掐自己的地方嘛!”孙伟见我脸色突然变了,赶忙追问起来。
我故作镇定的摆了摆手,“没事,没事,昨天不小心磕的。”我干咳了两声,想掩过去。
“你没事就好,今天你还得去一趟的。”他说。我讪笑脱了汗衫,说:“唉——村里什么事有我不要去的啊,你说吧。”孙伟点了点头,只说了一句话。
但这一句话我听了差点背过气去。“张建军死啦。”
我脑袋里“嗡”的一响,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死了?怎么可能?!不是在医院嘛!医生没救活他?”
“不,医生们抢救很成功,昨天下午建军就脱离了生命危险,”
我急了,“那怎么还死了?!那些个老麻批打了一晚麻将啊?!”
我一直对张建军住院的事感到内疚,我要不叫他来,这孩子现在还好好的。可如今人死了,这——
孙伟没说话,眼神飘忽不定,我没见他有过这样的表情。片刻后,他咽了口唾沫,声音微弱的说:“建军不是死在医院.而是淹死在黄泥塘。”
冰冷的恐惧感从我心里蔓延到了全身。孙伟大概的说了事情状况,但我根本听不进去。
今天一大早,医院护士去查房。发现张建军所在的病房里,只剩下当陪护的张自立,病床上只有一床被子。当下医院发动了所有能走的人去寻找孩子的踪影。
连附近的京竹村都找遍了,后来居然是在黄泥塘发现的张建军!而更邪的是,张建军的尸体居然正面朝上的漂浮在黄泥塘的正中央!捞上来的时候,人早就没气了,脸上如同上了层石灰一样,但那双眼睛,无论人们怎么盖,就是闭不上。
他爹妈知道后,是被人搀扶着抬到黄泥塘的,在儿子尸体旁是哭得死去活来,喊得昏天暗地。大家都很同情张家的遭遇,两个儿子就这么没了,这两天村里竟是出了两起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
他爹妈硬说是落尸鬼(当地方言——即水鬼)把儿子魂勾去了,儿子才会死不瞑目,必须请道士到这来做法,把儿子魂招回来,不然他们也不配做这父母。
听完这些之后,我眼前一阵发黑啊。连续死了两个小孩,而且同样是淹死黄泥塘。这可不是小事啊,万一上头县里问下话来,该怎麽解释?
告诉领导这黄泥塘里住着只落尸鬼?那明天我就能卷铺盖走人了。
李俊、张建军死的不明不白,就用鬼神来搪塞这一切?未免也太不负责任了。但也不能引起村民们的恐慌啊,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一琢磨,穿起衣服,关上门就和孙伟就打算往村长家去。
我家是在山塘村三沙围子,离村长家不远。走在路上孙伟细声细气的问我:“青哥,咱们得一起去趟李自立家吧?这孩子的死多少和我们有些关系,不去看看不像个样啊。”
我犹豫了会,孙伟这么一说,心里更难受了。无奈的点点头,只好和孙伟先改道去张自立家。
张自立家在黄泥塘东边,还得穿过一片茶树林。今天天气不错,太阳晒得人暖洋洋的,但那两个孩子已经看不到了。
和意料之中的一样,他们夫妻俩都悲痛欲绝,张自立什么也不说,眼睛里布满血丝,蹲在大门口一个劲的抽旱烟。他老婆眼泪都已经流干了,但嘴里还念叨着:“这是命,这是命。”
周围的邻里都过来安慰他们。本来就不大的堂屋,显得更拥挤了。我觉得自己该说几句的,但就是开不了口。只好和孙伟干站在那。
“法事是什么时候?”我问孙伟。
“好像是今天晚上吧?说是时间晚了不行,建军的魂魄就会散的。刚刚那人还在说呢,你没听见?”我看了看他,“今晚一起去黄泥塘吧。”孙伟点了点头。然后两人在张家堂屋的角落里缩了一下午——
我们回家吃了晚饭,两人闲聊了会就抄小路赶往黄泥塘。居然还晚了点,法事比预期的要早,已经要开始了。
我们三步并作两步走,急急忙忙跑到黄泥塘边。今晚明月高挂,四周亮堂堂的,手电什么的都用不上。做法用的灵台就摆在小山包下的红薯地中。
那里早已聚集了不少村民,尽是来看热闹的。虽说晚上到这死人的地方来有些骇人,但乡下不就是这样嘛。
我和孙伟得退到山上一点,才勉强看得到人群中心的情况——只见一个身着麻色上衣的老道士站在灵台前,他就是今晚主坛的道士了。这老头很普通,没什么特别的,正坐在灵台前的蒲团上打坐。
我对着孙伟小声说道:“这种人也能捉鬼招魂?穿的都不专业嘛。”孙伟只是笑笑,什么也没说。村民们看那人的眼神中,都流露出敬重的神色。我不禁感慨啊,“这有什么好崇拜的?迷信误人啊!”
这时道长旁边一个大概十五六岁的少年发话了,“麻烦大家让一让,刘师公要做法了!!”
“师公”是本地人对道士统一称呼。村民们一听,人群立刻往后退了一两米,顿时变得鸦雀无声,眼睛都死死的盯着那个道士。
刘师公这才缓缓地张开了眼,他扫视了人群一圈后,便不紧不慢的站了起来,走到法坛前,深吸了一口气。他右手放在胸前掐了个手印,口中念念有词。接着又从桌上拿起一张画了符的黄纸在蜡烛上点燃,然后左手在空中画符。
众人正看得出神,谁知他突然大喝一声,“刷”的一下抽出灵台边刻满咒文的桃木剑,又串上一张黄符舞了几下,又是一通咒语。
我叹了口气,这些套路我已经了如指掌了,“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谁都会念。要是给我一套法器,我也能骗人钱的。
人群里似乎只有我注意力没放在刘师公身上。每个人都看得津津有味。
“叮铃铃——”刘师公已经摇起了招魂铃。只见他一手摇着铃,一手提着桃木剑,脚踏七星步,绕着法坛转圈。仪式已经进行到最关键阶段——招魂。
人有三魂七魄,按常理来说,人去了之后,三魂各奔东西,生命就此终结,七魄也随着肉身消散了。
但要是死的不明不白,或被冤鬼拉了当替身,死人的七魄就不会聚在肉身里。可不回来是不行的,所以就得招。这是农村的说法。
我见过几种不同的招法。但请道士作法被誉为最有效的,也是最有排场的。
刘师公还在摇着招魂铃,这玩意得摇多久就看那孩子魂魄的反应。
这铃声太清脆了,让我不由得想起了梦里的“猛鬼戏班”,但我也只能皱着眉头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