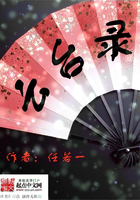怜光府,府衙。
自街口向府衙看去,大门前筑红色女儿墙,两侧八字墙各镶石碑四通,上书《太祖实训》或《大郜》等戒民之言。府衙仪门面阔三间,进深二间,侧檐木勾卷棚,顶上匾额书四个硕大金字:怜光府衙。自仪门而进便是大堂,中设公案,两侧是“肃静”“回避”等仪仗,公案后是江牙山海图,图上顶着“明镜高悬”四个字,威武赫赫;堂前竖石坊,一副对联赫然在目: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大堂往里进,过了寅恭门,便是二堂,也称为退思堂。
出退思堂向后过穿阁,自然就是“三堂”,不过三堂便是知府大人内宅家眷住的地方了。三堂是寻常四合院的规格样式,有左右门房,左右廊房和上房院。这上房院,就是知府接待上级,商讨政事的地方了。除此之外,在二堂西设有花厅,花厅之北则是签押房,签押房即鉴判之所,平日签署公文,案卷,办公,都在这个地方。
此时的知府大人,便是在签押房目光沉郁,暴躁难安。
怜光府知府大人郑先郑修明,如今已是四十有八的年纪,但却两鬓早白,模样倒像是花甲老人。其实说来他的仕途也不亦悲乎,这位郑大人二十三岁春风得意金榜题名,以二甲第三名的成绩得以钦点翰林,随后又观政六部,前途一片光明。但无可奈何的是,刚刚从科举中大浪淘沙出来的小郑大人实在太刚强了些,却忘了过刚易折,偶尔的一次聚会中酒后失态,大骂当时大权独揽的监国宰相欧阳舒,说他是“无有伦常,不当人子”,又骂他“目无君上,撷天子之威福擅自己之私权”,是当之无愧的“奸国宰相”。这下当真是捅了马蜂窝了,欧阳舒乃当今宰辅,权势滔天,几乎是第二日,郑先就被下放地方,成为了一个举人都能干的七品县令。
虽说不久之后欧阳舒就被当今天子一手宝剑一手白玉稳妥的赶出了庙堂,可是小郑大人在地方的穷山恶水中蹉跎了太多光阴,早对京官失去了念想,不愿意起复。吏部有不少他的同年,大家稍许运作,便将他提到了知府,放在了江南这种海晏河清歌舞升平的盛世中,也算是对这位小郑大人直言不讳的酬劳吧。
而此时的郑知府郑大人,却丝毫没有感受到江南的宁静祥和,反而感到了山雨欲来前的暗流汹涌。
“青苇,如今这怜光府里,已是满城飞絮了啊。”
知府大人声音低沉,透露出巨大的疲惫。被他呼唤的那人坐在知府大人对面侧方,是个与知府大人年纪相仿的中年人,着黑色的对襟襕衫,表情同样沉郁,片刻后才缓缓道:“这位陈大人,实在太刚猛了。”
“是太年轻啊。”知府大人叹了口气,轻声道:“与我当年何其相像,也是进士及第,得意登科。况且他如今没有奸相当权,又多逢拔擢,而立之年就是户部左侍郎,离大九卿之位只差一线之隔,心气儿能不高吗。”
青苇先生显然是知府大人身边常年参谋的西席,对大人了解颇深,听他谈及经年往事,便知大人是真的担忧了,便轻声说道:“东翁,容我说句不该说的话。”
知府大人眉头微皱,点了点头。
青苇先生深吸一口气,才缓缓说道:“东翁,钦差大人携谕旨明剑自京都奔赴江南,所行深意不言自喻,这点无须赘述。而我要向东翁所说的,是这十几乃至二十年来,江南诸州府的敏感之处。”
“东翁,自当今登基,已二十有一年矣,所赖上天眷顾,祖宗垂怜,二十载来,除西北灾荒之外,全国也算得上仓廪充实。此间又以江南为盛,盖因为江南丝织茶瓷之业,百倍于全国,且不算农耕之利,单就看瓷器、茶叶、钱庄、丝绸,就足以让江南州府存蓄之财远超太仓府库!这些事情外人也许还不太清楚,但咱们江南人自己却心里透亮,说句不好听的话,江南富贾们,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确实是富可敌国啊!“
知府点了点头,叹道:“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皆为利往。江南得天独厚,千百年积累开发,才有如今的泼天财富啊。“
“可毕竟,国家收税太少。”青苇先生眉头紧锁,说道:“自国朝建立至今,官府对商贸一事便及其的不上心,不管是英明神武的太祖皇帝还是垂拱而治的当今陛下,对商业一途的看法就从来没有变过。虽然这样可以抑制商人地位,稳定土地上的农民,但这也间接的给了商人积累财富,腰缠万贯的先决条件。商税稀薄,商人又怎么会不坐大,从而富可敌国?”
知府大人脸色凝重,道:“先生说的对啊。不过如今商人薄税已经成了朝野共识,一来本朝重农抑商,是祖宗法制,万一提高商税,也就是间接提高了商人地位。你要知道,士林那些清流们,是决计不肯和商贾们共处一室的。这二来嘛……”
“二来。”青苇先生补上了知府大人未曾说完的话,他笑了笑,道:“如今法度崩坏,国朝初年制定的商贾子弟不得科举的规矩早被人抛在了脑后,而今的官场上,几乎处处都有商人子弟的影子。就算许多家世清白的官员,不少也曾受过商贾恩惠,在对待商税上,肯定理偏。”
“不错。”知府大人痛心疾首,握紧拳头道:“而商人们有了这些子弟在官场上冲锋陷阵,自然就不在乎自己是否地位低下,朝廷是否依旧重农抑商,而那些清流们,又是否对他们骂声如潮。比起名声而言,闷声吃猪肉才是正道王道,总而言之,如今的天下是银子的天下啊!”
“这样自然也就加剧了商人的财富积累,北贫南富,国家却无力调度的弊端就更加突出。”青苇先生顿了一顿,才断然道:“此番西北大灾,朝廷赈济无力,导致尸横遍野,三省恍如人间炼狱——这样惨烈的事情发生,就是这种弊端的典型证明!”青苇先生似乎也有些无奈,声音变得软了起来,无力道:“东翁,这也正是在下所说的江南敏感处。这些商人们虽然家财万贯,但最怕的,就是家财露白。若是朝廷因赈济西北这件事吃惯了江南富户,且还觉得江南富户很好吃,很容易吃,甚至吃上了瘾……那他们辛辛苦苦积累的千万巨资,就将成为风雨飘摇的一叶孤舟,没有任何保障,随时随地都可能被狂风骇浪吞噬,万劫不复。“他言语果决,道:”这才是整个江南,最敏感的地方。“
知府大人闭上眼睛,无力道:“是啊。”
青苇先生苦笑两声,叹道:“可偏偏在这个时候,朝廷又派出了一个催命鬼般的陈秋山,根本无视江南禁忌,干脆大马金刀摆明了吃定富户的态度。他这样无异于有两个结果,一是走了****运,让他乱拳打死老师傅,江南乡绅富户并商贾世家都服了软,任他调度,凭他指挥;二,则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逼的官员们与商人彻底结合,一起运作将他赶出江南道!当然。。”说到这,青苇停了一下,看着知府大人越来越阴沉的脸,严肃说道:“这样一来,不但西北又将饿殍千万,且对朝廷而言,江南就成了不听号令,自成一派的眼中钉,肉中刺,早晚要拔了它!”
知府大人疲惫的闭上眼睛,点了点头,自然是承认青苇先生说的话。
青苇先生叹了口气,缓缓说道:“原本以我们的计划,是要费十年之功,慢慢改变江南商务现状,逐渐瓦解江南官商勾结的内幕,却不料被这个钦差大人斜插一杠子,如此一来,东翁被夹在其间,便万分尴尬了。”
郑知府沉默下来,表示着对青苇先生所说的认同,片刻后他睁开眼睛,略带一丝歉意的看着青苇先生,开口说道:“先生也是簪缨世家,若不是被我拖累,恐怕早就平步青云直上庙堂了,是我耽误了先生了。”
青苇先生忙起身道:“东翁切莫再说这样的话,东翁为国为民,不惜鞠躬尽瘁,乃当今治世之能臣,可以为东翁幕僚,参赞政务,正是在下求之不得的事,东翁这样说,岂不是让在下羞愧难当,无以自容。”
郑知府叹了口气,说道:“有先生在,真是郑某的福气。”说到这里,府尊大人不知想到了什么,表情一时决然下来,沉声道:“若是真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郑某哪怕拼着一生仕途完结,也要将那不当人子的陈秋山赶出江南!”
“万不至于到了此等地步。”青苇先生赶忙出口阻拦,顿了顿,才冷静道:“哪怕有京城来的书办令史帮忙,想要理清怜光府内所有衙门的户刑工三房账册及卷宗,也得不下三天的功夫。所以我们至少还有三天的时间用来仔细思考对策,想来天无绝人之路,府尊大人万不必如此悲观。”
“嗯。”郑府尊平静下来,点了点头,继而身子向红木的太师椅靠背上靠去,神色里充满了疲惫,轻声喃喃道:“书生意气,却常常误国啊,可怜可叹,你我还得百般小心。“说着慢慢转头,朝着京城所在的方向投去一抹不可言说的目光,叹道:”拆东墙补西墙,朝廷的那些大人们啊……“
青苇先生也轻轻的在心中叹了口气,又看见知府大人神色疲惫,显然已倦怠之极,知趣道:“大人不必想那么多,先好生歇息吧,船到桥头自然直,总归会有法子的。“说完便起身告辞。知府大人自然起身相送,不过想来也是累极了,只送出签押房,便在青苇先生的劝阻下止步,又安排管家将先生送出府衙,这才全身无力的倒回房间。
在签押房又歇了会儿,郑大人才慢腾腾回到后宅,匆匆与夫人打了个招呼,其余人一概不见,连晚饭都没吃,就回屋歇息了。只是躺在床上的知府大人,始终心乱如麻,愁眉紧锁。
郑大人一夜无眠。